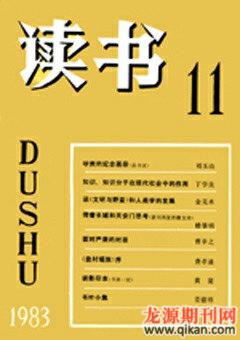读书有得
1983-07-15 05:54戴金禄
读书 1983年11期
戴金禄
读《读书》今年第四期上陈百楼同志的《熔铸三例》,颇受启发,深有所得,至为感奋。近读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又知古人对此道已有所论述,且古之作家振笔为文亦不乏善于吸收前人语言之有益营养熔铸新词之例,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词汇之宝库。“唯陈言之务去”,寻章摘句,或生造词语,终非妙法。欲在语言的学习和运用上推陈出新,不袭人后,别出生意,能收到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实效,却无捷径必得之术,非积学数载,手不停披,勤于刻意钻研,难有可得之道。鲁迅先生亦属善于熔铸古人语言之高手,其文辞往往带有文言气息,但运用宛转自如,恰到精当,读来绝无古奥生涩之感,反觉丰富而简洁,别有一种情味。就现在来说,惜乎喜爱佳辞者实繁,善学语言者盖寡,尤不知熔铸古人和群众语言之蕴奥者更之。还是邓绎《日月篇》里的论述堪称独得之见,足以发人深思:
古称中郎枕秘,深畏人知,汉、魏以来,一文之传,殊不易易;而后儒每忽视之,其终于固陋也宜哉。
以上所得,乃仗《读书》刊文所启,人云“开卷有益”,语诚不谬。
猜你喜欢
名作欣赏·学术版(2022年7期)2022-07-17
作文评点报·低幼版(2020年31期)2020-07-23
意林(2020年12期)2020-07-03
意林·少年版(2020年1期)2020-02-18
意林·少年版(2019年23期)2019-12-27
意林·少年版(2019年21期)2019-12-17
北方文学(2017年19期)2017-08-01
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7年6期)2017-04-17
学生天地·初中(2017年2期)2017-03-24
学苑创造·A版(2016年6期)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