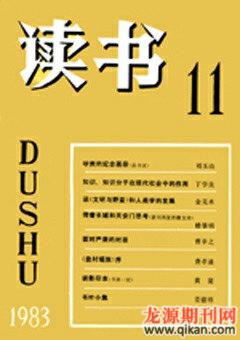关于亨利·特洛亚的“奇观”
李清安
为了了解在电视大量普及的时代,书籍能否抵御得住五彩缤纷的活动画面的吸引力,一九七八年,法国《快报》周刊委托一家研究所,进行了一番社会调查。调查结果,使人们意外地发现,过去二十年间,法国的电视机数量增长了十五倍,而读书人的比例非但没有相应地减少,相反,却大幅度地增加了。另外,在五花八门的现代读物中,人们读得最多的是小说。而在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作家中,名列第一的是巴尔扎克;仅次于他的,是亨利·特洛亚。①
亨利·特洛亚(HenriTroyat),法国学士院院士。他是个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原名列夫·塔拉索夫(LéonTarassoff),一九一一年生于莫斯科一个祖籍亚美尼亚的富商家庭。十月革命以后,一家人出于资产者对革命的恐惧,逃出俄国,在欧洲各地流浪,后来在巴黎定居下来。他们远离祖国,身在异邦,不久就陷入了穷愁潦倒的境地之中。一家人为生计奔走,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背井离乡的苦楚。在这个过程中,列夫·塔拉索夫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变成了身无分文的游子。这一变故使他加深了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他不得不一再辍学,还当过兵,并且很早就放弃学了一半的法律课程,到巴黎市政厅里充当一名文书,借以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他用俄文和法文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等大作家的作品,并且从长辈那里听到了许多从亚美尼亚土著到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民间故事以及俄国侨民们的离愁别绪。早在大学中攻读法律的时候,他就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可惜无人肯予出版。一九三五年,又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荒谬的日子》(Lesfauxjours),不抱希望地交到一家出版社,不料竟被采纳了。他本想把自己的俄文名字大大方方地印在书的封面,借此也算出口怨气。无奈出版商认为这会使人误认为翻译小说,执意要他另起个笔名。于是,年轻的塔拉索夫在纸片上胡乱拼了一气,遂造出了这个“亨利·特洛亚”。这个亨利·特洛亚出现时,仅二十四岁。
亨利·特洛亚的处女作引起了颇大的反响,还获得了“大众奖”。但是,那本书笔法沉闷,故事枯燥,并未引来很多读者。此后,他一边继续在巴黎市政厅中混事,一边抽空写作,相继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一九三八年,他的第四本小说《蜘蛛》(LAraigne)出乎意料地荣获了法国极有声誉的龚古尔文学奖。从此,特洛亚名声大噪,便放弃公职,当上了专业作家。
从四十年代至今,特洛亚总共发表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六个短篇小说集和六部多卷本“长河小说”,还有几个剧本和许多特写、随笔和游记等作品。
作为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作家,特洛亚还先后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和托尔斯泰等俄国大作家的传记。
特洛亚九岁才来到法国,但却出类拔萃地掌握了法国的语言艺术,四十八岁(一九五九年)就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成为全国仅有的四十位“不朽者”②之一,据说,他是有史以来得到这种崇高名誉的最年轻的一位,而且,他的作品在人才济济、名家辈出的现代作家群中独占鳌头,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无怪乎《世界报》上的评论文章将他称为七十年代法国文坛上的一大“奇观”。
有过一种传说,认为在西方书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一些趣味不高,艺术价值不大,但颇能以故事离奇迎合“大众”口味的所谓“畅销书”。特洛亚的成就,正是对这种主观忆断的反驳。特洛亚并没有想去迎合什么人的口味,也并没有削弱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但却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中有严肃的思考,有堪称高超的艺术,一言以蔽之,他抓住了最广大读者的心。
特洛亚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当代的人,我要以当代人的方式,为当代人去思考,去述说,去写作。”③他的全部作品,正是贯穿了这样一个宗旨。
在特洛亚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是一批以发生在俄国的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作者自己把它们命名为“俄国题材小说”或“法俄小说”,其中有《只要大地存在》(Tantquela terre durera,1950,三卷)、《播种与收获》(Les Semailles et les Moissons,1953,五卷)、《承继未来的人们》(Les Heritiers de lavenir,1958,三卷),《正义者的光辉》(La Lumiere des Justeso,1959—1962,五卷),《莫斯科人》(Le Moscovite,1974,三卷)。这些小说篇幅很长,内容基本上说的是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潮传到俄国,俄国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苦自求索的故事。这些题材,尽管在时间上属于历史,但所反映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知识阶层的思想现状。作者说,在这些小说中,超乎所有人物之上的,有一个主角,就是:“光阴”。他说:“我企图表现的,是那永无休止,屡屡再现的爱情、苦恼、政治热情、天伦之乐、死的悲哀以及代代相承的欲望。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头一个经受了某种生涯。其实,他不过是千百万跟天地一样古老的角色中的一个而已。”
早期代表作《蜘蛛》,写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中,种种习惯势力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人束缚得死死的,就象一张蜘蛛网无法摆脱。而近年来的新作《安娜·普列达依》(Anne Predaille,1973)则是反映的一家人之间的隔阂。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变得冷漠无情,彼此无法理解。这些小说,正是如实地道出了现代法国人深深的苦衷。《登峰造极的友谊》(Une extrème amitiè,1963)讲述的是,一对和睦夫妇,由于往日生活的印象突然再现,陷入困惑之中。《包、剪子、槌》(Lapierre,la feuille et las ciseaux,1972)探讨了西方社会日益引人注目的同性恋问题。书中同性恋者的形象安德列,曾经引起热爱特洛亚作品的读者的激烈批评,特洛亚本人,也把他列为自己笔下人物画廊中,一个“成问题”的特例。不过,这个“成问题”的文学形象,也许正好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成问题”的现象,也未可知。
在反映当代生活方面,特洛亚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长篇多卷本小说《艾格勒基埃尔一家》(LesE ygletière,1965—1967,三卷)。这部小说,用写实的手法,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当代巴黎市中,一个大亨家庭的老少关系分崩离析的过程。小说的最后一卷,标题就叫“裂缝”,表现了作品的主题:“一个陈旧、腐朽、布满裂缝的社会构架,正在咔咔作响地崩塌”。
特洛亚旅行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在旅行的过程中,他通过一个作家的敏锐的观察,用雄健有力而又生动活泼的笔调,记述了各方面的见闻,表现了当代世界的种种矛盾、不公与内在的苦痛。这就是他的游记《山姆大叔的小屋》(La Case de loncle Sam,1948)和《从摩天楼到椰子林》(De gratte-cielenco-cotier,1958)。为了了解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下,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特洛亚专程在规模巨大的雷诺汽车城里小住了一段。他参观过许多的工厂,到工人的家中拜访,在咖啡馆里与各种人闲聊,写出了长篇特写《一个“王妃”的诞生》(LaNaissance dune Dauphine,1958),在谈到自己的感受时,特洛亚说到:“面对着一个个烘干炉喷出的烈火,一台台冲压机发出的巨响,还有那传送带的单调的动作,我感到大吃一惊。而最使我惊异的,还是那被紧紧束缚在这嘈杂的声响和千百种枯燥乏味岗位上的人群的状况。我觉得,眼前好象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充满了无尽无休的疲劳、梦想、忧虑、希望、反抗和屈从。……我尽量忠实地将这一切写入自己的书中。”
就这样,我们在特洛亚的作品中,看到了法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听到不同人群的呼吸,感受到当代生活的节奏和韵律。正如特洛亚所说:“在今天,再想象历代名家那样写作是不可能了。即便想那样,也办不到。周围的一切给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打上了烙印。我们读到的报纸和书籍,听到的音乐与对话,看到的电影、戏剧的海报,所有这一行行文字、一幅幅画面、一个个音符、一阵阵声响构成了一个现代的世界,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我们。”他还说:“一部小说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它解答了什么疑难,而是在于它提出了问题。”特洛亚的一些小说(不是全部),就是因为提出了西方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并且获得了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价值。
特洛亚为当代人写作,他的作品为当代人所喜闻乐见,除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外,还在于它们有着崭新的艺术手法。
多数当代法国文学的权威评论家,都把特洛亚视为传统文学潮流的代表而屡屡提及。关于这一点,特洛亚说:“所谓‘传统小说,其实是对前人作品的发展。它在平稳地创新。它的新奇之处不大显眼,但总是存在的。只是不耍花招,不露形迹,自然而然地得之于环绕在作家周围的外部世界。”
当别人问及,特洛亚属于哪种文学流派时,特洛亚态度鲜明地回答:“哪派都不是。”他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没有比把自己限定在任何一种学派的体系中更可怕的了。从文学史上看,不难查明,那些杰出的作品,绝不是由于因循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恰恰相反,正是不顾条条框框,超出了条条框框,从而才给我们带来了人类的信息。谢天谢地,上帝在文学的娇弱王国里,使我们得免于恐怖主义之害!……要想把小说艺术的汹涌潮流纳入某种渠道,那是不可能的。文学遗产的丰富性就在于它的多样化倾向。”
说特洛亚是“传统派”,这只是相对于那些“革新派”而言。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拥有“并行不悖的两种文学”。一种是那些不断追求新的表现形式、此伏彼起的各种“现代派”如象征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反戏剧”、“新小说”等等。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但共同的趋势,都是与传统决裂。另一种文学就是在上一种文学不断嬗替、你消我长的同时,稳步发展,坚守着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传统作家的旗帜的种种“传统作家”。总的说来,在推翻还是维护传统这一点上,它们不外是两大派。比较起来,第一派的作家经常会引起轩然大波,但艺术生命不长,读者也有限。而第二派的作家,尽管不好作惊人之举,但始终占有着大量的读者。
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比埃尔·布瓦戴弗尔说:“与某些热衷于党同伐异的‘宗派批评家们的反复说教相反,那些保持传统写法,书籍大量再版的小说家(如特洛亚、巴赞、④圣比埃尔⑤等),他们的存在不但没有影响对小说艺术的探讨,相反却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所谓的“维护传统”,只是为了与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加以区别。其实决不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他们当中有影响有成就的大家,其创作手法也在不断地演进、丰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洛亚要算是“传统派”中的革新派了。
不错,对待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历代艺术大师,特洛亚始终是推崇备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头脑束缚住,为了表现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特洛亚采用了变化多端的手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大量吸收了现代派们的表现技巧,因此,他的艺术日臻完美,总能生动有力地说出他想要说的话。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特洛亚表现了一种尽善尽美的技巧,把不同的传统熔为一炉。他就此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使得小说对读者不再具有任何抗力。而是适应读者的希望与心理,与其说是文学作品,毋宁说更象是消费品。”⑥
在谈到小说创作方法时,特洛亚主张:“写小说,就是要使可能生动的事物,尽可能地生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地照抄生活现实。现实必须经过作者主观感受的改造和折射而后再表现出来。”他还主张:“小说家应该让他的人物活跃起来,但不加品评,不做褒贬。他如果参与到故事中去,称赞或者指责自己的人物,小说的魅力便会被他破坏掉。”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作家没有主张,缺乏爱憎。而是指的写作方面的技巧。其实,特洛亚的作品中,恰恰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当一位文学记者把特洛亚的政治见解归纳为“怀疑论者”时,特洛亚更正道:“就算是个自由派吧。”而当记者又问他,作为一个自由派的人士,生活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特洛亚回答:“人间的苦难。它是那样浩瀚无边,令人瑟瑟发抖。自然,要是让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享受洪福,那是太困难了。但是,我希望明天的人们会通过爱德,通过相互了解,能改变这种现状……也许就是为了探求别人灵魂中的秘密,我才无意中决定写起小说来。”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激情,特洛亚写出了这样一些感人肺腑的篇章。他说:“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之所以不得不写作,并非为了要尝试某种未曾有过的表现方式,而是出于内心的冲动。”
当别人问到特洛亚对当前的政治是否关心时,特洛亚回答:“能不关心吗?撇开了政治,这就等于割断了自己与世界的种种运动间的联系。所差的是,我并不以斗士的身分参与政治。一个政治家必须善于行动,而我却是一个幻想家。”
目前,特洛亚住在巴黎市中心,他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每天在书房里站着写作。面对着“奇迹”般深受读者欢迎的现实,他表示:“每当出版了一本新书之后,我就又一次处在无以表述的荒原之中。一切都恢复到成问题的局面,就好象我什么都不曾写出来过。我对自己说:‘迄今为止我所作的一切全都不能算数。现在才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可是,我行吗?这种热情夹杂着不安的心绪,始终在工作中伴随着我。”他表示:“我是一个耍弄笔杆的手艺人,”“我要藐视拖住我步伐的种种障碍,不顾一切地进行坚韧不拔地工作。”
特洛亚还有一个习惯,从来不读自己的作品。“作品一旦写完了,出版了,我就很快把他丢到一边,马上酝酿别的作品。我从来不重温往日写成的书。这些书,我对它们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于吗还去读它呢?它们已经从我的身上脱离开来,走入了别人的天地,赶自己的路去了。”
(《被玷污的雪——亨利·特洛亚小说选》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详见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法国在读书》一文。
②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系终身任职,而且历来被公认为学术界和文艺界的一种崇高荣誉,故有“不朽者”(immorte1)之称。
③引自特洛亚口述《路漫漫》(un si 1ongchemin)一书。后文中特洛亚作品以外的言论,出处同此。
④巴赞(Hervé Bazin 1911—),当代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学士院主席,五十年代曾被公推为“近十年来最佳小说家”。
⑤圣比埃尔(Michel de Saint-Pierre,1916-),法国当代著名作家。
⑥引自《文学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法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