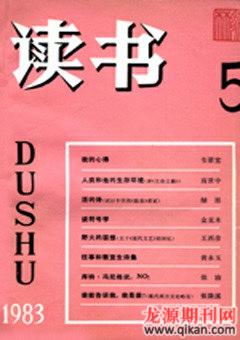古老的文化街
叶祖孚
《琉璃厂小志》读后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区,法国巴黎有赛因河畔,英国伦敦有弗业街,日本则有“书海”之街神田町。在我们国家,那就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了。这条街,这么古老,经历了五六个世纪的变迁,充满着斑驳离奇的故事,它以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吸引着国内外人士的普遍注意,不少人用如花的妙笔为它写下了吟咏的诗篇和文章。根据孙殿起搜集的资料汇编的《琉璃厂小志》一书,就以大量生动的材料证明了这条典雅、古朴的街道是名符其实的文化街。
一
清初,满族官员聚居内城,汉族官员大多被指定住在城外。这样,顺康年间一些著名的文人就散居在琉璃厂附近,像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吴梅村就居住在东琉璃厂,另一位龚鼎孳居住在离琉璃厂不算太远的善果寺。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史学家孙承泽居住琉璃厂南,他的住宅叫“退谷园”。《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居住在海波寺街。清初著名大诗人王渔洋也居住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这恐怕是日后琉璃厂成为文化街的一个远因。清初,最早的文化中心不在琉璃厂,是在广安门外慈仁寺(报国寺),这里有个书市。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北京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慈仁寺坍废严重。于是这个文化中心就逐渐移到离文人雅士住家较近的琉璃厂来了。加以那时琉璃厂附近还有丛林清泉、高阜低洼、风景美丽,正好是文人们徘徊踯躅的场所。那时琉璃厂已经有了鳞次栉比的房屋,比较稠密的人口,成为较大的市区街道。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兴起,海内举子
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既以古书业、文玩业为其主要内容,又与达官贵人的纷至沓来相结合。所以曾任《四库全书》编修官的程晋芳写给袁枚的两句诗:“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吝摊钱得古书”,简要准确地说明了琉璃厂文化街的特点。王公贵族们下得朝来,来到琉璃厂古书店或骨董店里,抽袋烟,喝碗茶,下盘棋,翻阅古书,欣赏骨董,纵论古今,尽兴而去。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清末。他们在厂肆活动久了,谈得高兴,不免铺纸舒腕为店铺写几个字,所以琉璃厂店铺的匾额都不出于凡人手笔。游逛琉璃厂的人除了买些古书字画外,附带也要欣赏店铺的牌匾,这也已成为习惯。《琉璃厂小志》中有关于坊肆匾额录的一段资料。据熟悉琉璃厂情况的人说,所有牌匾以翁同
在清朝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官员对朝政的议论,候试举人纵谈各地的情况,一般都不见诸文字,在浩如烟海的明清笔记中也很少能看到。但是《琉璃厂小志》收进去的朝鲜诗人柳得恭所写《燕台再游录》一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宝贵资料。
乾嘉年间,朝鲜文人随使节来京访问,他们都到琉璃厂采购书籍,结识友人,吟咏唱酬,互赠诗文。琉璃厂在沟通中朝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的材料来源看,有的显然来自官方,有的来自民间。从内容看,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谈话者的神态来看,有的粉饰太平,言不由衷;有的说了真话,又受到谴责。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好史料。乾嘉盛世,已经隐伏着严重危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样下去,怎能不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呢?
戊戌政变失败后,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者搬走了故宫收藏的图书、字画。他们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研究中国的情况,纷纷来到琉璃厂抢购图书。一时大批书籍文物外流。这种情况引起了琉璃厂人士的注意。孙殿起(耀卿)就写了《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一文,辑在《琉璃厂小志》内。
另一署名“老羞”的人,也注意到了这种文化外流,国粹罄尽的危险状况,他写诗:
大雅于今已式微,
海王村店古书稀。
如何碧眼黄须客,
卷尽元明板本归。
琉璃厂人士对这种文物外流的情况,是有斗争的。有些情况没有辑入《小志》内。如一九三○年左右,日本人松村太郎到松筠阁古书店买书,和学徒发生口角,他猖狂地要书店辞退学徒,并以不到书店买书为要挟。松筠阁主人刘际唐,是收藏期刊杂志的专家,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表示宁可不做生意,也要保护学徒,一时传为美谈。这是琉璃厂的骄傲。当然也有些书商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了横财。
作为历史资料书,《琉璃厂小志》记载了不少有意义的资料。例如它提到民国七年康有为在海王村公园开设长兴书局,出售新书的事。这家书店只办了五个年头就消失了。一九二四年起康有为将长兴书局归通学斋书店经营,它的一部分财产并进了北京最古老的印刷厂京华印书局,几年前我听原京华印书局经理宣节先生说起,他还使用过当年康有为用过的写字台。“文化大革命”中京华印书局被并入当时号称“六厂二校”的新华印刷厂,这张带有历史意义的写字台也被调走,不知流落何方。
二
在《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最重要的几篇著作应是乾隆时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民国二年缪荃孙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小志》编者孙殿起写的《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写的《琉璃厂书肆四记》等。这些文章记叙的时间从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起一直到一九五六年书店公私合营为止,它从商店概况、经营特点、街道风貌、铺主特点等方面记叙了这条街将近二百年来的变迁,虽然文章题为书肆记,实际上旁及其他行业,应该说是称得起“志”一类的文章。尤其是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在近二百年前,他留意观察,为一条街写了记,这样的文章在近百年来都是罕见的。李文藻和缪荃孙写上述文章时正值乾隆盛世和民国建立之初,市场显得繁荣。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琉璃厂的古玩、图书等行业的繁荣实际上是恶性发展的表现。到孙殿起写《琉璃厂书肆三记》时,他注意到散居在琉璃厂附近街巷中的个体经营户,也都写入《三记》中,并且加上了隆福寺、宣武门内等处的书商,材料比较完备,雷梦水写的《琉璃厂书肆四记》,还记载了每家书店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现归何处,说明了铺主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李文藻,益都人。乾隆进士,曾官广西桂林府知事等职。他本人就是个藏书家,《琉璃厂书肆记》记载他肯典衣买书。他在文章中记载琉璃厂的面貌:“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者。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纸、墨壶、镇纸、弓绷、叠褥备列焉。”解放以后的琉璃厂基本上也是这样。书店“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后,藻玉堂书店王雨等人还派自己的徒弟去南方收书。李文藻还记载他在琉璃厂书肆发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的书,上面盖着楝亭曹印,有的书是曹寅抄录他的好友朱彝尊曝书亭藏书的副本。这个情节既证明了曹家的败落(当时曹雪芹潦倒西山,刚死不久),也说明了这些书籍不管来自何方,最后总得在琉璃厂书市出现。藏书家不惜千金,寻找他们喜爱的书,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盖上一方鲜红的藏书印。李文藻就记载他的老师纪晓岚不惜千金买书的情况。《小志》也有材料记载有些人家文物被盗,不久也能在琉璃厂重新找到。有人甚至发现自己的字迹被人钤上假印,冒充文物出售,重新购回,不禁哑然失笑。
《琉璃厂书肆记》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记载了琉璃厂人物的生动形象。“书铺之中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文章还写老韦爱读书,他能帮助顾客选书,介绍顾客读哪些书,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笔墨不多,老韦这个熟悉书籍的人物如在眼前。
这确是琉璃厂的特点。书商天天接触书籍,从小买书卖书,他们熟悉书的版本、源流、内容,他们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受其熏陶,日长月久,他们自己也成了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老韦就是第一个出现在文献中的琉璃厂书肆的专家。
第二个就该是《小志》编者孙殿起老先生了。孙殿起(耀卿)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卒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享年六十五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朝代,饱经沧桑,眼见书籍的几度聚散,使他增加了很多知识,他又常和伦明、陈垣、徐森玉、王冶秋等交往,学识更加渊博。一九三六年,他根据自己目睹手经的书册,一一作了记录,写成《贩书偶记》二十卷(已再版数次),后来又写了《丛书目录拾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等重要书籍。《琉璃厂小志》也是他的重要著作。孙殿起先生是琉璃厂书商第一个以著作问世的人。他平时搜集资料之细心和严谨令人吃惊。我曾见到他在厚厚的古籍中夹纸条,问他这是作甚时,他答阅编书。后来看到《琉璃厂小志》这部巨著时,不能不为他在搜集资料方面所下浩繁的功夫叹服。
其次,就该是王晋卿了。琉璃厂书肆有学问的书商有谭笃生、何厚甫等人。但是北京著名的藏书家,通学斋古书店的铺东伦明却推崇孙耀卿与王晋卿二人。他写诗:
书目谁云
书场老辈自编成。
后来屈指胜兰者,
孙耀卿同王晋卿。
王晋卿与缪荃孙、姚茫父、陶北溟、邢赞亭、周叔
再往下就是现尚健在的雷梦水同志了。他是孙殿起的外甥,从小随孙学徒,得到孙老先生的亲传,后来又得朱自清、邓之诚、郑振铎、阿英、王冶秋等专家指点,对于古籍方面的知识更趋丰富。孙殿起逝世后,他和张次溪、陈怀谷、赵羡渔等人协助整理出版了孙先生遗著《琉璃厂小志》,去年还整理出版了孙殿起编辑的《北京风俗杂咏》。近年来又撰写了《慈仁寺考略》、《古书经眼录》、《隆福寺书肆记》等文章。他继承了孙老先生详细占有资料的优点,挨家访问,了解书商搜书的历史,一九六三年撰写了《琉璃厂书肆四记》一文,今年《小志》再版时,将此文收进去,删去了有关渔洋故居古藤杂咏等资料。
其实琉璃厂还有很多可写的人物。《琉璃厂书肆后记》作者缪荃孙记载翰文斋古书店曾为他搜罗了很多宋元版本书,主人韩子源(有时写自元、滋源)颇有能耐。孙殿起写《琉璃厂书肆三记》,也提到翰文斋与韩子源,一九三二年时这家书店已“经营五十余年”。《琉璃厂书肆四记》中又提到韩子源,历记他搜寻各种名贵书籍的功绩。由于上述文章的记载,可以证明翰文斋是当时琉璃厂最古老的书店,门口挂着光绪年间当过礼部左侍郎的李文田书写的匾额,那是韩子源的父亲韩心源开设翰文斋时,李文田朝罢归来到他那里看书,即兴为书店题写的。
《琉璃厂小志》有多处提到张樾丞这个人。他能刻墨盒,又善治印。他刻的墨盒都由陈师曾、齐白石作画,由他镌刻成为美观的艺术品。鲁迅先生就喜欢用张樾丞刻的墨盒和铜尺。鲁迅先生也请张樾丞刻过印章,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以后又刻过数次。他刻印兼用各种刀法和笔体,尤擅刻铁线篆(小篆),纤细中显得刚强。解放后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刻了国印,并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治过印。
孙殿起非常重视琉璃厂这种师徒相承的情谊,所以在《小志》中特列《贩书传薪记》一章,以记载师徒渊源。也可以说正是师徒一脉相承,源源不断,才促成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历久不衰。今天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的老韦、孙殿起、王晋卿、张樾丞、雷梦水等人出现,而且青出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把琉璃厂文化街建设得更加繁荣兴旺。
三
琉璃厂除了以图书、古玩著称外,清朝以来一年一度的春节厂甸集市也在这里举行。所以《琉璃厂小志》书内也有很多记载北京风物方面的资料,它是研究北京民俗、风俗、时代风尚的极好材料。《小志》编者孙殿起先生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他曾为那年的厂甸集市布局设施提过建议。
厂甸集市有它的独特的手工艺产品,象早期的琉璃制品、后来的风筝、空竹、宫灯、乐器、玩具、面人、剪纸、绒花等物,通过这些手工艺产品可以看出这条街与文化的关系。厂甸的小吃也具有特色,象大糖葫芦、碗豆粥、艾窝窝等,在老北京的脑海里都记忆犹新。对海外侨胞来说,他们就是把厂甸的大糖葫芦与北海的白塔、天坛的古柏看作北京的象征。奇怪的是琉璃厂的小吃也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象享有盛名的信远斋酸梅汤,制得后主人把它放在一只白地蓝花的大瓷缸里,再镇在一只老式绿漆的大冰桶里。人们在琉璃厂浏览旧书、古玩、字画之余,信步来到这里,主人用白铜勺从大瓷缸里给您斟上一勺,倒在一只古色古香的青花瓷碗里,一口喝下去,真称得起“沁人心脾”。信远斋的匾是清末老翰林、博仪的师傅朱益藩写的,一式两块,“信远斋”和“密果店”。喝酸梅汤的人,差不多有这个习惯,一边喝着冰凉的冷饮,一边悠悠地欣赏着这块有名的匾额。您说,这样的食品店,开设在历史久远的琉璃厂里,不是正好增添了文化街的特色吗?难怪鲁迅先生一九三二年回京省亲时,作了著名的“北平五讲”,敌人阴谋逮捕他,他仍抽空去琉璃厂,并到信远斋买了蜜饯。
研究中国杂技史的同志也可以注意《小志》中记载的琉璃厂的杂技资料。北京的杂技有悠久的历史,平时在天桥一带,一到春节,就到厂甸设摆献艺,《小志》的资料说明那时已有驯熊、驯虎的表演。孙殿起辑的另一本书《北京风俗杂咏》,也有这一方面的丰富资料。
书里记载的很多风尚,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已经消失了。再读此书,不免激发人们思古之遐想。琉璃厂很多精巧的手工艺品或美味食品,也长期为人民赞赏和怀念,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有关部门恢复生产,这不是复旧,而是人民需要它们。
《琉璃厂小志》原于一九六二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现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所收资料限于明、清、民国的史料,很多当代的资料限于体例没有收进去,这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例如琉璃厂一家中外驰名大型书面文房四宝商店——荣宝斋,叶圣老就写过文章,《小志》没有收进去。一九三三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郑振铎为选购笺纸,风尘仆仆地在琉璃厂各南纸店中反复寻觅,后来写了《访笺杂记》一文,也是介绍琉璃厂的重要资料,《小志》限于体例,没有收进去。近年来雷梦水同志有志于把《小志》以外介绍琉璃厂的其他重要资料,另辑《琉璃厂续志》一书。在《琉璃厂小志》再版之际,殷切希望雷梦水同志编辑《琉璃厂续志》一书的美好愿望在出版界的支持下能够圆满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