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艺术品市场的探索与演进
吴明娣 常乃青
[摘要] 北京艺术品市场在清初恢复以来,经历了清中期的全面发展,至晚清已空前繁盛,并在清末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成为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艺术品流通中心,一时间享誉海内外。这一过程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清代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对20世纪中国书画、古器物的流通以及国际艺术品市场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清代 艺术品市场 北京 琉璃厂
清代的北京艺术品市场从恢复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在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极为丰富的面貌。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统治者无心顾及艺术品鉴藏,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大量文物艺术品随之运抵北京,入藏清宫内府。当然,也有不少文物艺术品在这一过程中流散民间各地。康熙初期,三藩之乱平定后的清廷政局趨于稳定,民间艺术品交易逐步复苏。当时的宫廷贵胄热衷中原文化,对艺术品鉴藏极为关注,不仅妥善保管前朝内府遗存,还倾力从他处搜求各类艺术品。就清朝鼎盛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而言,他们自幼接受着严格的传统教育,对翰墨丹青均有不同程度的爱好。上行下效间,整个社会的鉴藏风尚得以确立下来。由此,彼时的北京艺术品市场在经历了几番动荡后终于渐入佳境。然而,自嘉庆时起,清朝国力转衰,加之道光二十年(1840)列强入侵,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封建王朝一朝倾覆,艺术品鉴藏的主导权由官方逐渐转入民间,北京艺术市场的面貌随之改变。
清顺治至康熙初年,北京艺术品市场虽然走过了一段低迷期,但一批热心收藏的文人士大夫尽力保护散落民间的前朝遗珍,使得明代的鉴藏、交易传统得以继承下来。当时,部分文人带有强烈的遗民情感,借鉴藏整理国故来排遣心中郁结,也有部分文人广求书画古玩以博取功名,一时间“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求古器”[1],涌现出不少热衷鉴藏的名士,这其中既有坚持不事二主的明代遗民崔子忠,又有入仕清廷的钱谦益、王铎、孙承泽、宋权、周亮工、曹溶、朱彝尊等。而这些人中,又以京官孙承泽收藏最富。他在《庚子销夏记》中详细记载了私人收藏状况,为后人了解清初北京的艺术品鉴藏、交易提供了参照。
此外,以徽商为代表的儒商群体竭力保护家族珍藏、推崇传统文化,大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艺术品鉴藏。面对当时人们日渐增长的鉴藏需求,各地古玩商人瞅准商机,纷纷参与艺术品交易。顺治十七年(1660)便有古玩商人向孙承泽兜售荆浩的《庐山小图》,交易场所即位于北京正阳门外金鱼池的孙承泽宅邸。[2]江南艺术品商人与手艺人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北京艺术品市场。南北往来间,北京地区艺术品的流动性得以增强,艺术品交易频次也大大提升。
清朝盛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均不同程度地关注着艺术品鉴藏,是这一时期北京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主导者。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在文化建设上卓有建树,对艺术鉴藏颇为用心,力图通过掌握传统资源来强化帝王的文化主体地位。他推崇董其昌书法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自称对董书“临摹最多,每谓天姿与功力俱优致此,良不易也”[3]。帝王的鉴赏趣味直接影响着书画鉴藏的风尚,宫廷内府的书画收藏倾向也会在艺术品市场上形成传导效应,如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明代松江画派画家的真迹,以及代表正统的“四王吴恽”的书画等在北京售价颇高,受到了市场的追捧。古器物及各类名品珍玩的鉴藏也同样为帝王权贵所看重,这也促进了康熙时期宫廷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彼时,部分内府所造堪与宋、元、明古物媲美的金玉铜瓷、竹木牙角等“时玩”也为当时鉴藏者所珍视。
康熙皇帝任用了一批学养深厚、精于鉴藏的文人士大夫为宫廷服务。梁清标、高士奇等名儒投帝王之所好,在江南地区搜寻了许多珍宝,其中书画名迹有半数被收入了清廷内府,江南地区与北京艺术品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4]当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江南三织造”(按: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既为皇家生产造价高昂的丝织品、玉器、铜器、漆器、金银器等,也负责寻访书画及各类器玩入贡。清宫档案中保存了曹玺(按:曹雪芹曾祖)于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职江宁织造时的进单,上列绘画9件、书法4件、玉器4件、铜器2件、瓷器6件、珐琅器3件、漆器2件、竹木等工艺品28件。[5]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也频频向帝王进献书画、古铜器、玉器、瓷器等。康熙帝多次出京巡幸,其中六下江南,沿途进献宝物者甚众。朝廷上下多方开源,扩充了清内府收藏,由此影响了北京乃至全国的艺术品流通。
清初北京的艺术品交易集中于棋盘街、报国寺等地,这些场所在明代已“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摩肩毂击,竟日喧嚣”[6],至清代“贸易如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皆往来于此,其中交易品种以元、明书画为主,“元四家”、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的作品颇受藏家青睐。这些得到藏家垂青的作品中也有比较罕见的晋唐真迹,如孙承泽就曾于报国寺购得王羲之、王献之的《洛神赋》。[7]除书画外,交易品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器玩。谈迁的《北游录》记载了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见得吴姓医师“以贱直购得大内书画古器若干,因出杯玦珮瓶注,俱旧玉”[8]一事。
清初艺术品价格下跌,五代、两宋名家真迹的润例多在百两左右。当时画家杨铉曾以300两银售出董源的《待渡图》[9],高士奇也曾以400两购得李公麟被视为“永存秘玩上上神品”[10]的《潇湘》《蜀江图》合璧二卷。若在晚明时购藏宋代名家真迹,价高者可达一千余两,而明代名家绘画价低者不足一两,[11]可见重古薄今的现象尤为明显。直到康熙晚期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进入雍正朝以来,国家承平日久,府库充裕,于是内府收藏规模继续扩大,并于乾隆末期达到顶峰。同时,与鉴藏活动相关的理论著述也日趋丰富。乾隆帝命朝廷文臣将内府藏品分别整理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砚谱》,构建了清代皇家鉴藏谱系。

深居宫苑的乾隆皇帝雅好内府所藏名珍,时时观赏、把玩,对古玩市场也有一定了解。在一件宋代汝窑圆洗的底部刻有一首乾隆御制诗:“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对宋代名窑瓷器的交易非常熟悉。[12]清代帝王对文人出入市肆赏鉴、购买古玩颇为向往,然而因宫闱规制所限,不便出入市井,便设法复制、移植民间市肆于宫苑,聊供消遣娱乐,希望借此满足游艺、玩古的心理需求。乾隆皇帝曾在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内专设“买卖街”[13],其间“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更有甚者,“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門监督先期于外城各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卖去者给值,存者归物,各大臣至园,许竞相购买之,内宫亦至其肆市物焉”[14]。“买卖街”虽然是供皇帝游乐的场所,但其中的古玩交易店铺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这说明当时北京“外城”(今崇文门、宣武门以南的街区)已开设了很多经营古玩的店铺,市场的繁荣不难想见。[15]
乾隆时期,清廷与北京古玩市场的联系不仅限于购求,有时也会作为艺术品的供给方。清宫档案中曾留下相关记录:
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楠木供桌一张,传旨着供佛用,钦此(于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奏准交崇文门变价讫)。
乾隆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黑漆描金半出腿西洋玻璃镜一件,传旨着将黑漆镜架上面照样安搭脑,钦此(于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将漆描金玻璃镜一件奏准交崇文门变价讫)。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象牙透雕三层竹节盒一件(破坏),传旨着交崇文门变价,钦此。[16]
这表明,帝王也会淘汰不中意的器玩,将之“变价”出售。在这一流通过程中,发挥纽带作用的即为北京古玩市场。清中期,王公贵族普遍热衷收藏,如文学家曹雪芹,其家世显贵,曾祖、祖父、父亲及本人皆擅书画、通鉴藏。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以大量笔墨描绘了贵族收藏艺术品的雅闻,“古董器玩”“器玩古董”“古董文玩”“古玩奇珍”等词语在书中频频出现。读者通过书中所述荣国府的藏品,也可管窥古玩品类之丰:除唐至明代法书名画外,还有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等珍玩,甚至不乏自鸣钟、怀表、自行船、自行人、鼻烟盒、穿衣镜、洋画等舶来品。

曹雪芹在刻画不同人物的身份、心理时,也往往以奇珍异宝加以指代,如贾琏“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17],送给尤二姐作为信物。贾宝玉的“灵通宝玉”遗失后,贾母派人四下寻找,甚至“情愿送银一万两”[18]。尽管这些描述不免带有夸张成分,但也透露出当时珍稀玉器的贵重程度。此外,世宦之家也并非一味追求奇珍异宝,民间工艺品亦进入了贵族的生活空间,如探春就曾让宝玉为她购买柳编、竹根雕、泥塑等玩好,并通过“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19]表达欣赏之意。此类描述也暗含着曹雪芹的鉴藏观念。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古玩鉴藏的描述,一方面烘托出权贵生活的奢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彼时现实生活中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在《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宝玉与探春的一段对话涉及“字画”“金玉铜磁器”之类“古董儿”的交易品类、价格、场所,不仅反映出贵族公子、小姐的审美喜好,也体现出了艺术品市场的面貌。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及冷子兴、程日兴两位古董商,另有“古董行”[20]“古董房”“古董账”及相关表述,反映了雍正、乾隆早期市场上的艺术品经营状况。[21]
乾隆中晚期,许多朝廷官员倚仗权势,大肆聚敛艺术品,影响了北京艺术品的鉴藏与交易风尚,如有平定大小金川之功的名将傅恒位高权重,“朝野上下争相馈问”。他直言“凡以四王、吴、恽书画馈我者受之,他则否”,结果“斯语一出,而四王、吴、恽书画为之一空”[22]。可见,权贵之好对京师艺术市场的影响之大。乾隆帝宠臣和珅的收藏富甲天下。嘉庆四年(1799),其家产被查抄,所藏古玩仅次于内府,约值八亿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受贿、购买等交易形式带动了艺术品的流通,促进了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着全国的艺术品市场。
清中期,北京艺术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贾云集。南方商人更加活跃,极大促进了艺术品的生产、鉴藏与交易,其中尤以扬州盐商财力雄厚,且与官员联系密切,在书画流通方面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重要藏家安岐著有《墨缘汇观》。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唯嗜古今书画名迹以自娱。每至把玩,如逢至契,日终不倦,几忘餐饮。自亦知其玩物之非,而性之所好,情不能已也。迨后目力日进,南北同志人士往往谬以余能鉴别,有以法书、名绘就政于余者,鬻古者间有持旧家之物求售于余者,以致名迹多寓目焉。[23]
这段史料清晰表达了商人出身的安岐对鉴藏的热爱。安岐结交各地士商,得到了京师名臣纳兰明珠的庇护,在扬州和北京的鉴藏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两地的市场经营。商人投藏家所好,登门精准营销,反映出当时书画交易方式上的承前启后。
乾嘉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于考据辨伪,赏古、玩古之风盛行,涌现出一大批金石学著作,如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孙星衍的《京畿金石考》、阮元的《积古斋藏器目》等。学术研究与鉴藏互为依托,古铜器、玉石、碑版等艺术品的市场需求量显著增加。无论士庶,多以古为贵。[24]这促使更多商贾转而从事古物搜求、交易,以投文人之所好。于是,古瓦、陶器、钱币、铜镜、印章、封泥等受到关注,价格陡增。在利益的驱动下,仿古作伪技术广泛传播,造假手段多种多样,仿品、赝品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北京艺术品交易品类增多,市场规模扩大,经营方式更趋专业化,交易量和交易频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北京商业区域面积在清中期已逐步扩大,正阳门附近的大栅栏、东华门外附近的灯市口,以及东四牌楼、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花市等地店铺相对集中,从事艺术品经营的商贾大多汇聚于上述街巷。清中期,琉璃厂发展为北京的艺术品交易中心。周广业在《过夏杂录》中记述了乾隆中晚期琉璃厂的状况:“正月朔至十七日,琉璃厂市集最盛,书画、珍玩、花木俱在火神庙。百戏杂物,在厂桥北隙地。”[25]纪昀、钱大昕、朱筠、翁方纲、罗聘[26]、桂馥、黄易、孙星衍等名士都曾慕名至琉璃厂购求艺术品。[27]
除了相对集中的艺术品交易市肆,专营艺术品的店铺也渐次出现。早在康熙十一年(1672),琉璃厂就出现了专门经营文房用品的松竹斋(按: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28]乾隆中期,因修撰《四库全书》,琉璃厂专营古籍、书画或文房用品的店铺相继出现。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徐扬绘制完成的《乾隆南巡图》中,也可见临街售卖书画器玩的店铺。
就这些相对对立且专营艺术品的商户而言,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北京艺术品交易专业化程度得到了提升,艺术品经营的分工变得更为明确。同时,古玩店铺由分散到集中、由流动到固定的转变,也显示了北京艺术品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交易空间。北京艺术品市场的格局至此已基本形成。
道光以降,清朝国力日渐衰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北京艺术品市场却逆势而兴,成为晚清国内艺术品交易中心,声誉日隆,名扬海内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内府所藏古物珍宝大量流散,流通于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商品数量激增。随着内忧外患逐渐加剧,晚清帝王已经无意于鉴藏,故私人收藏更加活跃,沈太侔在《东华琐录》中记载道:
京师诸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推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未几,盛司成有重刊太学石鼓文之举,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骎骎乎,观兰台之盛事矣。[29]
晚清士人的思想觀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总体上更加务实,这与朴学、实学的推行不无关系。思想转变后,他们在艺术品市场的参与度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一批博雅好古、精于赏鉴、收藏丰厚的权臣藏家涌现出来,其中陈介祺、潘祖荫、翁同龢、沈树镛、李文田、吴大澂、王懿荣、盛昱、端方等人极具代表性。他们与古为徒,对艺术品鉴藏近于痴狂。翁同龢曾为购得王翚的《长江万里图》而不惜“典屋易画”。盛昱为五更购书,于厂肆旁“时时襥被住宿”。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曾寄银票请王懿荣“代求有风雅事物数品”[30]。

彼时的文人士大夫已经养成了购藏艺术品的习惯,将“阅市”作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日不间断,如文人缪荃孙在《琉璃厂书肆后记》中提及“旧友日日来厂者:朱子清、孙铨伯、黄再同、沈子培、子封、徐梧生”。显然,“阅市”“游厂”已成为当时北京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阅市”时,士人广泛参与艺术品交易,与艺术品经营者联系密切,如祁寯藻、翁同龢、潘祖荫、克勤郡王、徐郙等权贵还亲自为琉璃厂古玩店题写匾额、楹联,提升了古玩店铺的知名度,帮助其树立起经营“品牌”,极大推动了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同时有益于打破由来已久的士商藩篱。不少名儒显宦甚至作为“中间人”,为商家、藏家牵线搭桥,助力于跨区域交易网络的形成,增进了北京与山东、陕西、江苏、江西等地的商业联系,使艺术品的流通量和流转速度得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书画家、僧侣、工匠、小商贩、太监、盗贼等尽皆参与到艺术品交易当中,极大地丰富了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的样貌。
同一时期,来华洋人驻留京城者亦显著增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品的重要买家。加拿大人福开森从光绪十二年(1886)起在中国生活长达60年,其间主要居住于北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不仅擅长书画、古器物鉴定,而且参与了中国艺术品的国际交易。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他在琉璃厂购买古物运往美国,还曾将两江总督端方所藏青铜禁售予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31]此外,日本商人、藏家在北京也十分活跃,尤好收藏名画法帖。[32]宣统时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多次在琉璃厂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中国古籍。[33]外来人士的赏鉴趣味、购藏目的不同于国人,他们的购买力较强,出手大方,收购量大,且多不辨真伪,带有“扫货”性质,给国内市场交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打破了长期形成的议价规则,无形中抬高了青铜器、瓷器、丝织品等艺术品的价格。交易品类、数量、频次、价格的变化对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少高古器物的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刺激了仿品生产,扰乱了市场秩序。不过,外来因素的介入和刺激对中国艺术品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流通体系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晚清部分洋行在从事中国艺术品贸易的同时,组织手工艺人生产适应海外需求的玉器、牙雕、景泰蓝、雕漆、京绣、地毯等北京传统工艺品。这些工艺品畅销于欧美地区,还在国际博览会上斩获了奖项,[34]促进了海内外艺术品市场的互动、联动,有利于传统技艺的推广。
晚清北京的艺术品经营区域较之清中期进一步扩大,琉璃厂、隆福寺、打磨厂、阜成门内、东华门内、杨梅竹街等均设有艺术品商户,其中专业化程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仍为琉璃厂。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艺术品集散地之一,琉璃厂市肆林立,图书充栋,宝玩填街,蜚声海内外。[35]面对琉璃厂的交易盛景,时人曾感叹道:“人至此间,目为之眩。”[36]在当时,琉璃厂的艺术品数量庞大、品类繁多,以至于“每入一店,披览竟日,尚不能尽” [37]。从朝廷名宦到市井百姓,多以“厂肆闲步”为乐。
同治中兴时期,晚清政府的财政与社会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一阶段,北京古玩店铺数量稳定,一些代表性店铺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冀商祝晋藩1832年开设于琉璃厂东街的博古斋擅鉴定、重信誉,经营有方,于1865年至1944年间先后设立笔彩斋、茹古斋、大观斋等13个分支机构,形成“博古斋门系”。晋商李诚甫开设的德宝斋创办于咸丰元年(1851),擅于青铜器鉴定、营销。[38]总体而言,同治、光绪年间开设于琉璃厂经营书画器玩的店铺既有综合性的,又有专营某一品类的,[39]可谓各有所长。它们在竞争与合作间共同促进了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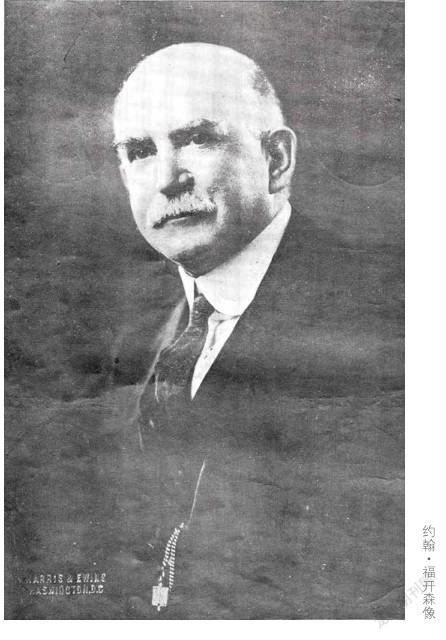
同治、光绪年间,艺术品交易门类更加丰富,以往不被重视的器玩不断流入市场,这成为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繁荣的首要表现。罗振玉在《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便提道:“……若封泥、若饼金、若三代陶登、陶量,若范金、陶土之梵象,皆前人所未见。而近三十年来,若明器、若珧骨、犀象、雕镂诸器,若殷墟甲骨,若竹木诸器,则又道、咸诸贤所不及见也。”[40]自清末实行“新政”后,铁路、公路等现代建设工程在全国各地陆续推进,不断有古墓、古建筑遗址重见天日,大量文物出土并流入市场,如陇海铁路汴洛段修造时首次大规模发现的唐三彩陶俑也现身北京市肆。
当然,古代书画、金玉铜瓷等传统经营品类在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中仍旧占据了较大的比重。琉璃厂店铺所经营的字画“为大宗售品,土地祠、火神庙皆悬挂无余地” [41]。汉唐碑拓、宋明刻帖、元明清书家真迹等亦备受晚清文人士大夫推崇,《宋拓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二册、《宋拓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册、沈周《游张公洞图》卷等古代名迹均曾于晚清市场中流转。不过相对而言,明代以前的作品因历经社会变乱而存世量有限,故晚清流通的名家之作多为“四王吴恽”的作品。从翁同龢到恽毓鼎等文人士大夫藏家大多爱重“四王吴恽”,这对民国时期的北京书画市场有着直接影响。至于书法作品的交易,则受到清代书学的影响。自清中期起,碑学逐步兴起。经康有为等人提倡,崇碑抑帖的风尚形成,碑刻拓片交易逐步兴盛。在北京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精于碑刻传拓鉴定、营销的高手,与推崇汉魏名碑的书家、金石学家形成联动,引领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碑拓交易。在当时,宋、明拓片炙手可热,甚至残损拓片也在市肆中销售,仅凭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北京艺术品交易的繁荣。
文人继承乾嘉考据学传统,潜心金石学研究者甚众,这也促使了古器物鉴藏较之以往更加兴盛。潘祖荫曾言:“同治辛未、壬申年间官农曹,以所得俸入尽以購彝器及书。彼时日相商榷者,则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涛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无日不以考订为事,得一器必相传观,致足乐也。”[42]古器物交易量、交易频次因需求增长而得到进一步提升,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虢叔钟、虢季子白盘等重器还曾先后通过北京商人完成交易。高古青铜器价值连城,尤其是铭文数量多寡成为定价的重要依据。当时京师藏家的购买力较强且慧眼独具、长于营销,于无形之中推动了青铜器价格的提升。[43]

晚清艺术品市场中交易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是陶瓷器。历代名窑瓷器及仿品在整个晚清艺术品市场中所占份额远超其他器物,其中明清景德镇瓷器,尤其是御窑精品瓷器的市场地位十分突出。晚清文人鉴藏秉承宋、元、明鉴赏传统,最珍重汝、定、官、哥等宋代名窑器物,且“以汝为冠”。自晚明已出现的“贵华贱素”倾向愈加显著,加之受外国藏家偏好的影响,钧窑瓷器异军突起,时有“钧窑无对,窑变无双”之说,带紫红斑窑变釉瓷的价格不断攀升。明清官窑瓷器普遍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重视,其中永乐、宣德青花,成化、万历彩绘瓷,康熙素三彩,雍正、乾隆粉彩、珐琅彩等为海外藏家所珍视,被大量购藏,流向国际市场。古陶瓷的供不应求在北京艺术品市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仿古瓷数量因此成倍增长。北京古玩商除去往各地收购外,还利用旧白瓷在北京制作“后加彩”,真假同体,以假乱真。带古文字的古陶器则颇受金石学者关注,然而真赝难辨的高仿品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光绪年间,张之洞曾在琉璃厂海王村古董店见一巨型作古陶瓮,误以为真,只因对瓮上铭文极感兴趣而不惜以二千金购得。[44]作伪行为的猖獗也反映出当时北京艺术品市场需求的激增和交易的繁盛。
随着北京艺术品交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公开化、专业化、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行业分工的愈加细化,出现了更为专门化的店铺,如主营书画的松竹斋、博古斋、论古斋,主营瓷器的德珍斋、崇古斋、赏奇斋,主营玉器的英古斋、大观斋、青山居,主营铜器的德宝斋、通古斋、尊古斋,以及专营印泥等文房用品的清秘阁等。[45]为适应外籍人士的艺术品购藏需求,北京还出现了主要向外国人兜售古董的“洋庄”,如开设在狗尾巴胡同的瑞记、德兴斋、明古斋、欣元斋等。[46]琉璃厂的论古斋、永宝斋在清末曾与美国藏家弗利尔进行书画交易,不少中国古代书画被运往美国,成为后来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主要藏品。与上述古玩店铺协同发展的书画装裱店、锦匣纸盒店等作坊商户也集中于琉璃厂及附近街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产业链。
从经营主体来看,晚清北京古玩商的身份日趋丰富,身份地位、专业水平与文化修养显著提升。一方面,北京古玩商精赏鉴、知收藏、懂经营、好学术,提升了晚清北京艺术品经营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晚清文人“弃儒就贾”“士商相杂”较之以往明显增多,[47]士商得以合流。精通诗、书、画、印的文人士大夫广泛参与艺术品交易,亲自开办古玩店铺,成为“古玩儒商”,琉璃厂博古斋的创办人祝晋藩、德宝斋的经理人刘振卿等皆为个中代表。[48]亦有部分朝廷要员、地方官吏出资开办古玩铺,并聘请行家作经理人,如光绪年间新民府知府陈昔凡(陈独秀叔父)在琉璃厂开设崇古斋,请张鸿儒代理经营。清末内务府总管文索聘请赵佩斋经营其名下大观斋。
“在商言商”的同时,“古玩儒商”并未背离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做生意“讲信用,重礼节”成为北京古玩经营最重要的特点。曾任职大理寺卿的古玩商赵汝珍于所著《古玩指南》中谈道:“昔时外官之一切京中应酬,全由古玩商代办,非特价值不争,即原物亦不能亲见,如不信义,能有人托办乎?”[49]赵汝珍所言“信义”在晚清权臣藏家顾文彬与论古斋长达二十余年的书信往来中尤为显见。[50]顾文彬不仅通过论古斋来代购书画,还会以赊账的方式来达成交易,这正表明了古玩铺与士大夫之间是互相信赖的。琉璃厂的多数古玩店铺对从业者管理严格,要求其不仅要具备鉴定、营销等方面的业务能力,而且要知书达礼。当时的一些古玩商铺还提出了自己的经营口号,如博古斋的“以学养商,不卑不亢”[51]、德宝斋的“以诚为本,与古为徒”[52]、论古斋的“以客为上”[53]等。这些举措推动了古玩行业的良性发展,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获得了名公巨卿以及文人的认可与赞许。[54]在儒商的调和下,士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彼此尊重,相互依存,提高了艺术品交易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能够持续繁荣的“思想基础”。
晚清北京地区的古玩商经营管理有方,有效地抑制了偷盗、欺诈等行风,避免了恶性竞争,在维护市场秩序、树立行业信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持市场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在业务能力上,北京古玩商通过长期实践,已形成较高的职业素养,部分古玩业的行家甚至博古通今,鉴定能力令文人士大夫刮目相看,“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55]。一些身份显赫的朝臣乐于同古玩商人交往,甚至向他们请教,如端方曾因同僚嘲讽其不懂金石之鉴别[56]而“遍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与宜古斋掌柜李云从朝夕讨论,[57]三年后终得精鉴之名。松竹斋的张仰山、博古斋的孙虞臣、德宝斋的李诚甫、尊古斋的黄濬、论古斋的萧佐甫、德珍斋的赵沧涛[58]等经理人更因学养深厚、举止得体而被士大夫赞为“市中风雅者”。潘祖荫、翁同龢、叶昌炽等与古玩商亦师亦友,以鉴真辨伪、把玩金石为乐。这一批学养深厚的古玩商在经营中发挥的纽带作用是以往牙侩、驵侩、掮客、掌眼等交易中介难以比拟的。他们在艺术品经营方面承前启后,对北京艺术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以琉璃厂为代表的晚清北京艺术品交易场所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和海内外藏家,也聚集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品商人,其中除北京本土商人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外,河北、山西商人的地位也极为突出。冀州人有着“幼而读书,长而经商”[59]的传统。晚清时,全国各省几乎都能看到冀商的身影,尤其集中于资源充沛、经济发达的北京。[60]咸丰年间,琉璃厂曾被称为“冀州一街”,论古斋、隶古斋、茹古斋等知名古玩铺均由冀商创办。冀商还通过“引荐子侄”的方式安排同乡进京谋生,比如“衡水帮”在古玩业中闻名遐迩,其中萧秉彝、萧维邦等人颇有声望。太平天国后,冀商在琉璃厂已取代了江西商人的地位。除冀商外,晋商也为数不少,德宝斋、英古斋、永宝斋、寄观阁等均是咸丰至光绪年间由山西人开设的古玩铺,时称“山西屋子”[61]。晋商以乡邦文化为根基建立自身的商贸体系,晚清德宝斋、英古斋等古玩铺在雇佣伙计时“限于山西人,他省之人不得授用”[62]。经营过程中,冀商与晋商还通过多种途径结成鉴藏交易网,互相帮衬,彼此制约,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信誉。
晚清江南商人在北京古玩行业也占有一定比例,影响力非同以往。光绪、宣统年间,部分上海商人往返于京沪,经营书画等艺术品,海派书画社团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63]于北京谋生的江南商人在乡邦文化的驱动下,快速组建自己的“熟人圈”,在乡邦内部建立起“商业信用体系”,共享商业资源,共担风险。
晚清北京古玩铺的销售方式多样,除店铺展销外,精准营销、登门求售为多数商家采用的方式,这也更符合士大夫藏家的需求。接受卖家寄售、买家定制的方式亦被广泛采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无论身份地位高低,均不再讳言价格,而是公开讨价还价,尤其晚清随着古玩商地位的提升,他们开始在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即便面对名公巨卿的鉴定议价也能据理力争。

为招徕顾客,北京古玩店的装潢大都非常讲究。为迎合文人士大夫的品味,其中一部分商铺的内部环境如私家庭院般古雅怡人。对此,我们依据文人笔记中的描述可了解一二:“旁有古玩店,余购数器,因得觇其铺后花园,以盆植香桃及各种鲜花,罗列殆满。中一玻璃缸,水满其中,蓄鱼数十头,长约一指,色如真金。”[64]《陶雅》作者陈浏曾作诗《因忆茹古斋所得石》:“英石自来声作铜,横逾五尺起三峰。似闻箫竹销沈后,拖入蓬莱小院中。”[65]松竹斋等店铺则在店内分设柜台,前柜服务一般顾客,后柜接待贵宾。一些店铺还设置了客房,备有餐桌、床榻、暖炕。清秘阁中还设有更衣室,方便官员下朝更换便服。文雅幽静的环境使得晚清北京古玩铺不仅作为艺术品展陈之地,而且成为京师文人雅集的场所。曾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常至琉璃厂、报国寺“阅市”,不仅购买书画、古籍,也于古玩店铺汇聚友朋、商讨政事等。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他常光顾的古玩铺达29家。[66]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大观斋掌柜赵佩斋任会长,这标志着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北京艺术品市场经历了清中期的全面发展,至晚清空前繁盛,在清末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学养深厚、亦士亦商的经营者群体崛起。在他们的探索下,不同的市场形态衍生出来,适应了不同阶层、身份购藏者的需求。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整体的交易规模与专业化程度远超明代,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东西文化的交流。因此,清代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对20世纪中国书画、古器物的流通以及国际艺术品市场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刘毅.从金石学到考古学——清代学术管窥之一[J].华夏考古,1998,(04):87-96.
[2]李一鸣.清初北京地区绘画鉴藏与交易探微[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13.
[3]参见清代冯鼎高修、王显曾编纂《乾隆华亭县志》卷十五,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第324页)。
[4][清]吴其贞.书画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57.
[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
[6][明]蒋一葵.长安客话[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674.
[7][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四[M].汪政,注.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86.
[8][清]談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8.
[9][清]梁诗正.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藏一四[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0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
[10][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M].邵彦,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1][清]高士奇.江村书画目[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十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329.
[12]吴明娣,常乃青.震古烁今——清代陶瓷鉴藏及交易考略[J].中国美术,2019,(02):143.
[13]赵连稳,乔婷.清代三山五园地区的买卖街[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74.
[14][清]姚元之.竹亭杂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5.
[15]梅松松.晚清(1840—1911)文人鉴藏活动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22.
[16]张荣.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八辑[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133.
[17][清]曹雪芹.红楼梦[M].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89-990.[18]同注[17],1316—1317页。
[19]同注[17],369页。
[20]曹雪芹笔下的薛家当铺“恒舒典”开设在“鼓楼西大街”,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该当铺位于北京。
[21]吴明娣.谁解其中味——论《红楼梦》与鉴藏[J].美术研究,2020,(06):56-62.
[22][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7.
[23][清]安岐.墨缘汇观[M].郑炳纯,审定.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4:4.
[24]张勇盛.阮元的金石鉴藏活动述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03):102.
[25]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7.
[26]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91—1792),罗聘尝携其子允缵寓琉璃厂观音阁,应故旧翁方纲邀请,至翰林院作画,后又参加乾隆帝主持的“千叟宴”。
[27]吉少甫.中国的琉璃厂和日本的文求堂[J].中国出版,1991,(10):61.
[28]辜鸿铭.清代野史·第7辑[M].成都:巴蜀书社,1988:201.
[29][清]沈太侔.东华锁录[M].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170.
[30]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1][美]聂婷.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旅华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西士的中国艺术发现之旅[M].郑涛,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156.
[32]同注[27]。
[33]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J].敦煌学辑刊,2017,(04):176.
[34]吴明娣,主编.百年京作——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
[35]蔡大鼎.北上杂记[M]//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编委会,编.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第22册[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104.
[36][清]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82.
[37]佚名.燕京杂记[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121.
[38]李特.晚清(1851—1911)北京琉璃厂德宝斋古玩铺艺术品经营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39]论古斋长于书画营销,尊古斋主营青铜器、印章,清远堂则专售明清官窑瓷器。
[40]罗振玉.雪堂藏古器物目录(外五种)[M].罗继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41]同注[36]。
[42][清]潘祖荫.说文古籀补序[M]//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北京:中华书局,1988.
[43]李特.德比圭璋 与古为徒——晚清民国(1851—1945)德宝斋古玩铺艺术品经营初探[J].美术大观,2019,(9):60-62.
[44]吴明娣,常乃青.震古烁今——清代陶瓷鉴藏及交易考略[M]//吴明娣,主编.中国陶瓷史专题研究.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9:382.
[45]吴明娣.清代北京古玩市场考略[M]//艺术市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8.
[46]刘泊君.清末民初西方人在京购藏艺术品的主要场所研究[J].美术学报,2015,(05):75-83.[4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32.
[48]祝晋藩出身书香世家,家境富裕,古物收藏颇丰,鉴定眼力超群。由于其家世、学养、见识不同于一般古玩商,所以博古斋能以学养商,树立良好的经营风范,受到同行和鉴藏家们的尊重。刘振卿原为山西襄汾进京赶考的举人,在功名无着继而进入古玩行后仍醉心学术,“昼则应酬交易,夜则手一编专攻金石之学,尝著《化度寺碑图考》” 。他还曾得到翁同龢的赏识。
[49]赵汝珍.古玩指南[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9.
[50]参见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和苏州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日记》。
[51]胡军玲.晚清民国琉璃厂古玩经营研究——以博古斋及其衍生机构为中心[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52]同注[38]。
[53]白宇.晚清琉璃厂论古斋书画经营状况研究[J].美术大观,2020,(09):84-86.
[54][清]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M].王淑敏,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50.
[55][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九[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98.
[5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二辑·杶庐所闻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84.[57]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59.
[58][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3.
[59]河北省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冀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85.
[60]杨昊.冀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以北京琉璃厂旧书业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5):154-160.
[61]同注[43]。
[62]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613.
[63]单国霖.海派绘画的商业化特征[M]//单国霖.画史与鉴赏丛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40-244.
[64]邓云乡.红楼风俗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5:350.
[65]参见清代陈浏《寂园丛书》十二种之《斗怀堂集》第4册(铅印本)。
[66]戴婷婷.翁同龢艺术品鉴藏及交易研究——以《翁同龢日记》为核心[D].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