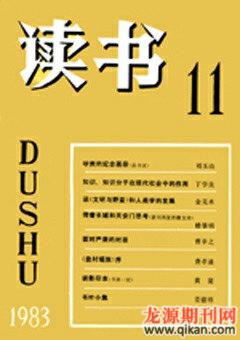《达尔文年谱》和它的作者周邦立
黄宗甄
一九八二年三月,为了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达尔文年谱》一书。
这部《年谱》约四十万字,附有照片、航行地图和插图五十余幅。它搜罗了有关达尔文的丰富资料,逐年逐月逐日加以编撰,其内容不仅包括达尔文的家族和家庭环境,童年生活,求学经历,进行环球旅行和科学考察的始末,而且也包括了他的科研和著述情况,家庭经济,朋友往还,以及身后的哀荣。达尔文一生绝大多数重要著作和论文的写作过程,他晚年与疾病作顽强斗争的动人事迹,《年谱》都根据可靠的资料一一记述,并附有不少原稿手迹的照片和初版书扉页的版样。对于达尔文与他的朋友们的交游,如与他的挚友赫胥黎、莱伊尔、霍克等人的书信往还等,《年谱》也作了详细记述。它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这位大科学家谦冲恢宏的风格气度和谨严的治学作风。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与达尔文这两位科学巨人间的一段交往。一八七三年,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曾把它寄赠给达尔文,并在该书的扉页上亲笔书写了“查理士·达尔文惠存。诚挚的敬仰者卡尔·马克思。一八七三年六月十六日。”达尔文为此特向马克思复信致谢。《年谱》刊载了这一复信的原稿。
一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开了进化论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本来是由宗教势力和保守分子发难,意在一举摧毁达尔文学说而举行的。当时达尔文本人因患病与全家正在外地休养,未能出席。代表他的,是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及霍克等人。他们痛斥了牛津主教等的无知妄说,挺身而出保卫进化论。在会议进行的三天中,赫胥黎以他锐利的词锋,杰出的辩才,渊博的学识和谨严的逻辑,击败了宗教顽固势力的围剿。经过这次短兵相接的论战,达尔文的学说由“异端”而逐渐成为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真理。《年谱》不仅详细记述了这一激烈的论战和斗争,而且还刊载了赫胥黎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珍贵图片。
由于编著者的辛勤搜集,这部《年谱》还公布了不少国内过去有关书刊从未发表或语焉不详的宝贵资料,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枚述。
正因为这是一部内容翔实,资料新颖可靠,文笔生动感人的《年谱》,而且又是在国外从未出版过同样性质的著作的情况下,由我国首先出版的,因此,它一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很大反响。初版本六千册,数日内即告售罄。现居英国伦敦北白金汉郡的达尔文的孙女爱玛·诺娃(巴洛爵士夫人),已经九十八岁高龄了。她曾经编辑过许多有关达尔文的书籍,如《达尔文旅行日记》、《达尔文和贝格尔舰的旅行》、《达尔文回忆录》等,当她拿到这本《达尔文年谱》时,激动不已,欣喜异常,为此特意寄语编著者和中国人民,表示她由衷的感谢。《达尔文参考手册》的编著者、英国伦敦大学动物学教授弗里曼,获悉此书的出版后,多次给《年谱》的编著者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件,表示赞扬和激赏。他把《年谱》送到伦敦英国博物馆及其他学术机关和图书馆陈列和珍藏,并亲自为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撰文,介绍本书的出版。考虑到读书界的需要,科学出版社又重印了此书。
这样一部著作,说来也许人们难于置信,却并非出诸国家科学教育机关的教授或研究人员之手,而是由所谓“社会闲散人员”的周邦立编著而成的。
周邦立出身贫苦,少年时刻苦向学,就读于苏州中学。抗战期间,他考入当时由竺可桢教授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甫进校门,他便加入了学生进步团体“黑白文艺社”。其后,更经受了抗战的洗礼和浙大民主精神、求是学风的熏陶。他的英文和德文修养原来就较高,入浙大后又努力学习俄文,通晓了三国外文。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最初所译的都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浙大毕业后,他又业余从事苏联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四十多年来,他翻译和写作了近一千五百万字(主要是翻译,也包括一些著作和文章)。其中已出版的十万字以下的书二十六种,十万至四十万字的十六种,四十万字以上的七种,还有与别人合译的二十种,共计六十九种。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译稿,在各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有二百六十篇以上。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周邦立做出的贡献是惊人的。
在周邦立的翻译著述生涯中,他对于达尔文这位科学中的伟大革新者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三十多年来,为了翻译达尔文的各种著作和编著《年谱》,他广搜博辑有关达尔文的资料。所有达尔文的原著,也包括这些著作的俄文版和中文版,他差不多都阅读过。达尔文的日记、书信及各国专家学者对达尔文的研究和评论,他都反复披阅,予以摘录,并编制了大量卡片。在编撰《年谱》的过程中,遇有疑难,他不惮烦难,屡次写信向英国研究达尔文的专家弗里曼教授请益和核实。正因为他半生致力于达尔文的研究和他著作的翻译,因此有关达尔文的生平及国外的研究情况,甚至达尔文的一些软事,他都十分熟悉。攀谈起来,如数家珍,具体而微。
去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周邦立以毕黎为笔名译注的《达尔文回忆录》。他不仅为该书撰写了《译者前言》,而且还编纂了七个附录。这些附录和注解,既指出了达尔文自传中的笔误和删简之处,又介绍了达尔文所提及的书名、人名、地名和专门名词。特别是那篇译者前言,不仅介绍了《达尔文回忆录》的手稿情况和版本源流,而且做出了一项重要考辨。达尔文的著述中,常有谦词和曲笔,后人不察,每每导致对他的误解。达尔文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看法就是一例。过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就曾在这一点上对达尔文予以贬斥。周邦立则根据印数极少、连生物学专家也很少去研读的林奈学会《会报》上达尔文的一篇论文,指出达尔文对马尔萨斯结论的反证,对过去流行的误解做出了订正。仅仅从这一本书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周邦立在研究和翻译达尔文著作中所付出的劳动和凝聚的心血。
周邦立之被投闲置散,并非由于政治上的错案,而出诸他本人的自愿,但和政治上的原因亦不无关系。他本来在机关中有正式工作。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他在工作上积极努力。但后来随着“左”倾思潮渐次袭来,给周邦立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苦闷和矛盾。他是惜时如金的人,渴望着为人民多做工作。经过反复思虑,他终究还是下决心申请退职,做了职业翻译工作者。除了十年浩劫中被迫搁笔外,多年来他就在沪上的斗室之中伏案著译。他尽管生活困难,工作起来仍然效率高,出活多。他在生活上自律甚严,虽然有时稿费收入颇丰,但他却总是粗茶淡饭,衣履简朴到甚至有些破烂的程度。但是对于一时有了坎坷遭遇的朋友,他却从不吝啬,总是慷慨解囊,济人急难。
作为“社会闲散人员”,周邦立无法领到图书馆的借书证,因此他只能在馆中仓促浏览,不能借阅书籍携归研读。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研究条件未免太差了些。他只好拜托在京沪和其他大城市的朋友辗转代借。打倒了“四人帮”,河清海晏,祖国又有了希望,周邦立这个“个体户”,何尝不想重回科学文教机关,有个正式工作,有个起码的工作条件呢?不久,某大学聘请他做特约编审,每周到校一次,给该校科技情报人员讲解翻译理论技巧和解答难题。他高兴的去了,工作虽然还是临时的,他却可以领一张借书证,从此借书有方了。但后来因为人浮于事,临时工并没做长,借书证又被吊销。就这样,他始终未能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始终未能取得一张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借书证。
周邦立一家五口,住在不到二十平米的两间亭子间里。屋子里到处堆满书籍,连要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稿纸也要煞费苦心地巧妙布局。子女们都大了,晚上要做功课,他只好把桌子让给孩子,自己在双腿上架一块木板,或者把棉被折叠起来当做桌子来写作。直到夜深人静,儿女们都睡了,他才能坐到桌子前继续挥笔著译。三十多年来,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还是在浙大读书的时候,因为周邦立生活素朴、体格清瘤,同学们都称他为“甘地”。到了晚年,生活的煎熬,工作的艰辛,更使他形销骨立,老同学们相聚总禁不住又回想起他青年时的这个称呼。
一九八二年四月,周邦立作为达尔文著作的翻译家和研究者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后,南归沪上。不久我忽然收到他的来信,说他已确诊为肝右叶癌症,正在努力与病魔抗争。信是由他儿子代笔的。我在震惊之余,又不能不联想到以他的处境求医之难。事实也真是这样,直至逝世前一星期,靠了好心邻居们的帮助和疏通关系,他才住进了医院的急诊室。但是一切都已晚了。确诊后不过一个月,他便溘然长逝。由于没有所属单位,所以他身后是寂寞的。同年九月,我们在京的四五十位周邦立生前的老同学和老朋友,自发为他举行了一次悼念会,悼念这位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而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翻译家和科学工作者。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许多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像周邦立这样有名的翻译家,带有我国知识分子的很多突出优点,在“社会闲散人员”中可能还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希望在开发我们民族的智力资源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