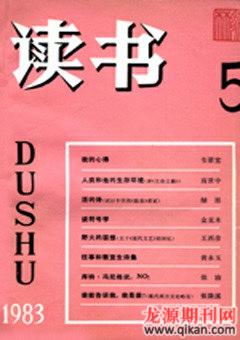旧京风土入画图
端木蕻良
我和羽仪论交,已有四十几个年头了。今年他恰满八十高龄,仍在孜孜不倦地作画,《旧京风土画集》就是他最近完成的作品。羽仪是名画家王梦白的私淑弟子。他擅长花卉,兼善山水。他的画和吴待秋、陈师曾等画家的作品,在早年都曾被荣宝斋刻制水印版画,作为艺术信笺发行。鲁迅和郑振铎合作的《北平笺谱》,羽仪的画笺,认为是长于小品的佳作,也为他们所赏识和选用。
羽仪早年留学美国,毕生从事铁路技术工作。基于爱国热忱,对工作奋力以从,对祖国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浓厚的感情。在工作余暇,便借画笔抒写情怀。他的画,纯出自然,不雕不饰,情趣盎然,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澹泊、真实。
当桂林这座八桂名城被誉为“文化城”的时候,羽仪为湘桂铁路建立发电厂,也来到了这山水胜地。当时和他往来最多的有柳亚子、田汉、熊佛西、尹瘦石、陈迩冬、李白凤等人。这些朋友,有的是诗人,有的是画家。后来徐悲鸿也来到了桂林小住。他的到来,应该说给桂林带来了一次诗画的热潮。在那些日子里,连熊佛西也变得手痒,画起画来了。那时我故意给羽仪出点子,找一些过去画家很少画的冷门来和他为难,如画猪、画乌龟等等。可是羽仪毫无难色,即席挥毫,神情毕肖,连悲鸿先生也为之击节不止。
羽仪久居北京,对旧京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更加深了对北京的怀念。他寓居牯岩(电厂所在地),当他把几间老屋修建为客室时,特意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并按照北京习惯以重彩油漆柱梁门窗。他说,要使八桂风光,京华情调兼而有之。为此亚子先生把客室命名为“春明馆”,以示对沦陷的故都的深切怀念(北京一名春明,中山公园有春明馆)。羽仪为绘“春明馆图”,并请亚子先生题诗以为纪念。此画在辗转流徙与十年动乱中,幸得保存无恙。成为当时幸存下来的仅有的珍贵纪念品。
我和羽仪一样,也把北京作为第二故乡,对于有关北京的图画艺术,总是深感兴趣。陈师曾当年的《北京风俗画》,今天还依稀记得;对泥人张当年捏作的泥人,所表现各色人物的生动形态,也都记忆犹新。有一天,我和羽仪闲谈旧京往事,话题便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了。我很希望他对这方面能有所贡献。羽仪说:他早在一九三四年间,曾在收藏家陈汉第家中见到他向梁思成借阅的陈师曾《北京风俗画》共三十余页。当时认为旧京风俗可以入画的题材,还远不止此,因此起了续作之想,并且还试画了几张。可是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于七七事变前夕他离京南下,风俗画续写只得停止下来。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完成这宿愿的机会。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学习过人物画,因而有些踌躇。我笑着对他说:京剧有反串,作画亦未常不可。如陈师曾以花卉著称,人物似非所长,但他以写意笔法所作的风俗画,别有一种韵味,我想你也可以做到,希望你在这方面能做出贡献。因为我认为旧京风俗既有民族学的价值,又有社会学的价值。历史是不应割断的,实际上也割不断的。我们如果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对看,就更能了解当时汴京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风土人情的风貌,这可能远远超越了他们原来的意图。我之所以极力鼓励羽仪把风俗画继续画下去,其意实在于此。果然,羽仪听了我这番话后,深受感动,便兴致勃勃地画了起来。
现在,羽仪的旧京风土画已积有百幅,从各方面表现了旧京的风貌,其中有不少幅是描绘旧京低层社会小市民的悲辛劳动与苦难生涯以及封建迷信陋俗。在这些方面作个今昔对比,不仅对新一代有所启发,就是对来京旅游者,也是一种贡献。当人们看到这个画集时,不啻看到了故都的三百六十行,不啻又听到了旧京的货声和市声……,加深人们对于新中国的认识,不啻读了一本活的旧京风土史话。
羽仪对于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画册的形式,印象很深。陈画是由他的朋友马公愚等予以配诗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能配上诗句,出版社也有同样要求。从我和羽仪几十年的友谊来说,应该说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为风俗画配诗,谈何容易。我确实缺乏桐花芝
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