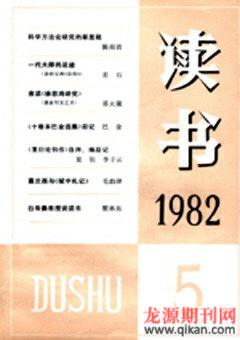评陈汝衡新著《吴敬梓传》
蔡国梁
近年来有的同志感叹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可算个大作家,在胡适五六十年前编写了《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之后,新材料也发现了不少,可是,四五十年来,只见单篇论文和资料汇编,却不见有比胡适更系统更丰富的《吴敬梓传》和《年谱》问世。”现在陈汝衡教授新著《吴敬梓传》的付梓,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要求与期待。
陈汝衡先生为吴敬梓立传的想法由来已久。从他一九三九年《大晚报》“通俗文学”栏发表《儒林外史研究的新资料》起,到本书成稿为止,也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其间关于传主的生平,在《外史》以外他的一切诗文著述,他的文学活动和交游状况,不论系今人发掘还是他翻检图书所见的,都加以记录排比,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料。从这些第一手资料出发,陈先生构成了自己的观点,对传主有了系统深入的认识。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为吴敬梓作传的强烈愿望终于实现。在历史的催促与文坛的渴求下,箸者怀着为有志写作者铺平道路的志向,完成了这部十二万字的新传。据我管窥所得,新传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钩稽史料,据实叙论。新传共计七章,各章的内容较为充实,可以看出著者的功力。如第二章“青少年时期的学养和生活”,胡适的《年谱》仅列其诞生前后十年艺苑文坛的某些大事,新传则加增益:引金榘的《泰然斋诗集》刻划其童年学习八股文情况;引吴湘桌的《外史》序指出其多方面的写作才能,从“才大眼高心细”的赞语中可以测其创作这部卓越的现实主义杰作所具备的才华,特别指出他具有较高的散文水平,并不受桐城派囿囚,“横发截出”,自有活力;引江宁黄河序《外史》语,谓其诗“如出水芙蓉,娟秀欲滴”,“至词学婉而多讽”,用清辞丽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鲁迅先生评论他的小说有内在的一致之处;引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说他遍读各家注疏,“莫不抉其奥,解其纷,猎其精英”,著有“醇正可传”的数万言的《诗说》……这些都为他峭然成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九月间在北京保和殿举行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吴敬梓没有去,究竟是因病还是装病?第四章“定居南京时的交游和活动”针对胡适摭取唐时琳《文集》序而提出的“他的病是真病不是装病”的论点,列举六条文献资料,据理而辨。这六条,程晋芳的传和《金陵县志·人物志·文苑传》未提吴的病,《国朝金陵诗证》、程廷祚序虽提有病,却不曾说明真假,只有金和的《<儒林外史>跋》中的“先生坚卧不起”一语颇可玩味,是说装病不起。特别是陈汝衡先生在抗战中发掘、向为文学史界重视与引用的顾云的《
“一首老伶吴祭酒,几篇乐府白尚书。”新传又补叙传主的佚诗《老伶行》,并以王又曾十绝句之七为线索,指出吴敬梓尚有几篇象《白氏讽谕》一类的诗佚失有待发掘。又从他为老伶工写诗留念,谈到他很关心戏曲音乐,为李本宣的传奇剧本《玉剑缘传奇》写过序。第五章“在扬州和真州,以迄逝世”谈到他曾为经学和金石家江昱的《尚书私学》撰序,以及论述他在全椒、南京、扬州、真州的广泛的交游(其中不少是《外史》中儒林群士原型,有的对他的思想有积极的影响,如和论文乐友的程廷祚,即《外史》中庄征君的原型,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
谱年立传,联系创作。以往的文学家传记有的偏重于排列其身世经历,有的详述其创作成就,而本书则以传为主,就传而评,将谱年立传与创作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人们考察《外史》的成书提供了方便。考证作者生平家世,是为了研习作品。文学史上第一流作品最能反映创作规律,因而新传在这方面的用力有助于我们窥探艺术创作的真谛。著者在历叙传主的家世时,就有意识地指出它对创作《外史》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著者据传主津津乐道的高祖吴沛(《移家赋》说这位“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的宿儒,“贫居有等身之书,干时无通名之谒〔宁国太守以书召,谢不往〕。”),说他嗣后反科举的见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比胡适仅仅列举家世、铺叙门第深入了。吴敬梓的为后人所知是因为他的不朽名著《儒林外史》,所以著者很注意从他的出身和经历里挖掘此书的创作思想的由来,在各个章节里不断地点拨、提示、议论。新传要读者注意一个出身于地主剥削家庭、大官僚贵族的后裔,怎样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怎样从生活实践中经历了艰难奋斗的曲折过程,才从一个自幼蒙受儒家教育(包括程朱理学在内)和八股制艺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反程朱理学和反科举制度的。吴敬梓从功名进取的道途上遭逢挫折,财产耗尽,经历生活上的煎熬和痛苦,认清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才促使他要把自己所憎恶的形形色色的脸谱勾划出来,同时也把他志同道合、衷心钦佩的一群人,不管是否在儒林之内或儒林以外,都收在他庄严的笔底下。胡适早就指出:吴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当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八股的气焰又大盛起来。这正是吴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时代,它的价值正在这里。新传论述了由盛而衰的康雍乾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他无例外地受到流毒既深且广的八股的熏浸,他在《外史》十一回里描摹鲁编修和鲁小姐这类典型的八股迷决不是偶然的,有它特定的历史内涵。而一个自负才高,以为指日可以飞黄腾达的人却弄到二十三岁才进学,二十九岁科考遭不幸,同年秋闱乡试又告失败。这一系列刺激,必然加深他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但是吴敬梓不是范进。一连串不幸,终于使他于愤世嫉俗的斗争中转变成为奋发有为的一名文艺战士,画出了不朽的儒林百丑图。新传以娓娓动人的笔触诉述了传主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实践,结合当时的环境和风气历叙其创作动机的孕育,阐明《外史》的主题与成就,辨析他如何突破局限与囿于局限。
此外,新传不断联系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启发读者思路,提高读者的鉴赏力。在谈到南京友好时,特地提及迂腐拘执的马二先生的原型冯粹中。《外史》描述公祭泰伯祠盛典时曾给此人以“三献”的位置,让他主持最后的礼节,很重视他。著者从他《国朝金陵诗证》的一首《西湖归舟有感》绝句,联想到第十四回借马二先生去杭州选书机会烘托湖光山色,使读者换一下新鲜空气,效果颇好。新传引述《
著者并没把这位讽刺文学家偶像化,他尽力遵照求实的原则反映传主的复杂性。低回往复,摇摆波动,在前进或后退的道路上充满着矛盾,中国进步的文人大多如此。他们年轻时追求功名,积极进取,获嫉受挫后,或放浪形骸,或效法陶潜,或发愤著书,吴敬梓即属最后一类。著者提到他参加了鸿博的省试,作过两篇赋、三篇试帖诗,其后虽因滁州科岁考蒙试官之辱,以及因科举种种弊端、与试者的排斥谤誉而“以疾笃辞”,未赴京廷试,但事前事后却徘徊踯躅。“人生不如意,万事皆坼坼。有如在罗网,无由振羽翮。”(《丙辰除夕述怀》)哀叹自己不能有司马相如、董仲舒的非凡际遇,功名在身,青云直上,胸中交织着愧悔之情。新传毫无隐晦地指出,“一直到三十六岁岁杪,他还没有多少进步可言。庸俗无聊,书空咄咄,和一般封建文人没有什么不同。”待第二年落第名士,纷纷回南,他庆幸自己,作《美女篇》以寄意,谓参加廷试的绩学之士如富家美女不获君王顾视,以汉皋神女自由解
新传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是熟谙资料怎么与理论上的建树、开拓有机结合,使材料上的广度与理论上的深度统一起来,以及个别地方的论据是否充足有力,有些课题的论断是否公允合理,也有待学界研讨争鸣、发掘补正。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陈汝衡教授曾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戏剧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目前虽已八旬余高龄,仍耕垦不息、挥笔不休,继《说书史话》后又完成这部面貌全新的吴传,它必将引起文学史家的兴趣与学术界的欢迎。我们期待着他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进一步地修改此传,并盼注他另外的新著问世。
一九八一年一月初稿,国庆改毕。
(《吴敬梓传》,陈汝衡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0.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