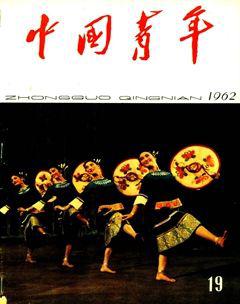电水车
程裕祯
今年春天,父亲来信说:“家乡很旱,麦子点火就着,刚出土的秋苗也半死不活。县委正采取紧急措施……”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已经给乡亲们造成较大的生活困难,今年的夏收又没指望,怎不令人心焦?我盼着暑假快来,好回去看一看。
从北京到山西太谷,沿途千里,碧绿一片,年景显然此去年好。临近故乡,白塔在望,贴着玻璃窗向外看,不禁使人大为惊奇:肥沃的晋中盆地竟如此苍苍郁郁,绿里透缸,一派丰收景色!我扪心自问:旱象何在?
下了火车,离村还有十里路。田野里,电线纵横、交织如网。不时传来山西梆子“打金枝”的唱腔。走不多远,迎面碰上邻家的保成叔。他是我们生产队瓜菜组的组长,今天和一个叫贵娃的进城卖菜,一见我,连忙停下菜车。我问他们:“你们好啊?”
“好,好!今年都好。”保成叔说,“麦子大丰收,十几年来都没有过。秋庄稼也等着咱社员最后笑哩!”
“不是旱吗?”
“旱?”贵娃插嘴说,“给咱赶跑了!”
刚见到乡亲,他们就这么高兴,话也说得这么硬朗。我算放心了。但同时又升起一团疑雾:丰收是怎么得来的?
“春天是旱来着。”保成叔说,“正因为旱,咱才和老天爷斗!怎么个斗?咱县委想到电!你知道,咱这儿的电去年就从太原拉过来了,可惜没有大用起来,电力水车也安了几部,但太少了。今年就不同,公社买来了不少水车。不怕旱得早,只要县委抓得早。刚见旱象,郭书记就在公社跑来跑去,要咱立即动员起来,挖井修渠,安装水车。不到半个月,咱这儿远远近近都安上了。白天黑夜,突突嘟嘟,给咱的麦子喝了个足。赶到麦收,你说怪不怪?一亩地打了三百多斤。连麦穗顶儿上的那一粒也都饱乎乎的。电水车,真顶事哩!”
为了赶早市,他俩拉着平车走了。我独自回家。父亲在菜园里看菜。我走去一看,果然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过去,瓜菜园这一带叫西旱地,根本不能种菜。零零落落,只有一眼半眼辘轳水井。可是现在,能触眼看到的,就有十几部电水车。有不少藏在庄稼里,用时才能听到响声。菜园里盖着两间草房,算是生产队的田间办公室。父亲就住在这里看菜。要用水,只要一拉电闸,突突突就冒上水来。父亲说:“咱这儿哪,只差煮饭不用电了。”
下午,我就留在菜园里劳动。这几天,又有点旱,二茬茄苗又该浇水了。我拉开电闸,那水,活蹦乱跳地窜入地里。父亲说:“老天爷再旱,咱也不怕了。就靠咱这电水车,高梁、玉米都长得这么壮实,秋后哪有不丰收的!电井,电力水车,过去想也不敢想。还是公社家大业大力量大。你听后生们唱什么:“不是公社化,这几年的庄稼打不下;不是电力水车,今年难得好收成。”
真的这样,电水车给家乡带来了丰收,给乡亲们带来了喜悦。然而,电水车是公社带来的,一家一户单干时连想也不敢想。如今,乡亲们想了,做了,也完成了。无怪乎他们一说起今年的丰收来,话就那么硬朗,而且总带着一个“咱”字。这个“咱”,我想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正是正在成长壮大的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