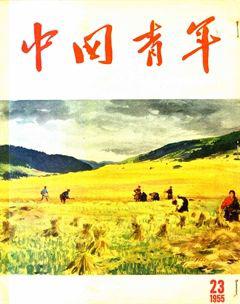关于学生和工农结合的问题
韦君宜
中国青年社要我写一篇纪念“一·二九”二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是今天的知识青年怎样与工农结合。据说:有些学校学生和机关青年干部,怀疑自己要去和工农结合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有可能?编辑同志提醒我,对这些青年,似乎应当说明:第一,与工农结合的问题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因此,这对于做任何工作处在任何条件下的青年都是一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也还是应该尽可能到工农中间去。
我想,关于第一点,那当然最重要。毫无疑问,在立场上,我们应当为工农群众服务,应当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从工农群众的利益出发,应当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工农化。即使你整天坐在机关里打字、算帐,难得见到工人农民的面,那也还是为工农服务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人服务,这对于一个革命青年是比其他一切思想修养问题都更重要的根本立场问题。这一点,在这篇短文章里不想详细谈它了。我想单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除去要坚定立场之外,一个革命的知识青年是不是还有必要到工农中间去?
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这是“一二.九”运动里的一个口号。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情形和那小时候当然大不相同。第一,在那时候,知识青年的阶级出身很少是工农,很多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与工农结合,这包含着一个阶级变化的意义,包含着离弃本阶级,投向另一阶级的意义。可是现在不同了。中等学校的工农子弟的比重巳经有极大增长;有些工农青年已经踏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在机关、部队、工厂里,工农出身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更是很多很多了。第二,在那时候,知识青年是没有与工农结合的自由的。那时候要去与工农结合的青年,都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一二.九”运动中,一个人去不去农村,常常就代表了他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时候,反动统治阶级为知识青年所安排的出路就是为反动派服务,青年不肯按这条路走,不为他们服务,要去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这就表示了青年的革命觉悟。现在可是不一样了。现在一个学生从高等学校毕了业,国家就会把你分配到适宜的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岗位上去。不用你担心。一般知识青年,国家都是唯恐你不肯为工农服务、不肯与工农结合。只要你好好服从国家分配,那是不必发愁自己为工农服不上务的。
照这么说起来,在今天,知识青年和工农结合、到工农中间去的问题,不是就不大要紧了吗?
这却不是。我想,其实是更要紧了的。正因为今天我们的前途确定地是要为工农服务,所以更必须和工农密切地结合。更必须力求了解工农,接近工农,了解工农的劳动,也了解工农是怎样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不单是从理论上知道工农是领导力量、是主力军就够了,还要实际上去熟悉这些人。如果自己要去为些这象服务,但是对服务的对象却不认识、不了解,服务对象对于自己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这怎么可以呢?这几年,在屡次的政治运动中我们也看到,学生的政治热情是高的,但是每逢运动的内容不是直接关涉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例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团的组织和报刊的编辑部就一定接到大量的学生来信,问:“我又不是工农,这个运动和我有什么联系呢?我怎样能从这里面学到些东西呢?”这样要求联系的心情是好的,但是这种情况却也说明了原来的缺乏联系。需要联系起来至于怎样做法,自然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办法。但是,不论怎么说,像目前存在的学生虽然在理论上大致都认识了要为工农服务,在实际生活上却长期和工农相当隔绝的现象,并不能说是好现象。事实上,许多高等学校的学生进学校好几年,不到生产实习的时候,是见不到工农的面的。一提起工农,虽然满腔热情要去向他们学习,但是对工农实在了解太少,去学习的时候老仿佛是从自己生活的这一个世界跑到另一个生活的世界似的。甚至有些青年原是农民子弟,上了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之后,回到农村,也和农业劳动疏远了,和叔叔大伯疏远了。一拿起锄头,人家就笑:“是洋学生。”(多少篇开于初中高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通讯都记载着这种现象。)其实,那里是什么“洋”学生呢?不原来就是土生土长的,我们自己的学生吗?这种情形已经被许多同志批评过。但是我们不依当专等这些学生已经出了学校门回到农村去以后再去批评,应当先就想些办法。
我想起前几年我去参观过一次苏联,曾经到一个集体农庄去访问农家。看见一个集体农民的儿子,就在本农庄所办的中学里读书。他白天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就常常跟生产队下田。(学校下午两三点钟下课,生产队那时候还没有收工。)到年底他也挣了不少的劳动日。他是一个中学生,同时又是一个集体农民。当时我心里就想:人家这样来解决和工农结合的问题,解决得多好!这个人毕业以后如果要从事写作,他就不会像我国的文学工作者那样要重打鼓另开张地下去体验工农生活了。(他如果要体验生活,会是另一种体验法。)劳动南下宣传团向老乡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批学生,脱下长袍,穿上军装,向延安进发。
观点的问题,自然也跟着解决了。现在我国的学生要做到这样,自然还有许多条件上的困难。但是,我们总还是应该尽量使青年们在学生时代就能常常和工农接近,因为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学生和工农已经不应该有什么人为的界限。
在“一二.九”时代,学生去接近工农,那种接触当然是非常不够的。但是,在学生运动中间特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却是值得珍贵的。请愿示威之后,党批示我们,马上抓紧了下乡宣传。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来之后,马上抓紧了长期的民众学校工作。我记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在办民众学校的工作上是花了不少力量的。清华附近各村庄的了众学校都是我们创办的。从清华附近的成府一带、前后八家村、宝福寺、挂甲屯,一直远伸到清河。在清河镇除创办了民众学校,还帮助清河织呢厂的女工建立了读书小组。现在的学生们,功课很重,需要把功课学好;和那时候的革命学生以干救亡活动为主丢下书本的情形,当然有不同,当然有不同。但是,现在的学生也还是要进行社会活动的,把这些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按说也还是可以行得通。在社会活动里,除去报告会朗诵会之类以外,更着重这些使学生学习社会、接近工农的活动,该是会对学生更有利的。譬如要六七个学生共同教一个扫盲班,一个学生一星期抽出一小时时间去教一教,应当不是太难的事。此外,譬如逢秋收的时候去帮助农业合作社收割,平常组织一组学生和一个固定工厂固定车间的工人联欢,常常在一起郊游,让每个学生有机会认识几个工人朋友,这都是不难办校班级的数量太多,即使这些人统统是群众观点特别强,推开虽的工作来为同学们服务,也还是没有可能完全满足所有各校学生的要求的。我们何不更多用点功夫在和工农接近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