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私观”视角理解中国农村集体
刘闯 秦彩凤 续志琦
内容提要:本课题从“公私觀”与中国农村集体、生民及生民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了讨论。(1)关于“公私观”的认识。中国思想史中“公私观”具有丰富的伦理价值内涵,并从“立公灭私”主流认识逐渐转向包容和承认“私”的一定合理性。(2)“公私观”视角从不同维度体现并影响中国农村集体实践,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乡里政治与信仰和仪式、乡村经济、乡村“会”等。(3)关于生民及生民社会。生民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体现在生民社会的民间合作机制,对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视自下而上的生民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自2023年起,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研究组设立了“中国农村集体原理性研究”项目。研究项目试图在农村集体研究的领域,搭建起从历史中国延展至现实中国的内在的原理性连接的桥梁;试图探究中国农村集体的本源性,即现实中国的农村为什么会演绎生成以村庄集体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单元?中国今天的村庄集体的成因,并非完全来自当代政治意志,更不是回归人民公社体制,而是在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脉络中逐渐演成的特殊的文化基因、适应当代社会变迁和发展需要的结果。
研究团队试图证实如下的理论假说: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和释放发展潜力的根基来自中国农村集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组织发展实践,这正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演进所凝结的特殊基因逐渐体系化而形成的中国原理的一种映照。研究从两个视角出发:一是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中形成的“公私观”在土地、人口、伦理、信仰、政治等维度的表现;二是现代以来乡村演进中的组织化历程。回答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形成农村集体这样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乡村组织化特征?探索其间的中国道理,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为未来几十年的乡村振兴战略构筑坚实基础。
关于“公私观”的认识
“公私观”视角是当下学术界探究中国农村集体本源性所缺乏但非常重要的视角。关于“公私观”的认识,中国社科院孙歌教授认为,“公”和“私”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强调了“私”的群体性和族群性,以及个人行为和欲望在“公”领域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需要验证并解释伦理空间的“公私”边界。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则指出,1949年后的国家建设不是基于传统的“公私观”模式,而是更接近日本的“公私观”模式,这表明中国的国家建设更加灵活,并且与日本、德国、苏联等的国家观念有相似之处。
现有文献研究也对中国的“公私观”有着丰富的表达。梁启超和严复在近代对公私观进行了理论重构,梁启超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而严复的公私观带有浓厚的近代西方色彩,强调“公”是来自个人利益的集合。晏阳初在民国时期提出从乡村建设入手拯救中国的思想,强调改造人、培育“公民”作为首要任务(宋恩荣,1989)。台湾学者陈弱水(2006)则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将“公私”概念的内涵归纳为五种类型,从政治社会概念到道德上的善恶对立。费孝通(2005)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公私的相对性,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已”为中心的差序结构。金耀基(2013)看到公私在行为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日本学者沟口雄三(2011)在探寻中国“公”观念起源时发现,“公”概念衍生出了伦理上的意义,包括公正、公平等。
总的来说,中国的公私观念历经古代到现代的演变,逐渐从传统的“立公灭私”转向更为灵活和包容的理解,这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化。
中日“公”“私”观的比较
在探讨中日“公私观”的差异方面,孙歌研究员提供了深刻的文化比较视角。在中国文化中,“公”的概念深植于伦理和自然性,其边界模糊、富有弹性,且“公”观念与“均”“平”概念紧密相连,这反映在儒家思想和历史变迁中。例如,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提及父子之爱本质上属于“公”,但涉及私心时即成为“私”,这种观念的流变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态性和伦理的深度。相较之下,在日本的文化中,“公”观念则表现为一种空间性和权威性的概念,不涉及深层的伦理性。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公”的理解:即使国法有不正不便,也不会因此被破坏,这反映了一种相对刚硬和明确的公私界限。
在“私”观念上,中国文化中的“私”在伦理体系中带有负面含义,其空间边界不绝对确定。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个人权利最初是没有位置的,同时皇权的“大私”受到指责。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逐渐将“私”与“己”分离,确保小民之私的正当性,如吕坤在《呻吟语》中提出的“万物皆有所欲”。与之相对,日本的“私”则缺乏伦理性,不具备道德上的负面含义;其空间边界明确,从属于“公”,体现为一种服从关系。
此外,孙歌教授还提到,中日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异源于各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日本,公共和私人空间是严格分离的,如在日本机场个人随意使用公共设施,民众会斜眼相看,这反映了日本文化中民众对“公”空间边界的理解。而中国人的“公私”观念则表现出更为灵活和具有伦理性,如家族和村落中的议事规则。郑振满教授则补充指出,中国的“私”其实在空间上是相当明确的,但其表现形式和理念与日本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分家文书、家族公共事务和财产权利的规定等,均体现了公私界限的清晰性。他强调,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府对民间授权的态度,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深入理解。
总的来说,中日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异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国的公私观念具有较大的弹性和伦理深度,而日本的观念则较为刚硬和明确。这些差异不仅深刻影响了两国的社会和文化,也为我们理解各自的历史和现代社会提供了关键视角。
“为己之学”与“天下为公”
从儒学视角中的“为己之学”与“天下为公”理解中国人的“公私”观。吴重庆教授对“己”与“私”的概念进行区分,指出“己”在儒学中是一个中性词,而“私”则具有负面含义。他强调,在儒学中,“为己之学”意味着从个人出发,逐步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是个人从“小我”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大我”的过程。孙歌认为儒学中的“己欲”和“私”是分开的,克己复礼中要克的是“私”,不是“己欲”。实际上,儒学的一个隐含线索是强调尊重生民的欲望,此时“公”和“私”连贯在一起而没有冲突,共同构成了“成人”的过程。
关于“天下为公”的概念认识,吴重庆认为它与“为己之学”是天下的自然状态,而政治秩序是一个自然秩序。儒家与道家在天成秩序观这点上是一致的,而朱子将这种自然的一面带入国家的伦常或伦理秩序中。同时,贺照田强调中国人表面看似自私,但内在具有一种能推广到更广泛领域的结构性元素,而围绕“己”的认识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之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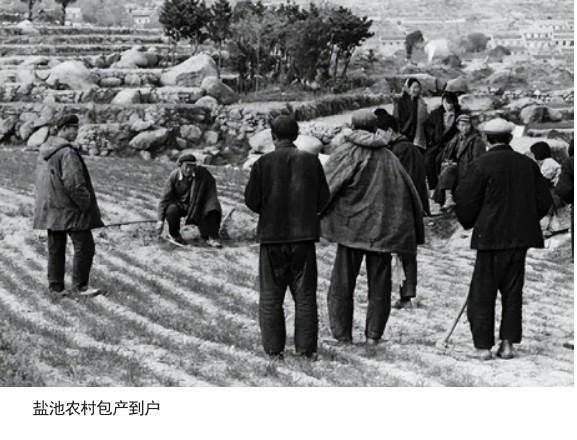
总的来说,儒学中的“为己之学”并非纯粹的自利行为,而是指通过个人的内省和自我修养,逐渐扩展到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层面。这种从内在出发的自我完善过程,最终导向了“天下为公”的理想状态。这一过程强调了个人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揭示了儒学对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
“公私观”视角与中国农村集体
从“公私观”视角理解中国农村集体的内涵与价值,这是当下学术界新的重要探索方向。中国的“公私观”在土地制度、乡里政治与信仰和仪式、乡村经济、乡村的“会”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其变化影响着中国农村集体的生成与演变。
土地制度
一是土地保护制度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和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稳定。土地对乡村社会而言具有多重功能,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土地保护制度建设,以维护乡村社会农民权益与基本生存伦理。吴重庆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土地既被用于农户生产粮食,也被用于支持办理村社民间各种“会”的活动功能。现今要让土地“活”起来,但土地应当掌握在农民手里,不应把农民的土地卖掉或私有化,否则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历史上,农民因家庭变故或危机把土地彻底卖掉,一般要经历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有人乘人之危把农民的土地买断,其名声会受影响。郑振满认为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保护制度也存在内在选择机制。比如过去老地主分家时坚持要留一些财产,主要是因为他明白守住土地的唯一办法是集中经营,只有土地集中经营才利于解放劳动力和实行内部分工管理。历史上,福建省农村公田变得越来越大,有的农村公田达到60%以上,包括祭田、书田、役田、香灯田、神明会会田等。杨团研究员认为,当下国家实行土地“三权”分置,并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体现,尽管很多农民已不种地,甚至抛荒土地,但从长期经济发展考虑,让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有份的土地制度设计具有战略意义。
二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需要进行拓展创新,不能将研究局限于“产权”视角。刘志伟认为,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私”观念,是不可能有产权概念。中国乡村民众对土地的执着与“吾民无地”(文贯中,2014)的产权视角说法是矛盾的,但两者又是统一的,而这种对立统一从古代到现代都是一以贯之,用现代产权概念去定义土地国有或私有是不适用的。我国宪法中没有承认土地私有,但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农民会毫不含糊地坚持“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的信念,甚至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农民也坚持此信念。杨团研究员认为,从先秦井田制到明清时代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有公有私,不是简单地讲“吾民无地”。西方以私为本的一套价值观、伦理观体系支撑了产权制度。用西方产权制度解释中國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着局限性。刘志伟认为,除秦代有《田律》外,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地法》,《唐律》《明律》《清律》等法律跟土地有关,但都没有关于产权的界定,其条文背后包含了某种原理性、结构性东西。如果从事法学的人回到中国本身的发展去研究,可能会有新启发。
乡里政治与信仰和仪式
一是乡里政治的维持离不开信仰和仪式。刘志伟认为,村社和乡里政治不能分开,比如四川省有的地方恢复“保甲制”,即建立网格制,但是其有效落地还得通过乡里乡约。村社的背后实质上是乡约,但是乡约必须扎根村社整个系统,不是条文写得好听,老百姓就会接受。当下,有些农村的年轻人继承传统,主动组织乡村的“会”,比如延续乡村婚礼的传统仪式。这利于保持乡村的团体性。
二是农村传统纽带利于延续存在的传统仪式。吴重庆认为,在珠三角地区,农村传统延续相对较好,当地农村的经济社(村小组)是以过去生产队为基础组建,生产队基本上是由同一条巷子的村民组成。这样的经济社筹钱修宗祠,村民会很齐心。
乡村经济
一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乡村“公共财”,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发育成长。杨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是推动社会发育成长和乡村经济发展。吴重庆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培育可以结合。
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赋予村民对村集体财产共享的权利。杨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股份,陈锡文在解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时明确指出,这是集体组织成员对共同拥有的资产的个人份,它只是资产利润分红的根据,不能作为股份买卖和抵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起到了保护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让集体资产经营起来,让集体和农民真的能够结成公与私相互依存、共举共融的共同体,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极少数的村庄能够像战旗村那样地维系着“公私兼顾”的村集体发展道路。吴重庆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珠三角地区有农村又经历了一次土地归到集体。当时,为了便于香港商人来村里租地建厂,村集体在经过所有村民同意后,以土地股份制方式重新集中土地,打包出租给香港商人建工厂。
乡村的“会”
传统乡村有各种“会”,比如桥会、路会、神会、庙会等,它们依赖于村社民间组织来运行。郑振满认为,因为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有限,需要依赖民间自身力量供给,明代以后基层社会出现很多“会”,比如各地的宾兴会最开始是以科举的名义资助科举考试,后来发展为士大夫管理的公共基金会,主要由商人和地主负责款。江西的宾兴会实际上是地方大家族的联合基金会。刘志伟补充,民国时很多宾兴会逐渐演变为地方政府财政局的功能。同时,郑振满认为乡村的“会”大部分跟公益慈善事业有关,但是集资和救助背后有受益者,捐款人可以限制捐款适用的人群范围。由于捐款是个人行为,因而这很难成为一个社会机制,不是现代社会的“公”,现代社会的“公”是一层一层的。刘志伟教授也认为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的“公”不是面对全社会,是有边界性、地域性和人群性特征,享受互助的人得有成员资格权。
关于生民及生民社会的讨论
生民的概念
生民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吴重庆,2022)。 “生民”和“仁政”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两个脉络,孙歌认为生民主要指民间的相互救助,从生民的脉络讲,所有的生民就是天之民,受天的佑护,天大于王朝。这样的观念从始至终一直存在,而且这与生民的伦理、生民的欲望、生民的均平要求一致。吴重庆认为生民的概念从政治和经济分析,有两面性,在政治动荡时凸显其革命性(例如历朝历代动荡时的替天行道口号),强调了社会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垂直的君臣关系。同时生民也指社会众生平等、财富均衡流通分布,但不是每人平均分得一份。刘志伟认为,“生民”与“食货”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一体(其中盐铁论时期的矛盾最为典型)。中国历史似乎一直在这种矛盾与一体的状态中不断发展,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才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打破,但这肯定是暂时的。生民的概念决定了国富和民富应是统一的,其概念最早可能源自《诗经》和后来的《周易》,它的逻辑表明天生之民会构建国家和君主的统治,而这一逻辑在中国古代经典中通往国家体制的建立,并塑造了君主的德和仁政等概念。贺照田教授认为,士大夫群体对生民观念与一般民众和王朝的生民观念可能存在差异,需要深入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生民”概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有现实基础,研究基层村干部的动机有助于在中国的传统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
生民社会及其民间合作机制
合乎天理人情的“私”欲望在生民社会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孙歌分析了吕坤关于“私”的主张,强调欲望符合天理人情,天理人情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因其伤了生之道,依靠“均平”可以让天地得到最好濡养。同时,她举例京剧《锁麟囊》中富家女把装满金银财宝的锁麟囊赠给躲雨相遇的贫家女,在五六年后,富家女遭遇大水而流落到员外家当保姆,又凭借锁麟囊与当年贫家女也是现今员外的夫人相认并结拜金兰。这个故事暗含了中国特有的民间生活的经济理性,即积德行善并非单纯的善举,也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投资,暗含了为应对将来可能遇到的灾难预先投资的共识。这一模式源自王朝治下生民不得不自救的社会结构形态。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善堂善会,建立了以村落或家族为单位的自助自救机制,行善具有社会性公共价值。
但是,中国生民社会的民间合作机制在清末开始衰落。孙歌认为,中国民间以相互扶助为基本机制、以均平为理念的生民社会主义,在以辛亥革命为顶点走向了结构性瓦解。当时,为了自保而组织的地方团练变成了瓜分领地的军阀,这导致中国社会的混乱和消耗,以及外敌入侵时无法有效抗衡。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在某种程度上重建和接续了瓦解的生民社会主义,但不是直接的接续,而是一个断裂性的接续。
同时,孙歌通过与日本社会的民间扶助机制比较,发现中国社会的民间机制更强大。在日本社会,相互扶助仅限于个人行为。除特定非常时期之外,相互扶助不具有公共价值。以日本关西大地震与中国汶川地震中政府和社会的营救差异为例。在关西大地震中,大阪和神户两个大城市高度地震,日本政府花了3天时间讨论要不要出动自卫队,结果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被耽误了。民间也没有任何动作,过了很久后才开始发动捐款。日本人一般认为灾难救助要靠保险公司,没保险的人有很多选择了自杀。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行动很快,民间行动也很快。可以看出,日本的相互扶助是一种个人的善举,依靠的是个人的伦理观。而在中国,相互扶助不仅是善举,而是社会机制的重要部分支撑着百姓的生存方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机制的功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与中国人的传统和历史直接相关。
生民社会中民间合作机制的特征和演变
生民社会的民间合作机制特征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一是过去形成的基于血缘的人情合作机制在农村社会依然存在。郑振满教授认为,普通人获得的支持大部分来自“私”领域。20世纪90年代,他在全国十几个省调查显示,70%-80%的受访对象获得的支持来自传统社会网络,来自“私”领域,而获得的现代各种机构的支持很少。二是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新的集体合作和动员机制。贺照田教授认为,差序格局所强调的越推越弱的同心圆状态不能完全描述社会现实。例如,1948年費孝通在去西柏坡的路上,看到农民推着点着灯的小车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形成大规模共同行动的状态。另外,抗美援朝中的亲情动员方式,激发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同时对朝鲜人民的苦难建立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三是农村大集体时期基于村民共同劳动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吴重庆认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共同体如果能够再赋予、植入或者发展出情感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则集体的生命力更强。现今,推动中国农村集体发展,需要更多思考乡土性、情感成分注入等问题。仝志辉则认为,集体化时期村社就是伦理共同体,生产队长跟社员之间讲平等,讲风气正,在同甘共苦中形成集体的情感联系。
此外,农民进城后,乡村传统的合作机制发生迁移,说明乡村振兴的价值可能会以在城市合作的方式体现。郑振满认为,不能狭隘地看乡村振兴的价值,关键是能否把乡村记忆重新激活,而不是一味关注乡村能否长期存在。中国传统乡村“集体”的最核心价值是民间集资动员机制,然后是合作经营,而这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重建乡村集体可能会在城镇化发展中推动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