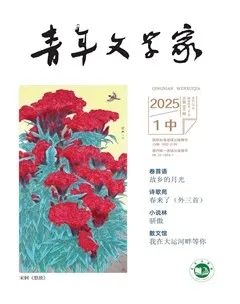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汪曾祺散文中昆明书写的生命体验探究
由于受抗战的影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最后迁移到云南昆明继续维持办学。京派作家代表人物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昆明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中生活了七年。生命体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空间是感知生命体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蕴含了生命的丰富多样性、存在的真实状态以及生存所承载的深远意义。昆明独特的气候通过物候触发了汪曾祺的生命意识,涵养了他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文学生命,使其呈现出独有的文学风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汪曾祺《水流云在》)。因此,汪曾祺在昆明时期的在场的生命体验、文化审美、美学表现,以及创作时的“心灵场”等都与昆明这一地理空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是他对昆明产生地域依恋的重要原因,作品也因此有着大量关于昆明这一空间的文学景观的书写。
“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学事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它的研究对象,概括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等,是20世纪80年代“空间转向”以来发展的文学批评的产物。本文从文学地理学的视域出发,通过探讨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自然人文地理中的气候和物候,分析它们对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影响,感知其生命体验;同时,利用区域比较法对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书写进行探究,这将对解释汪曾祺对昆明的地域依恋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又从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学景观来领略当时昆明的自然人文、民俗文化,以加强对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的了解。另外,汪曾祺笔下所写的部分景观在当代的消失或是改变,又能引发我们对现代化人类发展困境中必然伴随着失去的思考。
一、昆明的气候、物候与生命意识
气候,“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化”(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文学地理学中,把气候分为自然气候和人文气候,它们同时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按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物候”指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即“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周期性和地域性是气候的突出特点,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昆明这一空间的气候决定着物候。汪曾祺由相关物候变化感知生命时序的变化,从而引发出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昆明的自然气候对汪曾祺的生命意识有着触发作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认为,气候的影响是最初和最基本的,对人有着最强有力的影响,它以物候作为触发的中介。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5℃,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如春,降水充沛,这样的气候特征在全球少有,也使得住在“春城”的昆明人“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很少人家有一个钟或表”(施蛰存《施蛰存散文》)。这样温和的气候对汪曾祺的“生命本体”必然构成影响,使他能够放松下来,获得一种松弛感,能够以一种从容自若的态度来面对处于抗战时期的困难的学习生活,从而让心灵达到一种平衡。即使在草木摇落的秋季,他的生命地理体验却是“只稍为尝出百物似乎较为老熟深沉……白天太阳照着,温暖平和,全像一个稍为删改过一番的春天”(汪曾祺《老鲁》)。同时,在该种气候作用下,被誉为“花城”的昆明的物候又以花和野生菌为主要代表。按时令生长的花和野生菌,是自然生命力旺盛的表征,具有野性生气。这种外部物候触发了汪曾祺的生命审美意识和时序意识,他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花和野生菌,如“昆明缅桂花多,树大,叶茂,花繁。每到雨季,一城遍是缅桂花的浓香”(《昆明的花》),“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到处是菌子气味”(《昆明食菌》)。在汪曾祺的嗅觉和视觉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昆明的花香、菌香、米香、雨香等,这表明了昆明是一座散发自然之气的空间存在,自然之气与昆明小城融融相生,从这一点就能感知到昆明人精神上的那种和谐与融万物。
昆明的人文气候对于汪曾祺的生命意识有着重要的培育作用。法国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精神上的气候”,即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这里的“精神上的气候”就是文学地理学中所说的人文气候。抗战时期的昆明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僻,受战争影响小,仍旧保持着轻灵秀丽之气,但也充斥着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发生的“一二·一”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该运动是我国第三个民主运动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范例,可以说这是搭建昆明人和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桥梁。此外,作为一个多民族汇集的城市,昆明的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人民也十分淳朴热情。汪曾祺与这样一群本地人共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昆明空间中,构成了只属于昆明的社会关系,比如他在散文《寻常茶话》中写道:“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在这个茶馆空间中,汪曾祺既写出了昆明民间去茶馆吃茶的随意和生活的闲适,又写出了昆明人待人和气,处世宽容。这种城市精神和性格对于汪曾祺人文精神的培育是有着重要影响的,脱离战火的纷扰,能够让自我在这一新的空间中得以自适,回归生命的自我,进行生活文化的交流。所以,在拉近距离的精神交往状态下,汪曾祺发现了昆明极具地域色彩且多元的民俗,如铺松毛、耍西山、包清水粽等,他在《昆明年俗》中写道:“昆明有些店铺过年不贴春联,贴唐诗。……初一上街闲逛,沿街读唐诗,亦有趣。”这些风俗人情构成了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人文气候,使得汪曾祺能感受到昆明人即使面对着抗战的局面,但仍然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实现着自我的生命价值,这影响了汪曾祺的生命选择,体现在他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的作品中,它们包含着生存困境背后的生命超然之气。
二、文学景观与在地性体验
“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文学的一种地理呈现”“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既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又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在地性”指作家关于“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由此产生一种独属于这个空间的生命体验感。汪曾祺关于昆明的文学写作大多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创作的,属于在地性书写,其中的文学景观的书写是汪曾祺生命意识下的产物,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感知出汪曾祺的生命体验感,因为景观的情感既是身体的状态,更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另一方面让我们可以透过文学书写从中加深对昆明文化的了解。
自然景观大多以自然风景为题材,既能够在现实中欣赏,又能够在文学作品中欣赏。雨是昆明自然空间和风景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汪曾祺的散文《昆明的雨》中这样形容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值得注意的是,昆明的雨不是江南的梅雨,昆明的雨天是在阳光和雨水的交替中进行的,因此下雨时带来的清凉感受并没有给汪曾祺带来忧郁之感,反而使他的心灵更加纯净与安宁,让他能更加敏感地感受到生命的悸动,比如他感到“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另外一方面,这种天气是促成野生菌疯狂生长的关键条件,又能够满足汪曾祺口腹之欲,比如《昆明的雨》中的“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此外,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决定其属于稻作文化圈之中。汪曾祺在其作品中多次写到昆明稻作文化的产物,即米线和饵块这两个独有的吃食:有全城随处可见的小锅米线,文林街的焖鸡米线、爨肉米线、鳝鱼米线、叶子米线,荩忠寺坡的肉米线,青云街的羊血米线,正义路奎光阁的凉米线,护国路附近老街的干烧米线,正义路近文庙街拐角处一个牌楼西边的过桥米线等;有汤饵块、炒饵块,以及形状略似北方牛舌饼的烧饵块等。可以说,米线和饵块是昆明人最平民化的饮食,一方面不仅供应着人们生物性的身体,也塑造着人们文化性的身体,借由对它们的认同建立起了人际关系的网络和拥有食物记忆的群体,更多的人因为吃米线或是饵块获得地方性的文化认同,得到生理与社会化的具体经验,并且能够传达特定的有关自我认同的诉求,扩大来讲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祈愿心理和价值取向。
人文景观大多以历史建筑作为载体,它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因为“它们不再独自生存,或者仅仅依靠原本的样貌”(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它们与作家后半生所发现的一切彼此融化,如果没有彼此融化,至少也会彼此移植,也就是说,作家在在地性的生命体验中,将自己的生命感受移注到这些人文景观之中。翠湖公园这个人为所造的园林空间,是汪曾祺笔下又一重要的人文景观书写,翠湖之于汪曾祺有着某种特殊情结,他每天几乎都要到翠湖。翠湖中隐藏着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茶馆,它为昆明人提供了一个情感交际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昆明这个城市空间的缩影,极具文化代表性,浓缩着时代和社会的基本形态,这使得作家在茶馆中直接接触到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和人生百态。翠湖一方面成了汪曾祺内心独特的情感连接地:写到翠湖的水不深的时候,他会联想到之前一位因失恋想要投湖自杀却最终投河无果的同学;写到湖水的时候,引发了他的回忆,“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翠湖心影》);写到湖的名字时,他认为“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翠湖心影》);等等。翠湖在汪曾祺笔下形成了独属于他的人文空间。另外一方面,汪曾祺看到了翠湖的社会功能:“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心影》)翠湖公园早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地景意象,作为昆明城市文脉之一,沉淀了悠久的丰富的风景文化历史,这个昆明人共有的公共文化空间,寄存着昆明人的城市记忆,是昆明人表达对过往岁月的想念,对平淡生活的珍视的实物寄托,正如文中所写:“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翠湖心影》)
三、地域依恋与生命记忆
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对文学地理学提出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区域比较法,这种比较属于共时比较,或者横向比较,借用比较文学的概念可以称为“平行研究”,但它不同于比较文学的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它是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比较,而且一般不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它必须用事实说话,需要“实证”。通过比较汪曾祺对其他地域空间的书写,可以发现昆明已经成为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承载着“母亲”的某些功能,是哺育其生命的“子宫”,他曾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表明昆明是他的第二故乡。之所以说汪曾祺作品所建构的文学性的第二空间中的昆明城市空间是昆明战时的一块“活化石”,是因为汪曾祺在这个空间体验生命的过程中对昆明产生了依恋。后来离开所产生的隔离让汪曾祺无意识地产生一种“放逐感”,它使得这种依恋转变形成地域依恋,进一步说地域依恋又是文化依恋的一种表现,“文化依恋是个体与内群体以及文化间建立的情感联系,指向家乡城市的文化依恋为家乡文化依恋,它能够唤起个体的心理依恋,缓冲跨文化适应压力,增加主观幸福感,成为人们在不稳定、危险情况下的情感依托”(周婷、毕重增《地域多文化经验是否会削弱家乡文化自信:文化依恋的补偿作用》)。
在汪曾祺的昆明生命记忆中最凸显的是味蕾记忆,他有许多书写昆明吃食的文学作品。味道具有地域性,能够让人瞬间穿梭回当初的在地性体验。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汪曾祺会“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昆明菜·诸菌》);当西南联大时期校友巫宁坤写信向他要画时,汪曾祺会画上昆明见过的浓绿仙人掌,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当他吃到苏州洞庭山的杨梅和井冈山的杨梅时,他会认为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等等。其次是昆明的花记忆和水文记忆。他在张家口坝上沽源县的街头也看见了波斯菊,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喜。但他觉得塞北少雨水,花开得不如昆明滋润。沽源看见的波斯菊使他一下子想起了昆明,他认为“中国是茶花的故乡。茶花分滇茶、浙茶。浙茶传到日本,又由日本传到美国。现在日本的浙茶比中国的好,美国的比日本的好。只有云南滇茶现在还是世界第一”(《云南茶花》)。他在《翠湖心影》中认为:“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除了昆明,在汪曾祺的情感空间中还有似江南水乡的高邮,处西北塞外的山城,临华北平原的京城,但是我们大都可以从他的其他地域性写作的作品当中看见昆明的身影。这些或许是汪曾祺无意识的区域比较,因为昆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情愫,由此产生了一种地域依恋。他怀着一颗感恩昆明之心体验和审美着昆明,在地域比较中凸显昆明的独特,以表达他对昆明的独特的偏爱。
文学作品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作家当时生活过的地域特征和情境。这些昆明独有的地域空间风貌不仅是汪曾祺后来身体离开昆明,进行精神回忆的依托,它更永存于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空间中,这个空间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诗性空间,总是展现出令人赏心悦目,又别有情趣的风俗形象,呈现空间中所有新鲜的文化,是风景美(如雨后翠湖的柳树)、饮食美(如鸡枞、过桥米线)、情义美(如茶馆中的堂信)、风俗美(如贴唐诗、门头挂仙人掌);而且,随着现代化的城市发展,它也成为老昆明人的空间情感记忆空间,因为那些出现在汪曾祺笔下的昆明的饮食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城市文化格局等,在遭受外力与内力的瓦解下多数已成为昆明的往事,一种历史和记忆的存在。所以,当代作家余斌的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一如20世纪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揭示当时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目的是唤起昆明城市记忆中的地点和城市空间的情感轮廓。而在汪曾祺笔下曾经在任何大街小巷都见得到的烧饵块和菌子,今天在街头早已难觅,除非到专门售卖店或者菜市场旁。记忆的恢复似乎总是很“困难”,但通过某些景观又总能够轻易地被唤起,地点是精神土地深埋的矿层,就像普鲁斯特一样,他清楚的记忆与地方的景观总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昆明这个地点是汪曾祺的一个主观的空间,被他看见过、生活过、想象着、记忆着的空间,是他无意识的“空间部分的投影”(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但是要想窥探老昆明的城市风貌,我们还是可以阅读他的《菌小谱》《昆明的吃食》《米线和饵块》《昆明年俗》《翠湖心影》《跑警报》《职业》《艺术家》《膝行的人》等散文作品,然后借助想象,在头脑中构建出逝去的昆明老城空间,虽然这样或许会让我们产生“景观”消失或被其他替代后迷惘的感受。
昆明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无论身处何方,那份深植于心的昆明情怀总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在他笔下的文字之中。文本这一永恒的时间形式,构建了汪曾祺对昆明这一地域的依恋。总之,昆明这一地理空间以及昆明的经行地的文化对汪曾祺的个性形成和创作文风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也从汪曾祺的在地性书写中看到了昆明的各种地域文化,体会到了他在昆明这一地理空间中的生命体验。另外,面对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不断推进,那些汪曾祺笔下消失了的昆明地理因素,在令我们惋惜遗憾的同时,也能促使我们思考情感记忆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
本文系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省级一般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汪曾祺散文中的昆明书写”(项目编号:S20231068102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