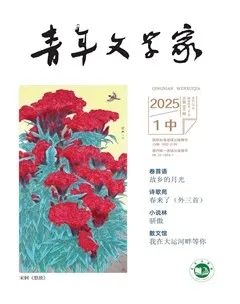沈宜修与徐灿词中的“燕子”意象
《全明词》序言:“千年词史,鼎盛于宋,中兴于清。”清词中兴,实始于明末,明词继往开来之功诚不可没。妇女诗词的创作数量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后大幅增加,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辑录的数目来看,有著作传世的女性共4200余人,而明清有3910人,约占全体的93%。其中,以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母女三人为核心的创作群体代表了晚明的江南闺阁文学最高成就。张仲谋在《明词史》中给予沈宜修极高评价:“明人称道女性诗人,动以李清照作比,实际相去甚远,而相近者当推沈宜修。”徐灿(1617—1698)在女性词史中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清初著名的遗民才女。清陈维崧的《妇人集》言:“徐湘蘋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蓄清照。”可见,徐灿的词足以与李清照并驾齐驱,俯视朱淑真,尤以富有遗民气质,饱含家国情怀,沉郁慷慨,开阔女性词之意蕴。
在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沈宜修与徐灿的词作中,所涉及的“燕子”意象十分丰富,她们书写了雨中之燕、归家之燕、双飞之燕、多情之燕、无情之燕、新春之燕……燕子在她们笔下不仅是生机和谐的自然之物,更是惜春伤秋,依依惜别,或忧国伤时的情感世界的代名词。
一、沈宜修与徐灿词比较的必要性
选择此两位词人进行比较有其必要性。
首先,两位女词人虽处明清不同时代,而生平却十分接近。她们都出身于书香之家,属于闺秀词人,社会身份和人生经历相似,前半生历经欢愉后半生坎坷不平;同时,沈宜修活跃于万历与崇祯之间,徐灿出生只晚于沈宜修二十七载,两人在词作内容和词风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并且,当今从女性词人个体比较角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同一时代,或与宋代最负盛名的李清照、朱淑真相较,而忽略了明清易代之际女词人词风的过渡与发展。
其次,两位女词人的著作代表了当时女性词的最高水平,从她们的词作比较可发掘明清女性词的特质。沈宜修存词190首,存词数量远远超出明以前的任何一位女性词人,是晚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文学家;徐灿更是被称作“足以与李易安并驾齐驱”(陈廷焯《白雨斋诗话》)的女词人,两人前期词风不出传统闺阁风格,不同的是,徐灿后期作品较沈宜修多几分慷慨豪迈之气,开一代风气之先。这背后既因个人心境,更因明清易代的黍离之悲。沈宜修于明末早亡,而徐灿经历了由时代更迭带来的动乱,经历过飘零的生涯。这些经历在两位女性词人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并对她们词作的风格与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将综合比较她们对燕子这种日常家禽的描写,感受两位女词人柔婉清丽中带有刚健苍凉之气的闺怨愁言。
二、沈宜修与徐灿词中的“燕子”意象的含义
(一)情感含义的相似处
在古代诗词作品中,最早提及燕子的作品可追溯到《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讲的是高辛氏的后妃简狄,在吃下燕子蛋后,不久便顺利生下殷的祖先契,因此,燕子也第一次作为祥瑞之鸟被记录下来。生活中,燕子往往筑巢于人们屋檐之下,是随处可见的家禽,具有贴近生活的朴素温情的特点。双宿双飞的燕子还是希望与爱情的象征,具有丰富的感情内涵。
沈宜修与徐灿都是标准的“闺房之秀”,她们认同闺阁典训,身上都有着当时社会对女性规训的修养与气质。因此,她们词作中的“燕子”意象有一些相同特征。
首先,是对她们情感世界长期压抑,困守于幽深孤寂生活的春愁秋感的抒发。沈宜修在《忆王孙·海棠枝上杜鹃啼》中写道:“海棠枝上杜鹃啼,憔悴春光燕子泥,香冷炉烟花影移。柳绵飞,落尽红英水拍堤。”春天莺歌燕舞,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在词人眼中,却多感伤之景。情感上的孤独,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使词人不堪忧愁困苦。因此,当词人看到枝上的杜鹃在啼叫时,眼中的春光只是憔悴。而沈宜修的另一首《忆王孙·云屏寂寂锁残春》更是愁苦:“云屏寂寂锁残春,锦瑟年华已半尘,芳草留香燕新语,绣苔茵,金钿琼箫总殢人。”当词人听到新燕梁间呢喃时,所思所想的只是华年的匆匆流逝,春天的新燕与芳草只是新的一年再次来临的信号,春光的美好词人无从体会,只有独守空闺的孤寂闲愁。徐灿期待着燕子带来春的气息,然而春的使者却久久未来:“一春催试桃花雨,游丝只供晴烟舞。燕也不曾来,湘帘空自开。”(徐灿《踏莎行·不雨》)桃花如雨般纷纷落下,然而春霖却不曾落下。闺中女子卷起帘幕,却连最常见的燕子都迟迟未来。这不由得使词人狐疑,今年的燕子到底哪里去了呢?词人心里猜测着:“萍叶将圆,桐花飞了。雕梁不见乌衣到。想应春在五侯家,东风怕拂寒闺草。”(徐灿《踏莎行·饯春》)在词人的眼中,燕子已经飞往了富贵人家,明媚的春光也没有再光顾自己这寒门小院了,这孤独的春天,怎能不让人惆怅失落。
其次,燕子筑巢梁下,比翼双飞,承载着人们对美满爱情生活的渴望,然而对于独守空闺的词人,看到双宿双飞的燕子却反衬出一份落单的孤愁。两位女词人都在中年时期多写鱼雁难传的离别之愁。正如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以“微雨燕双飞”来反衬“落花人独立”的寂寞。沈宜修在《菩萨蛮·春思》中写道:“蒙蒙细雨丝红落,乱莺啼树春愁恶。风絮舞闲庭,花寒锁画清。雕栏凭独遍,飞入双双燕。春色与归期,归迟春去迟。”莺燕在枝头无序的啼叫,听在百无聊赖的词人心中,只是满怀惆怅。当燕子双双归来,词人却又担心春天会匆忙逝去,正如曾经欢愉美好的时光容易流逝。沈词中的燕子,是反衬词人形单影只的愁言哀曲。徐灿在《醉花阴·春闺》中借双宿双飞的燕子更是发出人不如燕的感慨:“午梦沈沈香薄覆,梦醒春依旧。怕得燕双归,带却愁来,偏向人心授。”此词作于女词人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时,此时的燕子让词人惧怕,为什么呢?连燕子都能双宿双飞、自由自在,而自己却不得不与心爱之人各守天涯。除了与丈夫的长期分离两地,在丈夫升迁徐灿不得不北上之时,燕子亦是徐灿不得不与亲朋故友分离的伤感意象,如《忆秦娥·感旧》:“春风院,花前曾见如花面。如花面,浅斟低语,画楼春晏。闻来已作新巢燕,看花人在花如霰。花如霰,梦中王谢,那是愁见。”还有《玉楼春·寄别四娘》:“风波忽起催人去,肠断一朝分燕羽。无端残梦怯相逢,梦破更添愁万绪。”《忆秦娥·感旧》一词语言清丽感人,上阕回忆起与好友曾在一起赏花斟酒的时光,而转眼,好友已许下婚姻,如同那飞入王谢贵族之家的新燕,侯门一入深似海,两人只能在梦中含愁相见。《玉楼春·寄别四娘》一词写出了世事无常。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兴起,词人便得匆匆离去。与好友一朝分离,从此天各一方,正如那分飞的劳燕,何日才是归期。心心念念的牵挂,都化为了一场梦,然而词人却害怕梦里的相逢,因为梦醒后的怅然若失更让人痛苦万分。
(二)情感含义的深化
两位女词人在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情感色彩之外,徐灿因累于丈夫仕途,同时与丈夫家国立场不同,经历明清易代的黍离之悲,愁思更为幽咽悲慨。
徐灿的此类作品一是表现出远离故土的思乡之情。明朝灭亡后,曾被明朝崇祯皇帝贬斥为“永不叙用”的陈之遴,为了重振门楣,忽视了徐灿的劝告,决心出仕清朝。刚开始时他仕途一片光明,一度做到了户部尚书。虽然徐灿此时被封诰命夫人,春风得意,但她不满丈夫仕清,又担心其登高跌重,同时远离故土亲人,内心始终充满感伤。古时多有尺素寄情、鸿雁传书的典故,而徐灿则在词作《一络索·春闺》中使用“燕子”意象传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惯送好春归去,怕和花语。一帘残梦醉醒中,禁得这番红雨。群玉山头仙侣,乱云无处。不须乡泪染江流,倩个燕儿传与。”明媚温暖的春光已是司空见惯,而在春光将要流逝时,满地飘摇的落红雨又勾起词人伤春惜春之情。春光易老,而故乡此刻又是哪般盛景呢?想来不禁涕泪两行。只能让那秋往江南春回转的燕子带去自己对故乡的牵挂。
仕清后,陈之遴的仕宦生涯跌宕起伏,短短三年,陈之遴接连两次遭贬谪。第二次甚至陈之遴“全家徙辽左”(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一家流放,全族遭受牵连,一路惨凄。徐灿于次年(1659)抵达戍所。流放地尚阳堡环境艰苦,“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或踣其间,或僵马上”(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徐灿从小生长于贵胄之家,何曾生活于此苦寒之地,每当看到从南方飞来的燕子,思乡的愁绪更是浓得化不开:“无情燕,故故却才来。飞傍绣帘还絮语,笑人依旧是天涯,戢翼正徘徊。”(徐灿《望江南·燕来迟》)边塞苦寒之地的春天来得格外慢,连燕子也迟迟从南方飞回。在羁留他乡的词人眼中,迟归的燕子是无情的,因为它没有带来任何家乡的消息。
徐灿的此类作品二是书写了世事变迁的兴亡之愁。徐灿词作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对词境的开拓。词人在多篇词作中表达了兴亡之感,又因丈夫贰仕新朝的原因,其兴亡词在寄托物是人非的伤感之余,平添几分幽咽之音。世事变迁,词人每每思念故国,只用那生活中的最寻常事物来托物言志:“旧柳浓耶,新蒲放也,依然风景吴阊。去年今午,何处把霞觞。赢得残笺剩管,犹吟泛、几曲回塘。伤心事,飞来双燕,絮语诉斜阳。”(徐灿《满庭芳·姑苏午日次素庵韵》)端午佳节,词人返回故乡,看到江南一片生机勃勃的新绿,吴阊景色如故,尤其去年羁旅他乡,不得自由。然而如今回来,心境还能再似从前吗?那梁上的双燕,似乎也在诉说着故国如那斜阳一般,往事不堪回首的伤感,那燕子也仿佛见证了王朝的沧海巨变,后悔误到瀛洲。
三、徐灿词对沈宜修词的继承与超越
分析两位女词人的春愁秋怨,沈宜修之愁是对自身生活和贫病交加的叹息,与自己琴瑟和鸣的丈夫长期在外做官,偌大的叶氏家族上事下育,沈宜修虽尽心竭力,却勉力拮据,还有对亲友的牵挂,对儿女的怜惜;而徐灿之闺怨一是因丈夫仕途屡屡受挫而产生的世事沧桑之慨,二是对故国亲友的追念与乡关之思。在此类作品中,两位女词人都借“燕子”这一意象体现出了哀而不怨、悲而不恨的情感特征。综合比较沈宜修和徐灿有关“燕子”意象的词作,她们的词作都体现了闺音文学之本色。
首先,两位女词人的作品均多采取生活中常见之意象,表现出婉约纤细的气质。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收紧,在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压迫下,女性长期处于不平等与被压迫的位置,她们比男性能体会到更多的心理曲折,这种卑弱性导致的话语权的淹没,使女性在发声时有意无意体现出曲折婉转的风格。尤其是两位较为传统的、谨遵儒家夫为妻纲的女词人,家学的影响、自身的修养使其具有温婉典雅的气质,在作品里体现出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女性观。同时,女子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狭隘的环境中,困于闺阁的尺寸之间,在年复一年的时光变迁中,目之所见的事物单调而有限。因此,在她们的作品里,她们选取的总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意象,她们应和着鸟鸣虫吟,流连着春花秋月,用女性的敏感、细腻感受着生活。
其次,两位女词人的作品都具有幽咽愁苦的伤怨风格。两位女词人都有轻松愉快的年少时光和坎坷孤寂的中年生活。据笔者统计,《拙政园诗馀》直接出现“愁”字60次,“泪”字22次,其他抒发愁情泪意的字词如“恨”“怨”“瘦”“憔悴”“闷”“孤”等,更是随处可见。生活的创伤使她们的词作都呈现出一种忧愁苦闷的文风特征。因此,词作中愁苦的原因,除了中国文学传统之以凄为美的审美追求,愁苦之音易好,更多是来自对生活中苦难的嗟叹,使词中之情格外真切,情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再次,徐灿后期词与沈宜修词相比呈现出了一种超越性。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国破家亡使徐灿身不由己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唤醒了沉睡在骨子里的节操。正是对故国的坚定拥趸让徐灿从传统闺媛词中脱颖出来,取得与李清照并肩的词史成就。同时,在当时文字狱以及她与丈夫政治立场不同的影响之下,她的词作意蕴除了格调的深沉厚重之外,在美感效果上也表现了一种沉郁顿挫的幽咽曲折色彩。
沈宜修和徐灿处于明末清初思想大开的过渡时期,她们借“燕子”这一意象,抒发了自己内心的触动。沈宜修书写了家庭生活、思妇怀远,而徐灿书写的是闺愁、乡愁、旅愁、离愁、亡国之愁。她们的思想中既有传统妇德观念的守旧,也有一定的思想觉醒。徐灿词完成了从闺怨闺情向家国之思的倾斜,营造出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纵深,因此,徐灿词相较于沈宜修词,除了典雅含愁的闺秀风范外,还多了幽咽慷慨的悲壮感。但对于女性主义来说,两人词作的思想意识依旧处于萌芽阶段,与清中期的吴藻、顾贞立等女词人更为激进的女性意识表达形成不同。因此,通过典型女词人的作品思想对比,我们可以探求深层的社会发展思潮渊源,发现明清对女性社会价值和社会性别定位的反思。从沈宜修到徐灿,女性词走过了从隽雅含愁到词旨深化的过程,而这也是词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