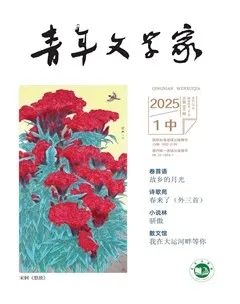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在路上”—《宇宙探索编辑部》的 叙事模式分析
《宇宙探索编辑部》讲述了民间科学家唐志军和他的团队的外星人探索之旅,片中荒诞又温情的叙事特色吸引了许多观众,成为2023年国产电影票房的“黑马”。影片采用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叙述,使观众不知不觉地沉浸于故事情境中。另外,影片颇具公路类型电影的特点,通过寻找外星人的明线叙事与唐志军寻解心灵谜题的暗线相交织的叙事方式,层次丰富地表现了“出走—寻找—救赎”的叙事主线,并且运用空间叙事的多种策略增强叙事文本的“临场感”,烘托叙事主题。从整体上看,影片荒诞的叙事特色十分突出,设置了多个情节“陷阱”造成反转,并且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直接呈现叙事文本,最后以开放性的结局落下帷幕,使叙事文本的意蕴回味悠长。
一、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
《宇宙探索编辑部》以时间的因果关联为叙事动力结构。因果式线性结构内含两个明确的要义:其一,该结构模式主要以事件的因果关联为动力展开叙事;其二,其叙事线索以单一的线性时间展开,很少设置插曲式叙述或多线索的并置处理。
影片以唐志军1990年接受电视台采访的录像为楔子引入文本关于外星生物探索与人类意义追问的叙事主题,最终又以唐志军对一路走来的总结性讲话为结尾,整体上叙事的结构体现为“总—分—总”式的圆满结构。全片分为五个章节,依次展开:第一章“追UFO的人”,介绍了编辑部的背景以及唐志军、秦彩蓉、那日苏、陈晓晓四人组成探索小队的起因;第二章“蜀道难”,展开了四人辗转向当事人孙一通访求异象真相的过程;第三章“等待麻雀降临的少年”中,四人跟随着孙一通踏上了与外星生物会面的路途;第四章“西南深处”,五人走入西南山林里,孙一通突然失踪,唐志军独自踏上寻找外星生物的路;终章里,唐志军历经艰险与孙一通相遇,放下心中关于女儿之死的执念回到北京。
电影的章节之间以线索相关联,随着唐志军等人一步一步地发掘调查,真相逐层被揭露,由此引向了下一阶段的情节。叙事文本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情节,以唐志军为绝对主要人物,围绕他的动向展开情节。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以简单明了的叙事着重于凸显叙事对象本身的因果关联,隐藏起叙事痕迹和“作者—隐含作者—叙述人”的叙事操纵。它反而更注重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通过对叙事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的巧妙驾驭,来强化文本结构的张力。影片线索与线索之间关联明晰,逐级导入,逻辑完满顺畅,呈现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发展脉络,遵循的是一种戏剧性的叙述惯例,通过一个首尾相连、圆满完整的时间序列过程得到逐次扩展和强化。
二、“出发—寻找—救赎”的叙事主线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情节发展伴随着主角几人的游历进行,在第二章至终章里,场景的变换隐喻着唐志军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索之旅,从而构成了寻找外星人的明线与寻找生命之谜的暗线相交织的多层叙事。影片以公路片的类型风格,通过调用空间叙事突出了“出发—寻找—救赎”的叙事主线。
(一)明暗交织的叙事线索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类表达反思现代消费主义社会,温情且治愈心灵的公路类型电影,它与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相伴而生,表现主人公追寻自我的精神向往。“Road Movie(公路片):一种主要产自北美的电影类型,其主角通常在路上旅行,有时以一种漫无目的的方式来了解所在国家的价值观及社会问题。”(吉奥夫·安德鲁《电影之书—世界电影史上的150部经典之作》)21世纪初,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国的公路电影也由此诞生。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矛盾冲突下,中国式公路电影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城市边缘的群体。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他们祈盼寻求自由,获取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因而选择逃离现实困境。
《宇宙探索编辑部》一片不仅是寻找外星人之旅的呈现,同时也是唐志军的心灵寻解之旅。影片的英文译名恰如其分地体现着本片的类型特色及叙事主线—Journey to the West,即“西游记”,这是现代文明中被挤压、被边缘化的一群人的心灵寻根之旅。
影片伊始便展示了唐志军的困窘,他在编辑部任职三十余年,一生致力于探寻地外文明,却是晚景凄凉,住在简陋破旧的屋子里。编辑部仅有一间拥挤的办公室,杂志也没有什么销路,在办公室的角落里随意堆砌着。另外,影片还颇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唐志军的精神困境—他只能靠在精神病院演讲获得额外的收入。在现代的资本文明中,唐志军这样把一生的钱财、精力全都投注于一项难以证实的研究就如精神病人一般难逃被边缘化的处境。影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边缘化的群体中的一员—内蒙古气象站放气球的酒鬼那日苏、童年灰暗又患抑郁症的陈晓晓、被村里人认为精神失常的孙一通,骑着玩具车四处追随外星生命的“陨石猎人”等。他们都心怀理想,沉溺于自己的追索中,企图逃离现实的种种压迫,始终在追寻精神之乡的路上。
影片以一环接一环的逻辑线条牢牢地抓紧观众的视线,从唐志军家电视的故障到网络搜索到肖全旺发出的帖子,从肖家找到孙一通,再到孙一通领路前往西南深山。接二连三的线索贯穿起唐志军一行人寻找外星人的旅程,但直到终章,影片才揭开唐志军苦苦追索地外文明的更深层的执念,即女儿自杀前发出的生命谜题。实际上,回溯到影片开头,片中隐秘地埋下许多指向最终谜底的伏笔,如唐志军独处时会时不时翻看的老式电话,这是接收到女儿自杀前最后一条短信的手机;秦彩蓉采访中提到的唐志军女儿患遗传性抑郁症而自杀的隐情;巴士上,秦彩蓉与唐志军的对话中唐志军对于女儿之死无法释怀的态度;等等。这些片段的线索都因结尾的悬置只能通过回溯来追寻,在影片的最后,寻找外星人这条明线的背后寻解心中执念之谜的暗线才得以揭示,影片藏匿起唐志军内心的情感活动,以造成悬置后出人意料的叙事效果。“所有成功的叙事,无论何种长度,都是一连串的悬念和意外,令我们处于一种不耐烦、惊奇和部分满足的波动状态中。”(H·伯特·阿波特《剑桥叙事学导论》)到了旅程的结束,唐志军才缓缓拿出手机,说出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此时,观众才明白他付出的艰辛都是为了解开女儿之死的谜题。叙事的主题由此得到点睛和升华,人物也终于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回归到生命原本的平淡和美好中。
(二)空间的叙事策略
苏联著名美学家莫·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一书中曾“把艺术划为三种—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时间艺术”。电影叙事通过一系列画面的排列和组合来刻画形象,描绘事件,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叙事表现力,它所构成的空间无疑属于人造的艺术空间。就形象空间而论,影片作为一部“在路上”的公路类型电影巧妙地运用空间蒙太奇的叙事策略,从场景的置换、空间畸变等叙事手段完成了影片的空间叙事对叙事主线的烘托。
形象空间是从影像整体结构角度对电影叙事空间的审视,有两层含义:其一,形象空间作为整体结构意义上的空间,具有相对完整、合成封闭性的系统性质;其二,形象空间具有某种“超文本”的性质,有赖于接受主体的能动参与共同建构。
1.场景的置换
唐志军的出走是为了寻找地外生命的存在踪迹,支撑他在艰苦中仍坚持寻找的信念被延宕至末尾才得以揭示,答案“不在外太空不在宇宙深处,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存在的谜题,也是这个谜题的答案”。实际上唐志军的回答早已隐喻于空间的场景置换中,他一路的旅途实质上就是生命回归到原初的过程。一行人离开北京,走入乡村,又从乡村走进山林,象征着人类离开城市文明,从现代化向传统的返归,又进一步回溯到自然状态。最终在深林洞穴里,唐志军看到了石壁上画的DNA双螺旋结构图,原来人类苦苦追索的自身价值本就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已刻写在每个人自身的基因里,等待自身去创造、去开发。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山林,又到洞穴,场景逐渐艰难,隐喻着人类的返璞归真。
2.空间畸变手段
影片除了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方面企图营造出探寻外星人历程中的神秘、难以预测的效果之外,同时也在空间叙事上运用了多种多样的空间畸变手段。
在拍摄上,影片全片采用手持摄像机的拍摄手法,尽可能地增强观众的“临场感”和伪纪录片的影像风格,引导观众轻易地进入情境中。与此同时,影片还采用了大量的变焦镜头,竭力突出摄像机的记录功能,当人物在谈话时,有意拉近谈话人的距离。在讲话人变动时,影片使用延迟镜头变向的反应时间,制造第一人称视角的在场。另外,影片还使用大量的跳切镜头,刻意打破时间、空间上的连续性,其中十分显著的是在人物谈话时,删去人物话语之间的间歇而用跳切镜头相接。一方面,跳切镜头形成了一定的间离;另一方面,摄像机保留跳切的痕迹,又使这种间离效果不至于影响到影片欲营造的在场感。
三、荒诞的叙事特色
“荒诞叙事显然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模式,是一种立意要通过叙事来推翻传统叙事及掩藏在传统叙事背后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认识与假想的另类叙事。”(范颖《主体意识的不确定性与中国现代荒诞叙事》)影片刻意营造荒诞的喜剧效果,在寻找外星人这条明线上制造笑料,却又在结尾揭示人物内心的痛楚;并通过唐志军这一理想主义人物的凄凉与笑料形成反差,从而造成黑色幽默的悖反性,造就了影片笑中带泪、荒诞中引人深思的叙事特色。
(一)似是而非的情节“陷阱”
伊曼努尔·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由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的悖反产生幽默。影片首先就从叙事主题上营造了这种幽默—一名民间人士带着自己制作的仪器和完全不懂天文地理的几个人上路,寻找外星人。第一章里就鲜明地展现了高端科技与民间科学之间的悖反性,为了拉来赞助唐志军穿上珍藏的旧宇航服,像件展品一般与人合影留念。又因年代久远,他被困在头盔里,只得叫来消防员将其拉到楼下锯开,拆窗户、看热闹的人群等场景形成一片混乱。穿着宇航服的唐志军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升空,宏伟的交响乐与狼狈的场景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事实上,影片多次都利用产生笑料的悖反性引诱观众走入情节的“陷阱”中,形成期待视野,随后又恶作剧般打破它,造成意料之外的荒诞效果。穷困潦倒的唐志军,每天带着自制的装备从电视机上接收宇宙信号,提着自制的探测器贸然上路;被村里人认为神智有些失常的孙一通,每天顶着一口铁锅却说自己能感应到外星人的指示。影片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充分展示两人不可信的特质,在结尾又突破观众的期待视野,实现情节的反转,造成惊喜。影片将看似荒谬背理的情节赋予合法性,完成悖反的喜剧效果。
(二)神秘的叙事视角
电影中,摄像机毫不避讳地存在于情节中,营造出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仿佛一部纪实新闻片,试图将观众全情卷入影片塑造的“幻想真实”。“布莱恩·麦克海尔(Brian McHale)曾提出一个从“纯”叙述到“纯”模仿的渐进等级表”(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分为描述性概括、较不“纯粹”的描述性概括、间接内容转述、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的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七种类型。电影采用伪纪录片的手段,始终强调摄像机的存在,引导观众处于摄像机的视点观看。观众由此被置于第一人称视角,从事件外部观察着电影叙述。人物的对谈行为则以直接话语的形态当场上演,叙事也以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进行。通过直接话语的搬演,影片制造了强烈的“临场感”,引导观众产生“幻想认同”,强化着叙事形塑的“幻象真实”,“使观众陷入对事件的外部流程的关注而不知不觉地成为叙事操纵的捕获物”(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践》)。
《宇宙探索编辑部》以因果关联为叙事动力建构起叙事文本的线性结构,运用空间叙事的策略展现出公路类型电影的叙事风格,将寻找外星人的明线和唐志军寻解心灵谜题的暗线相交织,丰富了文本的叙事层次,形成了“出走—寻找—救赎”的叙事主线。此外,影片还通过塑造情节“陷阱”、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等手段营造出了荒诞的叙事特色,以“黑色幽默”凸显现代资本社会的边缘人群体处境的困窘,鼓励人们探索自身生命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