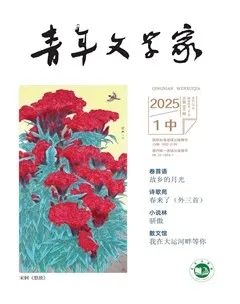独立与自由:中西方小说中女性形象之比较
在这片浩瀚的文学海洋中,女性角色或随波逐流,或挺立风雨,奏响了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欧洲戏剧之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作为挪威现实主义戏剧代表之作,其最后一幕中娜拉的谈话曾被誉为“妇女独立宣言”。面对世俗的不屑与命运的风雨,娜拉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妥协精神。相较而言,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通过聚焦中国20世纪80年代东北转型的时代浪潮中的芸芸众生,展现了当时的女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顿,以及她们对理想与自由的探寻。尽管两部作品相隔近两个世纪,但它们蕴含的女性独立与自由追求的精神依然让现代社会的我们产生共鸣,令我们思考女性成长的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启示。
一、灵魂的回声:娜拉与傅东心的共鸣与回响
在19世纪的欧洲,女性多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1854年,考文垂·帕特莫尔所著的《房中天使》的畅销,使得“家庭天使”成为理想女性的象征。《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无疑符合这一形象,她扮演着生活在“游戏园”中的“玩偶妻子”角色,所有生活细节均受到丈夫海尔茂的严格掌控。她为了取悦丈夫,甚至不惜“蹦蹦跳跳”“耍把戏”,她的婚姻最终沦为一场无休止的表演。相较而言,《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傅东心与庄德增的关系则显得相对平等。在婚前,傅东心便明确自己的底线:“晚上我看书,写东西,记日记,你不要打扰我。”这一坚持使她在婚后仍能追求自我和兴趣。她为庄德增的印刷厂设计烟标,取得良好反响,展现出对丈夫事业的实质性支持。傅东心在家庭中追求的,不仅是安稳的生活,更是精神与独立的渴望,与娜拉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娜拉如烈焰般决绝地燃烧,通过离家出走实现自我;傅东心如泠泠清泉,在隐忍中追求心灵的自由。她们的反抗方式各异,却同样深刻。娜拉的反抗经历了从温和到激烈的转变。娜拉在得知借贷事件即将暴露时,不顾海尔茂的悉心教导,跳起塔兰特拉舞。这一舞蹈不仅是对内心恐惧与压抑的宣泄,更是对海尔茂控制的潜在反抗。当“奇迹”未现,期望破灭,娜拉终于认清了自己在婚姻中的“玩偶”地位,愤然出走,以这种激烈的反抗方式结束了被束缚的生活。相较于娜拉的激烈,傅东心的反抗更显冷静。她通过游历,从现实中抽离,以应对婚姻的压抑。婚姻的初期,她展现出独立的面貌,甚至能够支配家庭财产,借钱为李斐垫付学费;然而,在婚姻的后期,她通过与庄德增的冷静疏离,逐渐摆脱了婚姻的压抑。傅东心并未完全割裂与家庭的关系,而是选择在精神和地理上保持距离,她的反抗更像是一场持久的疏离与冷漠,而非娜拉般的决绝。
二、双面镜像:献身与独立的不同范式
娜拉是献身型女性的代表,而傅东心则是独立型女性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她甚至表现得更为激进。二者不同的选择,展现了时代进程中的双面镜像,为世人提供了不同的生活范式。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往往在男性作为“第一性”的前提下确立,导致她们成为他人的附属。丁尼森在《公主》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期待:“男人耕地女人生炉……”娜拉在家庭困境中甘愿秘密牺牲,甚至考虑自杀以维护丈夫的名誉,最终却被视为“玩偶”,失去人格的尊严。与娜拉不同,傅东心表现出的是独立型女性的特质。她拒绝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主动追求个人意志与精神自由。这种激进的独立虽让她追求自由,却也给她带来了孤立感与生活压力。在工作中,她拒绝妥协;在家庭中,她与丈夫保持距离,内心的坚守伴随孤独。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强调,女性的独立需有平等的职场环境与家庭支持,否则,激进的独立可能沦为“孤军奋战”,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这正是傅东心对所面对的时代的挑战与反思。
三、命运之网:娜拉与傅东心悲剧婚姻的深层纠葛
无论是在19世纪的欧洲还是现代的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和女性内心的需求共同作用,导致了娜拉与傅东心婚姻中的悲剧性命运。
就社会观念而言,娜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自幼便是父亲的“玩偶女儿”,婚后又成为海尔茂的“玩偶妻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常被视为婚姻的附属,个人意愿往往被忽视。娜拉的价值完全依附于海尔茂,她的忠诚与牺牲并未换来理解,反而成为她无力反抗的根源,造成了她的悲剧结局。相较而言,傅东心在中国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仍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作为27岁的知青,她的婚姻选择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年龄和社会压力,而非真正的爱情。尽管生活表面平静,二人却始终没有真正走入彼此的内心。
其次,内心需求同样不可忽视。虽然娜拉和傅东心的丈夫在外在条件上看似优秀,但在情感交流与内心理解上,两位女性都感到孤独与被忽视。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娜拉与傅东心的悲剧不仅源于外在条件,更在于她们内心深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未被满足。最终,她们选择逃离,娜拉出走,而傅东心则独自旅行,寻求灵魂的自由与自我认同。这一选择正是对婚姻中缺失的理解与支持的有力反击。
娜拉因经济上的依附而陷入困境,而傅东心凭借独立的经济能力拥有了对婚姻的部分控制权。加之教育背景的不同,她们的人生之路分野而行,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经济地位在婚姻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夫妻人格的不平等源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经济基础是家庭地位的决定因素。娜拉在家庭中的一切完全依赖海尔茂,由丈夫控制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使娜拉的自我价值无法得到认可,她的身份被锁定为“玩偶妻子”,缺乏自我追求的能力。相较而言,傅东心具备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作为工人,她在社会中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经济来源,因而在家庭中享有自主权。在傅东心的婚姻中,经济上的独立使她能在家庭事务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能够提出个人需求并获得尊重。这种经济自主性为她的婚姻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促使她追求自我的实现。
教育背景同样在她们的命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娜拉被教育成优雅的淑女,遵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然而这种教育使她缺乏自我认知。相对而言,傅东心成长于书香门第,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独立的人格与思维能力,她将丈夫视为生活的合作伙伴,而非自我价值的延伸,追求个人的自由与理想。
四、自由的追寻:娜拉与傅东心的现实启示
娜拉的困顿与傅东心的自由,昭示了女性只有通过经济独立,才能获得掌控命运的力量。经济独立是她们挣脱桎梏的第一步,也是飞向自由的翅膀。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往往把幸福寄托在与她们有着同样缺点的伴侣身上,而这种压迫的根源在于无法独立获取生活资料。当女性无法为自己的生活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时,她们婚前依赖父亲,婚后则依附于丈夫。正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所写,女性在婚后几乎是“重生”为“丈夫的孩子”,不得不在丈夫的羽翼下生存。不同于始终受制于丈夫掌控的娜拉,傅东心能相对自由地支配家庭开支,且丈夫给予了她足够的尊重。这与她的经济独立密切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今天,女性应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尝试各种职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从依附于男性的贤妻良母转变为独立的劳动者。这一转变将有助于实现两性经济地位的平等,打破在婚姻中的失语状态。两位女性的经历揭示了婚姻并非依附与牺牲的舞台,而是平等与尊重的契约。正确的婚恋观是女性走向幸福的指引,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婚姻观是看待婚姻和爱情的基本理解。19世纪的欧洲,“美丽的外表是女人的权柄”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因缺乏财产继承权而将婚姻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婚姻往往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男性息息相关。《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林丹太太正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前者嫁给了有经济基础的海尔茂,后者则迫于生计选择富有的林丹先生。恩格斯强调,婚姻生活必须基于爱情,若仅仅是为了金钱、权势而结合,则必然走向悲剧。傅东心与庄德增的婚姻正是如此,傅东心因社会舆论的压力在“正好的时间”选择婚姻,却并非出于真正的爱情,在理性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
女性应摆脱将婚姻作为实现阶层跃迁的思想,只有寻求心灵与精神的契合,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现代社会更应关注女性的情感需求和社会诉求,女性应被视为独立个体,拥有自由选择婚配的权利。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不仅能帮助女性在婚姻中获得幸福,也能推动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与理解。只有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女性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成为不依附于他人的独立个体。
娜拉破茧成蝶,傅东心则成为自己的“摩西”,引领自己走出困境。她们的故事不仅是女性觉醒的颂歌,更是关于心灵回归与自我救赎的诗篇。
在婚姻中,女性常因沉迷于爱情的幻想而放弃独立的人格与理性的思考,最终迷失自我。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中指出:“当爱情(哪怕是纯洁的爱情),成为你生活的全部之时,你的心灵会变得过分软弱。”女性在男权压迫下逃离,成为她们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娜拉在认清海尔茂的虚妄爱情后,勇敢地离开家庭,寻求广阔的天地。傅东心同样在婚姻的束缚中寻找灵魂的自由。
关于女性在逃离婚姻后应选择回归社会还是家庭,一直存在争议。然而,女性无论选择何种道路,首先应回归自我。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到,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是女性真正的追求。娜拉出走前庄严宣告:“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长期以来,忍耐和服从已成为女性的代名词。在当今社会,女性应积极寻求独立,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在《平原上的摩西》中,“谁是摩西”的问题始终未解。对于傅东心而言,她无法拯救所有人,只能引领自己独自踏上生命之旅。真正的摩西或许只有自我,唯有自由意志、理性精神和独立人格,才能渡过这茫茫的生命之海。
五、破茧成蝶、自渡为舟的心灵旅程
娜拉与傅东心最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逃离了家庭,但这不是沉默的逃避,而是自我觉醒的力量。通过行动与内心的探索,娜拉和傅东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脱之路。这种自度与觉醒,代表了现代女性在面对现实压迫时的积极抗争,体现了她们对个人价值与自由的坚定追求。
通过对比分析《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傅东心,我们发现,尽管两部作品成书年代相隔甚远,但两位女性形象有相似的性格特质—善良的天性、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对人格独立的追求,二者跨越千载,相映生辉。
本文系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东北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410165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新世纪小说英译与副文本重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JYTMS202310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