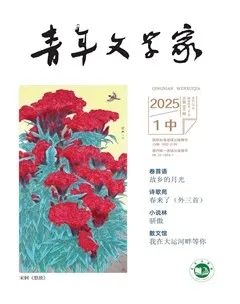莫言小说的史传意味研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史记》以纪传体书写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书写传统,其本纪、世家、列传的模式更是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模式,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文学注定要带有史传传统。中国文学“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史传文学太发达了,以至她的儿子在很长时期不能从她的荫庇下走出来,可怜巴巴地拉着史传文学的衣襟,在历史的途程中踽踽而行”(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自唐代元稹《莺莺传》、裴硎《传奇》始,传奇文章的篇名大多以“传”“记”命名,如《任氏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古镜记》《枕中记》《离魂记》《石头记》等,“传”“记”的命名方式暴露了传奇文体“补正史之阙”的叙事追求和历史意识。莫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以极其强烈的情节性突出人物特征,使人物在其作品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故事层面来讲,莫言的作品可以看作主角人物的传记,如《西门闹传》《上官鲁氏传》《余占鳌传》《戴凤莲传》等。另外,莫言虽然无意去叙述中国的历史发展,但其人物存在的历史背景以及对高密东北乡民间视角的历史叙事,使作品最终呈现出“民间的历史演义”的文学效果,在无形中呈现出作者的历史意识。
一、为传奇女性作传
莫言小说中有诸多纵情肆意的传奇女性,但是这些女性在成长初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个性之处,而是努力向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女性所确立的行为规范靠拢。正如《仪礼·丧服》所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成为父系社会下的附属品,失去自我主体性,要无限趋近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温柔”“贤惠”“顺从”“端庄”等优良品质,才能成为社会所认同的标准女性,其存在及行动无不受到男性形象的“凝视”和“审谛”,成为失语的、无主体性的、被观赏的他者存在。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在成长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经历了时代的巨变,精神的巨大潜力被激发出来,经历磨难之后最终成为异于常人的传奇人物。时代的风云诡谲与变革打破了女性形象原有的认知体系,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生活无尽的苦难造就了她们刚毅、不屈的品格,激发了她们久被压抑的智慧与心性,使她们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确认,传奇的经历使她们注定成为时代的传奇人物。
莫言小说中有众多富有个性的女性,如《红高粱》中“我奶奶”戴凤莲、“二奶奶”恋儿,《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姐姐”来弟,《蛙》中“姑姑”万心,《翱翔》中逃离包办婚姻的燕燕,这些女性在青年时期本质上仍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是人的异化状态,嫁人、换亲、生儿子,女性仍然无法摆脱强加于她们身上的封建枷锁,进而屈从于社会制度中压抑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贬损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成为父系文化的虚弱陪衬。自元稹的《莺莺传》始,女性形象是传奇小说中重要的书写对象,她们因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强烈的欲望追求、自由大胆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异于传统文化规范下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虽然传奇小说中的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制定规则、掌握权力的封建制度中,如霍小玉、李娃、红拂女等,但她们坎坷的出身、跌宕的人生经历使她们比同时代的女性更早地有了自我觉醒的意识和观念,不再是缺乏主体性的“单向度的人”,而是以自由大胆的观念和过人的智慧进行反抗,主动争取、自由表达,成为封建社会中的传奇人物,使读者感悟到传奇女性的价值与魅力。奇女子的传奇之处在于即使她们深陷泥淖,也遮盖不住其光芒。压抑的封建制度将女性逼迫到生存的角落,退无可退时,她们揭竿而起,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跳出传统女性的生死轮回,以跌宕奇异的人生经历异于同时代女性,成为一代传奇。
传奇女性的传奇在于其身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就发生了转变,从中国礼教制度规范下的传统女性成为远离社会核心的边缘人物,从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退出之后,所受的道德制约及意识形态性就大大削弱,是以能够大胆展示久被压抑的个性,蓬勃顽强的生命力才得以保存。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日常生活的意识与行为观念反映着意识形态的某些特性,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存在,人们全部的经验、看法及体认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性,反映了阿尔都塞所说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召唤关系。身份是意识形态下的象征符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映射,体现了社会体制的运行,通过个体身份的变化,反映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屈从或反抗。身份的转变是人物成为传奇的必要前提,如《红高粱》中“我奶奶”在麻风病父子被杀之后成了单家的女掌柜,才有了壮大酒业、英勇抗日的传奇故事;《蛙》中“姑姑”万心的身份从军医烈士的遗孤到空军飞行员的女朋友,再到乡村专职接生医生,又到计划生育领导组长。万心的身份从原本依附父亲和男友走向了自我确认,她凭借自己的本领获得了医生的身份,被人视作活菩萨,又因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成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虽然万心的一生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身份的获得与转变仍是她传奇人生的重要注脚。传奇女性大多走出意识形态的中心,在社会结构的边缘野蛮生长。这种边缘者身份是对《史传》中游侠列传式书写的继承,为底层百姓作传,描述江湖儿女的传奇人生。传奇故事中的女性以一种模糊了性别的社会身份来参与世界,并对其身份有一种深刻的体认以及责任的自觉承担,打破了男性对女性的文化建构,以女性的力量使自己成为民间传奇,进入正统的历史叙事,从而为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开辟出新的运行方式,在同样蓬勃的生命力中获得自我主体认证,最终完成民间女性的传奇化。
二、民间历史演义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对当下及过往的历史进程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历史的行进轨迹最终会完整无遗地体现在人的身上,人的个体经验是历史变迁的落脚点。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认为:“历史经验是现在的个人主体同过去的文化客体相遇时产生的。”个人主体在其存在的时代中成长,在时代精神的感染下建立了自我意识与观念认识,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当过去的历史存在作为文化客体与个人主体相遇,文化客体以其博大、浩瀚的历史储存打开了个体的思维视野,给予主体以精神启迪和文化升华,使主体在感受到其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形成符合主体时代的、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莫言小说中鲜有宏观全面的历史叙事,更多的是处在历史洪流之下的莫言在故乡的生活经历中切身体悟到的个体经验。个体经验指导着文学书写,无论是以客观写实、冷静理性见长的史传类叙事,还是以抒怀情感、言情达意的散文化叙事,抑或以荒诞离奇、奇幻跌宕的传奇化叙事,虽然文学的叙事方式不一样,但都是个体经验表达书写的产物。莫言在文学世界中寻找与自我历史经验相契合的话语表述,灵活地调动各种文学手法,有意识地突出和强调一些因素,也克制和压缩另一些因素,以作品主题、人物个性、基调变化、反复书写等技巧对历史素材进行创作和升华,进行独特的、个体的历史经验书写,以深刻的笔触描写高密东北乡上那群敢爱敢恨、肆意纵情、复杂的男男女女,在传奇男女的辉煌事迹中表达个体经验,在民间视野的范畴下书写历史演义。
莫言确立自己的民间书写立场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学作品的主流是革命历史小说,小说内容是讲述革命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发展步入一个焕然一新的新时期,个体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新的时代环境,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创作方式受到了新时期思潮的影响,有明显地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痕迹,以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刚刚结束的历史时期,发觉时代宛若一个顽童,恶作剧地将个人玩弄于股掌,不讲究逻辑和章法,无法预见,无人可逃避。在对峙历史与开拓未来时,莫言广泛地接触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精神,对“人”“自我”的认识变得越发迷茫和混乱,对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失去了信念感,进入到“先锋”的创作语境,从而陷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对存在的遗忘”的状态,但很快莫言就突破了既有的创作思路,跳出了新时期的写作方式。莫言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也不再使用“大说”的书写方式,与主流的叙事模式拉开距离,他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并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以小说的形式对民间进行书写,以“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立场来进行创作,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民间历史演义。
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基点来进行民间立场的文学创作,去挖掘高密故乡的人情与风物,在高密民风民俗的书写之中进行塑造一批偏离主流却又精忠报国、复杂立体的民间儿女,在对民间“岩穴之士”书写的过程中,以远离庙堂的江湖民间为对象来进行叙事,创造民间的人物传奇。王德威在《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书写中,“时间的流逝通常并不是最显要的因素。最令史家关心的反而是‘空间化’的作用—将道德或政治卓著的事件或者人物空间化以引为纪念”。王德威的研究表明,中国史学家的关注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品格高尚的道德模范或建功立业的政治典范,并将其丰功伟绩记载在册,成为可视的实体,在阅读过程中进行空间化传播,并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发挥作用。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以整体性的架构和国家话语来进行史书书写,对于道德模范和政治典范之外的个体,没有空间进行多施笔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发表过自己对史书的看法:“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鲁迅也曾说中国的正史是在“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在正史的书写之外,仍然存在着诸多“岩穴之士”“中国的脊梁”,经历复杂、坎廪失志,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激情活跃在民间。莫言承继了鲁迅等人的创作衣钵,他明确表示,历史与传奇是密不可分的,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会在后代的转述和再现中不断地变丰富,逐渐成为后人心中的传奇故事。跌宕的传奇故事是人们对历史的初印象。莫言借由民间儿女的传奇人生来间接地展示时代的更迭与变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来开辟自己的叙事世界,以此来重新发现、纠正和确立历史中价值秩序的路标和榜样,是主流之外的民间立场叙事。
莫言从小生活在民间的土地上,对民间的传奇历史耳濡目染,相对于庙堂之高的传统理论,莫言对乡间流传的民间传奇和人物野史更有兴趣。民间口口相传的逸闻趣事对莫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文学书写中,莫言不追求历史事件的还原,真实并非其创作目标,而是以主动、虚构的方式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故事,最终在人物形象身上实现意义表达,以民间书写的方式去发现、肯定人的价值。人物是文学的灵魂,以叙事性见长的小说用离奇的情节发展、复杂的环境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情节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最终都要在人物的身上才能实现价值,进行意义方面的升华。因此,小说书写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人的存在使历史经验找到了立足点,是文学作品动人心弦的根本原因。莫言小说中记载的历史是关于高密人的历史,是被史书遗忘的角落里的另类历史。历史是已逝的过去,是无法言喻的客观存在,具有一维性和不可回溯性。历史的本体意义是一堆模糊不清、凌乱散漫的历史遗留物,它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无法自我呈现,等待着被发掘。文学进入庞杂纷乱的历史存在,以人的价值为叙事线索来发掘被主流忽略的史料素材,将历史材料统一在以人物为主导的叙事方向中,以文学的方式来讲述集体与个人的行进道路、民间与庙堂的传奇变迁,在叙事中阐释对历史发展进程、主体形象生长的切身体验及形而上的探究思考。文学书写的是当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以一种压迫式和摧毁式的方式呈现时,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意义,生命力激情发挥的可能性。莫言的文学书写不是对现实真人的摹写,也不是历史社会的人格化,是作家在诞生无数传奇的民间大地上对人性的主观性探询,对实验性自我的探寻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