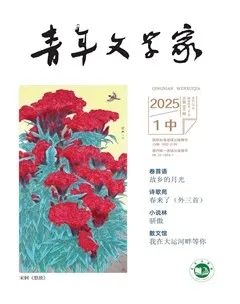胡杨路
几乎所有人对胡杨的第一印象便是其生命力了,在额济纳旗,人们赞扬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三千年的胡杨,一亿年的历史”。这么多年来,人们为胡杨谱画出的精神体系是近乎完美的—坚毅的英雄角色。翻了翻古今与胡杨有关的作品,关于它的诗歌、散文并不多,但都生出了一股豪迈的永恒的气息,像是旷野上的群狼,将土地生生地踩在脚下。
而我不同,自打亲眼见过了胡杨后,震撼便不是仅仅止步于它的不朽。诚然,胡杨是英雄式的,却又以一种有别于集体英雄主义的方式出现。它们有天然的,由环境所撒落的孤独感,却又以一种非合作的默契共生似的成长着,去抗击外在的环境。这是他成为英雄的独特之处(有些地方有落单的胡杨,也可做不同于胡杨林的孤胆英雄)。如同成群的孤岛覆盖沙漠的海洋,它们所形成的群便不是牺牲群,而是一群树有着共同的生存理想,以非集体或非个人牺牲的方式去实现一个非集体目标,而后再以集体的力量成就防风固沙的环保意义。强而非摧枯拉朽式的,美而不易折的,有韧性地在沙地上肆意蔓延着,以此来形容胡杨的长姿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大众为胡杨的气节所折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深深扎根,与边疆的兵团甘于奉献的精神不谋而合。这跟中国影视界上的英雄不同,那些所谓的英雄往往陷入了误区,把个人的受伤或者死亡作为实现价值的前提,为了满足人感受上的强弱平衡,编剧不得不以这样的结尾作为人物品格的矫正,实在是未能破除框架的病态。
祛魅英雄是成为英雄的第一步,胡杨精神理应得到延拓:它的奉献是基于自我的实现,以小小的个体的价值叠加成一个大屏障。正是这基于自我,展现风貌的开始,胡杨才称得上是英雄树。
倘若从胡杨林与胡杨树看,集体与个体是一个跨越很长时间的命题,甚至早于语言产生之前,人类文明开化之前。当我们把目光拉回一亿年前,胡杨林本身的存在就亟须我们思考怎么样才能将一个包含关系处理得更加随和(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人)。到了人类文明时代,部落出现了,每个生物文明都无法避免遇到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而每个生物文明的个体与每个地理环境又从属于整个生物圈。这样来理解环保或是共同体问题就会更加清晰。“舍小家为大家”最明显带来的是民族的凝聚性,但我们也不该忽视在实现集体目标中放弃个人幸福的过程。
而胡杨似乎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用向心力和自秉性给“孤独”二字以全新的诠释—孤独并不一定一个人行走,但必须一个人抗争。胡杨只有靠自己一次次挣扎着汲取水分,才能将不死的面貌展现给人们。而它面对自己痛苦时不言不语,才把美的力量发挥出来。
额济纳旗常是一望无垠的荒漠,上面点缀的荒枝拓印开的树影显得单薄,胡杨却是有声的。它的枝丫把我分解开,似乎我过往的罪孽就此一览无余,而我的苦难在它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在湛蓝天空的投映下,旅客很多,此时的自然伟力似乎在人类面前短了半截儿气势。而当我一个人面对一棵胡杨时,便已意欲臣服。这大概也是集体与个体的错节,如同胡杨盘踞的树根,将思考锁死在整片沙漠。
我很多次看过胡杨林,在不同的季节,一眼望去的胡杨林,四季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颜色。胡杨在绿的时候,总有些憔悴,反而淡化了它的独特,观赏的绝佳期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秋日,霜飔里屹然挺立的金黄,用大美冲刷着人们的心灵,你望向它们的时候,会涌起面对自然力量时的朝圣感,即使当下无人,寂静无声,自己心中的那口钟也会被敲响。胡杨树干相对短粗,枝干也有些错节,不长花,一棵树上的叶子也不尽相同,从美学角度看似乎不具备太多的美感。但沙漠绿洲的大环境却为无可替代的“胡杨美”做好了足够的铺垫。“胡杨美”不是停留于粗犷、豪放,这些使人心旷神怡的气质,就算在秋天,它也能展示出足够强的生命力。远处是黄沙遍地,抬头天空湛蓝,平视所见都是胡杨林的影子。这样“铁血柔情”式的英雄,用狂放的温柔守护着这片让它们经受苦难的土地。或许这才是大爱,一份深沉的回馈,一场无声的潜行。
除了与平日审美不同的色调美外,树的结构在摄影里也是绝佳的素材。意想不到的树杈形成延伸线,天与地的分壤自动为景色加了天然框,清澈的弱水河潺潺流动也能处理成倒影的分割。在动感上给人以静默印象的额济纳旗,于恍惚中流动起来。自然是艺术的取材,树开始与音乐联系起来。走神中,我仿佛听见旷野上的大鼓镗镗作响。而下一秒,耳畔又传来了《命运交响曲》的声响,贝多芬的呐喊那么清晰地传接至我的耳蜗。
在黄沙的压抑下,抗争成了唯一的命题。
在静谧的抗争中,泥黄色的树枝挑破夜晚的幕布,黎明便从黑夜中一泻而下。树枝无规律地生长,赋予了胡杨足够的奇思妙想。见证了胡杨的想象力后,我才明白这就是树的禀赋。屠岸写《树的哲学》时说树是“信念扎入地下,理想升向蓝天”,我想这不是树的本质哲学。先把自己想象成树才能去理解树,于是,我成为一棵胡杨,四肢寻找着适合的空间储放着,我的底盘稳稳地坐落,无止境地向下探去,用金黄的色彩在美学里踽踽独行。只有当真正用树的感官去聆听落叶的喘息,去感受黄沙的心跳,树的天性才展露出来了:生存的艺术。人有人的苦,树有树的苦,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所有的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艺术—胡杨在贫瘠的土地上深根的信念,向上的理想都来源于它对生存的渴望。说起树的哲学,我不禁想到德勒兹反对树状思维,提出不被层化的块茎思维。传统意义上,树状意味着单一权威,中心化,非线性。而当你好好观察一棵树的时候,或许曾经对树状思维的误解才会有所更正。我所见的胡杨,枝节点很多,逐级分叉,但主干的作用相对重要,因为可以沟通大地与天空。然而,当这种中心化一定程度地保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是否需要对中心化进行矫枉,将主干隐形,才能把树状和块茎的作用都发挥出来。
自然是简简单单的,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多孰是孰非或是人类拟人化的过度猜测,这样的过度解读虽非空谈道理,毕竟是有些许蛮不讲理。于是,当我脑海里翻涌的思潮过后,又是面对树的长时间的宁静,长时间的对视。对视,是的,我们平视着,这时,我与胡杨树是具有同等意义的个体。
我们都活着。
沉默给人以长久思考的时间(或许是发呆)。不知过了多久,我缓过神来,身边的旅客已稀稀拉拉,而我也转身往回走。
胡杨路上是没有径路的规划,朝东西南北全凭你的心情才好,只有这样没有安排而让你独自体味胡杨魅力的道路,才真正符合观赏胡杨的心境。
等我回到旁边的旅馆楼上,透过小窗,依稀看见若隐若现的胡杨树和大量的人影,看见自然得到了治理,同时也在一点一点遭到侵蚀。而在宣传保护自然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将自然过度美化了,像梭罗一样神化自然,而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的有益改造。答案是肯定的,可人类却在一边怜悯自然的同时,一边瓦解着自然。这样激荡的矛盾,在人类史上绝非少见,有时还会成为人对于自己复杂性“幽默”的开脱。
“决战狂沙同月醉,如花秋叶惹人怜。”看胡杨,我想了很多。离开额济纳旗时,胡杨已似个婴儿,重回襁褓之中。时间不早了,它们重新回到属于它们的大地上,准备入眠。也许,我用我的俯视对待它,本就是件不公平的事。
人类总是自以为是,无论是出于自私或是怜悯,他们总是以上位者的姿态凌驾于它们从属的世界,却又一边自吹自擂着为它们的生存保驾护航。
这么想时,我意识到我身上背负的是整个人类史的罪孽,于是我决心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它们就是这样,不管你在或者不在,不管世人用什么眼光审度它们。若你不去烦扰它们,它们就能一直立在那儿,一年又一年,三千年又三千年。
它们,是普天之下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