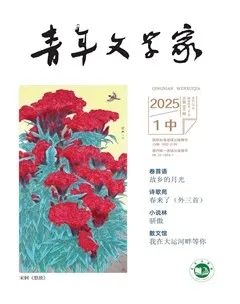老孔
老孔在县文化馆、县文联工作了一辈子,都是与文化人打交道,结交了不少文朋诗友。长年在文化系统工作的老孔,自称是孔夫子的后人,一直爱读书,勤写作,也养成了一个藏书的嗜好。
老孔是地道的县城人,住在城东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单家独院,一间旧屋,二层半房子,这是他祖上留下的老宅。因老宅为土木结构,楼板系杉板隔的,所以非常不隔音。儿子结婚前,老孔和老伴儿住一楼,儿子住二楼,三楼为阁楼,堆放杂物。儿子结婚后,晚上常会传出小夫妻的嬉笑声,让老两口儿难以入睡,加上城东靠河,地势低洼,春季大雨后易进水,非常潮湿,易引发老孔的风湿性关节炎,于是经老孔提议,将阁楼收拾妥当,老孔独自搬到阁楼居住。阁楼少有人上来,成了老孔个人的小天地。最让老孔高兴的是阁楼干燥,最适宜藏书。他老伴儿之所以没随他搬入阁楼,是厨房在一楼,她懒得爬上爬下。
独居阁楼的老孔更加热衷于读书、藏书,他从新华书店买来四个淘汰的大书架,把多年来的藏书全搬入阁楼,再分门别类,收拾得整整齐齐。退休后的老孔工资不高,而现在的书印刷、装帧精美,价格高,老孔常去新华书店看书,对一些新书爱不释手,可毕竟手头不宽裕,去得多,买得少。后来有一天,他在东门沿江路一带发现了好些旧书店、旧书摊,价格非常便宜,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欣喜若狂,每次来这里淘书,看这本想买,那本也想要,最后总是满载而归。
老孔性格开朗、健谈好客。常有文友登门来到他的阁楼喝茶、聊天儿,看到老孔那么多藏书都赞叹不已。文人都好书,一些文友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开口向老孔借。老孔虽爱书如命不舍得借,却又不好拒绝,只好忍痛割爱,并反复叮嘱看完后一定要及时归还。文友都应承道:“有借有还,一定的!”
文友走后,老孔马上拿出个小本子登记,以免自己忘记。有个文友借了本《安都地名溯源》,半年未还,老孔心里疙疙瘩瘩,催不是,不催又不是。最后,老孔还是拨通了文友的电话,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对方竟否认向他借过此书,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老孔认为书品亦人品,他决定不再与此人深交。
老孔为此书难过了好些天,他痛定思痛,觉得应想个对策。他用毛笔写了张纸条,上书“本人藏书概不外借”八个大字,欲贴至墙上,可又觉得不妥,有不少文友都是冲着他藏书而来的,有的来此找些资料,有的为读某部文学作品,还有的为某些历史争议问题寻找根据,再说自己偶尔也会向文友借书。思来想去,老孔最后决定,对向他借书者逐一进行登记,并让借书者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问题解决后,又有新的问题让老孔感到不爽。有些文友不惜书,还回来时的书总是皱巴巴的,或“缺胳膊少腿”的。为此,老孔总要对还回来的书“修理”一番,让书恢复“原貌”。
老孔的家人都不太爱看书,体会不了老孔藏书的快乐和借书的烦恼,对老孔的爱好既不干涉也不过问。老伴儿偶尔进屋收拾,老孔是不让她动他书籍的,老孔对自己的藏书了如指掌,哪本书放在哪个位置他一清二楚,哪本书变动了一点儿位置,老孔就知道有人进去过。
转眼老孔已过完七十大寿,恰遇国家棚改政策出台并快速推进。老孔住的祖屋也在棚改范围,这把老孔多年来的藏书梦击得粉碎。
老孔现在的祖屋一家人住着还算宽敞,加之一楼门前还有个20余平方米的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老孔看书写作之余拾捣拾捣花草,他觉得日子过得真是天上人间。可棚改实行的是货币补偿,不能拆旧建新,按棚改货币补偿政策算下来,老孔祖屋连带院子只可补到110余万元。
晚上,老孔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购房事宜。
大多拆迁户都面临要重新购房,以至于县城房价一下飙升,每平方米突破万元。老孔掐指一算,棚改补偿款加上这些年一家人的积蓄,满打满算可买套120余平方米的套房。
老孔一家人几乎走遍了县城所有的楼盘,经反复对比讨论,终于在梅水湖畔购买了一套三居室的精装房。
看样板房时,老孔的儿子与儿媳就谋划好了,他们住主卧,老孔读初中的孙子住次卧,剩下那个只有10余平方米的小房间就归老孔夫妻俩住了。
老孔想到搬入新房后,摆进一张双人床后就再放不下什么东西了,他在为那些藏书的命运和归宿考虑。
细心的老伴儿察觉出了老孔的心思,劝老孔:“你那些书赶紧去处理吧,这旧房一拆,搬进小套房,哪里有你放书的地方?”
老孔默不作声。
一日,老孔到旧书店溜达后空手回来,听到儿子与儿媳压低嗓音正在说话:“我们这老房子要拆了,你爸那些宝贝书籍怎么办?”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叫他清理后卖到旧书店去吧。”“我爸肯定不会干的,这些书都是他的命根子。”“那搬家后,这些书放到哪里去?”“让他用纸箱装好,塞进他床底下吧。”“那也放不下呀!”
“我爸也真是,一大把年纪了,还折腾这些干什么?”“他不舍得卖掉,等他百年之后,我们用不着迟早会给他卖掉。”“那倒也是。”老孔耳朵不背,两口子的话他可听得一清二楚。
那晚,老孔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老孔收拾了百来本他实在不愿舍弃的书籍,用纸箱装好,准备搬家时带入新居。剩下的那些书,他不愿糟蹋,按称卖掉。他想为这些书找个好归宿,发挥它的作用。
此后,只要文友来访,临走前,老孔便会热情相劝:“就要乔迁,这些书也没办法全搬过去,你挑几本喜欢的带回去,我送给你。”文友们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惜书如命连借都难的老孔怎会把书送人呢?后来,看老孔说得那么认真,也就不客气了,一个个都捧着自己的爱书满意而归。
消息一传开,老孔这儿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当初限期三个月搬出老宅,老孔几十年来的藏书不到两个月就处理一空。
搬入新居后,三代同堂的老孔失去了自己的小天地,文友少有来往,老孔仿佛换了个人,变得郁郁寡欢、少有言笑,人一天天变瘦,后来竟一病不起,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肝癌。
老孔的病情日渐恶化,他预感来日不多,将精挑细选留下的那几箱书籍吃力地从床底下搬出来,整理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有文友再来看他,他会颤抖着双手递给文友一两本对他们有益的书籍,轻声说:“谢谢你来看我,这书你用得着就送给你做个纪念!”
临终前,老孔床前仅剩下六本他个人所著和编撰的书籍,他交代儿子,待他走后,一起火化,随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