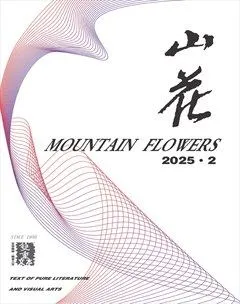佛光普照
一、长生的护佑和关照
时节是大规律,人们按照规律过光景。
我无法想象更为具体、真实的情境。盛唐的唯一见证是一位坐了千年的女子,在“佛光寺东大殿”,一席之地,光照不到的地方,于我而言是神秘的。我从未见过有神灵的存在,她,宁公遇,在一个薪火相传的时间流程里,经由一位叫梁思成的先生的文章,呈现在世人面前。瓦楞上的枯草,殿后的山脉,永不停止的风,这些组成了一张网,让生命得以循环。
第一次遇见,大约是1998年,一个阴雨天。憋足了劲的雨并没有下很久,很快云层的轮廓变得清晰,我辗转来到佛光寺。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时的乡村和田野没有那么沉重,大地涂抹了一层明黄色彩,是挤出云彩的光照。山野被夕阳激活了,光是最好的修饰品,一切都停在那个时刻。真实远离了现实,那个年龄段的我也仅仅只是缘于自己简单的张望:我来过,知道了“宁公遇”。
她和周围没有强烈的对比,似乎在隐约之中,又似乎并没有她的存在。伴随着声音、气味、季节的交替,一闪而过的光使大殿灰暗下来。那一瞬间,我看清楚了她的模样,并映在了脑海中。
宗教,是信仰土地者的仪式。土地不仅给我们粮食,还给我们最终的住所和传承的渠道。过往的生命之上必定是新的生命,宗教犹如河流,悉心编织它的脉络,把小块的天地与房屋连接起来,只要我们双脚站立于土地之上,就必定能感受到它的呼吸。
1941年7月,英文版的《亚洲杂志》中刊登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篇文章——《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其中,他特别提到了:“这所古老的佛殿是由唐代一妇女捐献的!千年之后,年轻的女建筑学家,也是一位妇女,成为了第一个发现了这所中国古代最难得的珍贵唐代木构庙宇之人,这显然并非只是巧合。”
文中唐代妇女指的是宁公遇,年轻的女建筑学家便是林徽因。而她们的这场相“遇”,看似一场偶然,却如同天地在视野的尽头交汇,很蓬勃,很打动人心。
冥冥之中一场缘分下的四目相对,引得后来人津津乐道……
寺庙是承载社会劳动人的精神的场所,历史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朝代的更迭,人祸和灾难,没有改变那些像汪洋一样的底层人群的命运。他们对土地的遵从,虚像或者是远景,在不断接受一个个价值,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流失之际,他们被历史驱离,像散落在典册与生命旷野之间的流星,倏尔在大地的腹地显现,顷刻间就又消散了自己的踪影,重复的劳动,在传递着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
人总是有罪过的,无论多么完美的人。
于是,有了宗教,彼岸在不远的前方。
每一个时间段里,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属于这个更为宽泛的程序或环节的连接点。
佛光寺的连接点上,宁公遇守护着寺庙,从容地与悠长的安宁交融,并获得了一种长生的护佑和关照。
二、缘起敦煌
白驹过隙,昼在大地的腹地萌生,夜又止于它的尽头。
历史以沉默的方式存在,世间的丰功伟绩太多了,人拥有了基本需要的获得和大地持续永久的供养,人应该知道,更高的规律更应该服从于简单的道理。
寺庙,万物竞存的道理歇息处,它给人退路,宽厚地承接了多数穷人的依从,依靠经年的实践,使生灵逐渐心有皈依。
佛光寺坐落在豆村北面的峨谷山沟壑的深处。峨谷山北起代县峨口镇,南至五台豆村镇,总长50公里,分布着白云寺、圭峰寺、秘密寺、峨岭寺、古法华寺、古竹林寺、佛光寺等十余座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大寺,是五台山除清水河谷外的第二条寺庙密集带。
可以想象一下从前,寺庙坐落在山林之间,云雾缭绕,云在寺庙所在的山脊上最富于变化,它们展尽自己的身姿,会出现“山从人面起,云旁马背生”的景致。
五台山古属代州,而从代州上五台山最近的道路就是峨谷,这使得峨谷成为了历史上重要的朝台古道,五台山四关之一的西关峨岭关就坐落在峨谷之中。那个年代,居于山林的人心灵与躯体是一致的,灵魂是虔敬的,而居于城里的人却那么浮躁狂妄散乱。
1937年6月,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山鼻祖梁思成携妻子林徽因,曾沿着这条千年古道踏上寻觅佛光寺的旅途。战乱使人心惶惶,而此刻的他们却是沉静的,处于身心最健康的状态,浮躁和喧嚣这类杂音已经摒除在外。他们来山西寻找唐木构建筑,不仅仅是证明给日本人看(因为当时日本人放出话来:“要研究唐代木结构建筑,只有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来!”),也是要证明给自己看。是对建筑的爱,在动荡的世事中,引领了他们的方向。
梁思成20世纪二十年代先后就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是中国第一代受过正规教育的建筑师。在出国之前,他就知道了,中国建筑文化,是东方所独具的一种“大地文化”,也是世代中国人与大自然不断进行亲密“对话”的文化。中国文化建构于东方大地,它所传递的是一种属于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信息。从自然宇宙角度看,天地是庇护人生的奇大无比的“大房子”,此即《淮南子》所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为庙”;建筑象法自然宇宙,所谓“天地入吾庐”。又因为中国人的时效性观念,对宗教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淡泊,“淡于宗教,浓于伦理”,也使民间寺庙建筑向来“重文史,轻技艺”,建筑艺术只是作为一种工艺技术在匠人手中相传,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艺术”来对待;所以,也就从来没有人对中国古建筑作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以致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大地上早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了。
生命注重的是自身的尊严和高贵,虽然个体的光焰很难融入历史,但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山阔水长的背景,那就是国家和民族。战乱中的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做出了不合时宜的事——去山西寻访唐代木构建筑。
山西,恰恰是对土地信仰最茂盛的地方。
个体生命不可能全方位配合历史,而人类正因为有了一批不合时宜的人才显得丰富多彩。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1932年开始,便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遗存的古建筑。这是他们的一个宏愿,是他们人生时间段上的一个刻度,是在没有起始和终点的时光之流中,寻找心中的“历史”作为区分的界标,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感定向。
十五年间,夫妻二人共调查古建筑2738处,辽金时期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应县木塔,宋代的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太原晋祠圣母殿,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筑先后被发现了,其中却没有唐代的建筑。梁思成很苦恼。他隐约担心中国古建筑在“不求原物长存”的文化观念下,忽视了建筑古迹的保护,更热衷于建筑物天摧人毁之后的重建。
重建,比如武昌黄鹤楼的重建已有二十次之多,每一次重建并不是对宗教的皈依,而是对重建之物形象所传达的伦理传统的重新认同,但是,这对建筑的伤害是彻底的。
梁思成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建筑史料时,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绘制的《敦煌石窟》第六十一窟的宋代《五台山全图》,图中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他的注意。
莫高窟第六十一窟北墙,就是名满天下的壁画《五台山全图》,画面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全景展示了五台山周边方圆五百里的山川地形和社会风情,共绘有城郭、寺庙、楼台、亭阁、佛塔、草庐、桥梁等各类建筑一百七十多处。
据介绍:
长庆四年(824年)吐蕃赞普使者向唐王朝求五台山画样,开成五年(840年)日本僧人圆仁朝拜巡礼五台山,同时期的汾州和尚议圆巡礼完之后,请画博士画五台山图一幅赠给圆仁,让他带回国供养,于是五台山图便东传日本,西入吐蕃,实际上西传的地方并不仅在吐蕃,还传到了河西及中亚一带,五台山便成为佛教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世界供奉了一幅“五台山全图”。
《五台山全图》,一个在现实中,一个在信仰中。
莫高窟是丝路上的佛教胜地,东来西往的僧侣必然会来此停留巡礼,他们所带的五台山图必然会留在此处。地处敦煌的佛教徒怀着向往崇敬中原佛教胜地的心情,将五台山图绘制在敦煌第六十一窟的墙壁上,绘画是有声音的,它提醒人不要忘记了来路与归途。现存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与五台山有关的画卷,而且大部分都是五代曹氏家族统治时期所写。《五台山全图》采用鸟瞰式透视法,描绘了五台耸峙,萦回千里的境界及五台山周围数百里的山川景色。全图不同于其他经变画,它描绘的是当时五台山一带的社会生活场面。
《五台山全图》长13.4米,高3.4米,规模宏大,是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展现了山西太原途经五台山到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方圆250公里的地理形势。图中所画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各种菩萨化现景象,莅临五台山上空赴会;中部描绘的是五台山五个主要山峰以及大寺院情况,又有各种灵异画面穿插于五峰之间;下部则表现通往五台山的道路,包括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沿途的地理情况。全图以鸟瞰式透视法,描绘了五台山萦回千里的境界:朝拜中台文殊大殿的两条大道,山峦起伏处众多高僧说法,信徒巡礼,天使送供,香客朝拜,还有道途中百姓割草、饮畜、推磨、舂米、开设客舍及店铺。人物在图中三五成群,结队而行,到处都有人物的活动场景。这其中,寺庙是最生动的建筑,从画面上看,它们宁静又跳跃,像春天万物茂盛生长那样五彩缤纷。
希望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在绝望当中的。也许生命从来就不是为了某个回答而存在,但寺院的存在一定有它的缘由。
《五台山全图》点亮了许久以来的疑惑和困顿,梁思成欣喜地查找了明代镇澄法师的《清凉山志》,得知佛光寺不在五台山寺庙群的中心区。
书本决定了方向。
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莫宗江和纪玉堂两位学生来到了五台山。在豆村,因为山路崎岖,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换乘骡子入山。那时的山路不像现在平展,十分陡峭,进山的几条路彼此呼应,每一条路在伸展开之后都与别的路发生关联,所以常常走错方向。走向山巅,在高处完全开放的视野里,他们获得了一种舒爽的凝视。
对道路的注目变成了目光笼罩、俯视,时间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停顿。
走入峨岭关下沟川的阎家寨村,与佛光寺正对着,通往寺院的小路由村边岔入。村子的正东面,但见三山环抱,气势巍峨,佛光寺雄踞山腰,坐东向西,背有靠山,左右有护山,迎面开阔,雄视着远处的高山和河流。
寺庙的钟声响起,终于,笼罩在绚烂余晖中的佛光寺迎来了无限虔诚的造访者。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只是在心里,他们期盼着。
想象那深远的出檐、硕大的斗拱,清晰又模糊,梁思成感到浮在眼前的佛光寺在暗示什么,他下意识地回过头,空空的路旁几匹骡子打着响鼻。这是一座时间停止的舞台,四处的风景仿佛正凝神谛听一个久远的声音。他不能确定,但是,唐代木构建筑一定不会存在于“台内”。五台山的五座山峰环互而列,当中腹地为“台内”,五峰的外围称“台外”。台内是文殊菩萨道场中心区,向来得宠而厚遇,不乏历代帝王青睐,高官富贾亦多出重金布施,香火极盛之地必然修葺不止。唯有台外,交通不便,祈福进香的人少,寺僧贫苦,香火寥落,因而使得古刹保持了原样。
他的妻子林徽因在夕照下微笑着,她也在耐心地眯着眼睛审视着周围,如此安静。日子和日子过去了,这些加起来的日子是多少生命的消失?他们仿佛在验证一个自己的预感,这里可能真藏着一座唐代的木构古建筑!
因为不确定,他们的停顿和接下来的投入将变得漫长。
我不知道神示谕人间是什么情景。这既像一部封存已久的宝藏被突然打开,又像一颗沉入海底千万年的明珠重新现世。
三、宁公遇活在倒流的时间中
昼与夜的边缘,落霞尚未褪尽,一行人沉浸在微风中,一抹余晖将殿宇映照得格外亮眼。
照壁前的山洼里老树婀娜。天色已昏暗,依稀可见寺后的东山坡、寺左的南山梁,松柏一片青碧,蔓延到寺院的红围墙旁。山门前平台高筑,影壁立于平台边缘,上书“佛光寺”三个大字。
从韦陀殿的入口到寺内,因为年久失修,佛光寺似乎远没有当初的风采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坐北向南的金建文殊殿,结构奇绝。院中又有一座石经幢。理想中至美情境的到来使一行人无比激动,连日来舟车劳顿的疲劳和身体的诸多不适,一下子全然消失了。
中间一层院落,除东面是石券窑洞外,南北都是清式的小阁殿堂,是后建的客房。
院台很高,下面筑石券窑洞,洞上再砌石壁,一排窑洞中间又砌陡峭的台阶通往上院。通过倾斜七十度的台阶,时光像攀爬绝壁悬崖的藤蔓,跳过眼前的现实,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大殿巨大的斗拱,它们有力、简单,出檐深远。
梁思成从经验判断,那是比辽代还要久远的木构,它会早于之前所知最古的木构建筑吗?
大殿坐东向西,也可称东大殿。殿的立面,只有上到台上才能观其全貌。殿前有刻工秀美的唐代石经幢一座,两侧有粗大的松树夹立。殿南侧还有一砖塔,形式很古,应为魏齐原物。
夜幕降临,明月当空,四周静极了。
他们愣在那儿倾听时光的回溯。虽然没有足够的肯定,但正如李白的《古风》所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作为中国古代最强盛的历史时代,建筑是唐代这一历史“巨人”屹立于东方大地的伟大身影,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它所具有的英雄史诗般的恢宏气度和不可抑制的内在激情。日影下的阳刚之气,成为了那一时代光辉的文化标识。
阳光普照,土地以炊烟般的质朴迎接了新的一天。
佛光寺作为佛殿,它的建筑形象没有任何神秘、阴怖的风格特征,造型风格类于唐代宫殿,是一种神圣、明丽、雄巨的造型。那是一种时间凝固、事物都停顿下来的特殊感受。打开正殿之门,有释迦玉石像,其“佛体肥硕,结跏跌坐在须弥座上,发卷如犍陀罗式。”正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平面为长方形,采用“内外槽”平面布局,以列柱和柱上的阑额构建内外两圈的柱架结构,“再在柱上用斗拱,明乳栿、明栿和柱头枋等将这两圈柱架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支持内外槽的天花,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内外两个空间,而在天花以上部分还有另一套承重结构。”
佛光寺东大殿的屋架结构颇为复杂。
梁思成和林徽因通过斗拱处的一个洞进入到斜坡殿顶一间藻井处。由于黑暗无光,仅能靠打着手电筒经由檐下的空隙小心攀爬进去,所经之处,皆积了厚厚几寸的尘土。手电筒照往殿梁的结构处,他们看见了蝙蝠,不是一只,是上千只。成群结队的蝙蝠聚挤在檀条处,重叠在一起。蝙蝠两耳尖且细长,眼睛虽不大,但隔着几米都能看见它眼里泛出的瘆人的猩红。它们的吻鼻部有复杂的叶状突起,鼻叶两侧及下方为马蹄形的肉叶,中央有一向前突起的鞍状叶,手电的亮光下,整个画面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和恐惧。
为了安抚妻子,梁思成漫不经心地讲蝙蝠类是唯一真正能够飞翔的兽类,它们虽然没有鸟类那样的羽毛和翅膀,飞行本领也比鸟类差得多,但其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特别长,并支撑起了一层薄而多毛的,从指骨末端至肱骨、体侧、后肢及尾巴之间的柔软而坚韧的皮膜,这也形成蝙蝠独特的飞行方式。
林徽因抚摸着木梁,看着前方的斜撑,那厚重朴素、质感强烈、色调沉着的粗木。看见那些悬挂着的蝙蝠时,她心里悚地如冰水漫过,脚步恍若踩在鲜花或刀尖上一般,她给了丈夫一个无声的回应。
殿内的木梁上除去蝙蝠,还到处爬满了臭虫,灰尘积有三四厘米厚,脚踩上去如同踩在棉花上。也许是为了吃蝙蝠血而扎堆于此的臭虫被人惊扰到了,它们开始趋光架起翅膀乱飞。
大概真是上天的旨意,无论是从人情还是地理上,让她领受这无法言喻的情景——一个女人,她的嘴角线条分明刚毅,眼睛明亮、隐忍,直面着这些存在。
我看见过梁上宿居的蝙蝠照片,那是看一眼都叫人浑身汗毛倒竖不忍再看的画面。
梁思成举着相机,准备拍下殿顶的结构以作记录,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蝙蝠见光惊飞,一股腐烂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尘土携带着虫鸟的粪便抖落,呛鼻呛眼。林徽因忍着这呛人的尘土和难耐的秽气,和丈夫、学生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身上和背包里爬满了落下的臭虫,脸颊和脖子上开始被臭虫袭击,浑身奇痒,但为了工作顺利开展,她依旧坚持测量、拍照、记录,大家分工合作,尽可能一点不漏地详细记录与绘制。
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说过林徽因作诗的“仪式感”:“她常常在晚上写诗,而且还会做很多准备工作。比如,点一炷香,摆一瓶插花,身穿一袭白绸睡袍,做完这些后,面对一池荷叶坐下,在晚风中酝酿佳作。”
消逝的年代里,这只是部分片段场景,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她站立在蝙蝠和臭虫中的身影,世俗社会刻意关注的是她的风花雪月。
若干年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消亡之后,2024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傍晚,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宾大正式向林徽因颁发了建筑学学士学位,以表彰她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先驱的卓越贡献。这是一份迟到近百年的学位证书。弗里茨·斯坦纳发表讲话说,“有一句话是,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女人……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伟大的建筑师,但今天,林徽因没有站在梁思成背后。”
林徽因的外甥女于葵,在林徽因追授学位座谈会上说:十七岁那年,林徽因从欧洲游学回国时即认定了自己“事业的模样”——立志要成为一位建筑师。她陶醉于伟大时代的建筑作品,着迷于美学、科学的融合,沉浸于人文、历史的厚重……她只身闯入了一个本属于男人的世界。林徽因的选择,使她面对的不止是求学的难题,那是她一生的挑战,她遭遇的困难将数不胜数。当年,在中国,建筑学尚是一片空白,建筑仅仅被看成是手艺、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这个领域更与女子毫不沾边。而她却要为祖国带回一门新学问、新学科,要成为新一代的女建筑师。
历史绵延无尽,而与此相比每个人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在与时间漫长的较量中,林徽因,是我永远的仰望。
或许是快乐本身有它特殊的含义,不只是看见和幻觉中的慰藉,当梁思成确信这是一座唐代木构无疑,可又不知该怎么报告这座古建筑的具体建筑时间时,林徽因以她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发现了藏在凤梁底部隐隐约约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字样。对于这无法言说的喜悦,梁思成是这样记录的:
我妻子注意到一条横梁下有很淡的字样,这个发现于我们而言犹如电击。没有比确定这座古庙具体的建造日期更让我们喜欢的东西了,我们知道这座辉煌的大殿是座唐代木构,可唐朝前后几百年,到底是哪一年呢?正是妻子发现的木头上淡淡的字迹,让所有人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答案。当其他人准备在价值连城的塑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认题字时,我的妻子早已踮着脚尖从各个角度辨识出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阵努力,她认出了一些不太能确定的唐朝官职人员,同时,也认出了最右边梁上“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13个字。
这座珍贵的唐代庙宇竟然是一位妇女出资建成的。
生怕有误,灵光闪现,又赶忙跑到殿外的经幢石柱处,再次核实上面的题字。这一次,又在长长的唐朝官名中再次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同样写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字迹,并且,确定了建造日期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时间开始后退,在时间与历史联结的交叉点上,宁公遇盛装出现了。
四、生命因守护而不老
寺庙的僧人指着佛殿上一尊盘坐在角落的女子塑像说:“那是武则天。”
此刻,林徽因立马再次走到那位面目谦恭的女子面前,原来,她并不是这座寺庙的寺僧所说的“武后”,而是这座庙宇的女施主宁公遇。
权力永不会放低身段。
有幸与宁公遇相见,这遇见只存在于她们之间,如果有秘密,也只是单向性的。一个在现实中,一个在历史里。寺庙的供养人,宁公遇呈现出一种梦境一样沉静的美,她是谜,是气息,是显露在存在之上闪耀的光辉。
林徽因久久不能移开目光,她遥想着这位女子该是凭着怎样的信念捐出家产修建了这座庙宇,当庙宇建成后,又以何念将自己永远留在了这里,日日听着暮鼓晨钟与诵经声,以谦卑之态守护着缭绕的香火和青灯黄卷。一千多年后,两位女子在此地四目相对,林徽因走近她,一手托在她的肩上,阳光一抹柔亮的光送到她们身边。
林徽因说:“我愿意陪你再坐一千年。”
梁思成用相机给妻子和这位“女弟子宁公遇”塑像拍下了一张合影。被完全陶醉的物我两忘的生命体验,被纳入一张合照,它的背景在构筑着大地上最宽敞、最清静的佛光寺,殿外,凌翔于生命的天空出现了长着翅膀的狮子云。
生命里的每一天,一切既不可选择也不可期待,岁月可以选择的仅仅是如何对待这似乎可以无限延伸、不断重复的情境,后来的许多人也曾遇见过,只是顷刻间就沦落成了人间。
从遥远到遥远,清晰而又模糊。四处的风景仿佛正凝神谛听一个悠长的回音。
佛祖说,人一出世便是苦难的开始。佛光寺也有人生般的际遇。和消失相比它是幸运的,幸运地遇见了宁公遇,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面对万山丛,面对无言的青山,湍急的溪流,残留于悬崖峭壁之上的石梁、碑刻、庙基、琉璃残件,遗痕处处,让人为古人的胆识与智慧激动。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形制,而不是别的形制?天地是一本大书,历史中一些角落需要人去探幽发微,需要人去思考追问,如梁思成、林徽因与古代的宁公遇,薪尽火传,代代相袭,方使中华文明流传不息。
历史上佛光寺规模十分宏大。
相传,北魏时(公元471—499年),孝文帝朝拜五台山,至南台顶,天色将暮,忽见峰西放光,照彻虚空, 以为文殊灵迹,于是创建了佛光寺。到了唐代, 佛光寺置有五大院,即,南禅院、白云院、华严院、单禅院、各寮院,又有法兴禅师,大约在元和至长庆年间(公元806一824年),在佛光寺“建三层九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这是有记载的。民间也流传有“骑马关山门”的说法。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毁佛灭法,“五台诸僧多亡奔”,佛光寺三层九间高九丈五尺的弥勒大阁, 以及其它殿堂,都毁于一旦,仅留祖师塔在寺。尔后,对佛光寺建筑做过贡献的,就是愿诚禅师和女施主宁公遇了。
自从会昌五年灭法,佛光寺只有愿诚和尚孤身独守。唐宣宗时佛法再兴,愿诚想到他当年在长安时,认识一位女居士宁公遇,是位好善乐施的居士,想去找她一回。
唐宣宗大中五年,愿诚辗转到了长安,会见了女居士,诉说了想重建佛光寺的宏愿,女居士欣然赞助。这样,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就在原弥勒大阁旧址上重建了单层七间的东大殿。
金熙宗天会十五年 (公元1137年),又修建了文殊殿、普贤殿、天王殿。元代,佛光寺曾一度衰落,明宣德年间 (公元1426—1435年),河北省蓟州游来一僧,法名本随,号照庵,重新整顿了寺院。他有八大门徒,每徒发给化缘簿,各走一方募化布施,补修东大殿,新塑罗汉二百九十六尊,维修文殊殿,并在两山墙绘罗汉二百四十五尊。
至此,佛光寺由以前的十方常住改为子孙庙。
子孙庙是指小庙,是寺庙形态之一种,区别于规模较大之“十方丛林”而言,寺庙之财产多为一僧或一系僧众所私有。
佛光寺东大殿,唐木构、泥塑、壁画、墨迹四种艺术荟萃一处,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来看,都至可宝贵。东大殿檐柱的柱头微侧向内,角柱增高,建筑学上所称的 “侧脚”和“生起”都很显著,这样,便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力。殿的转角挑起,如大鹏展翅。前檐柱础作覆盆宝装莲花状,即如盆子倒加,雕莲花,每一莲花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这是唐代最通常的建筑风格。柱头之上没压普柏枋,直接承托斗拱,又是唐建之一证。当把东大殿和其下的文殊殿作一比较时,就发现金代文殊殿的檐柱头上压了枋,斗拱没与柱头接触。东大殿肥硕雄健的斗拱,承托着深远翼出的屋檐,传递着梁架承载的殿顶荷重,将力送到各柱。斗拱称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无论在力学上还是在美学上,都叫人赞叹不已。
从殿内三佛的头发看,释迦和弥勒二佛为螺发,阿弥陀佛为直发,发型作陀罗状。三佛的衣饰、塑制工艺极高,衣纹流畅,折皱分明,如真衣一般薄而贴身地披在身上。
遗憾的是民国初年重新着色时,被变为龙袍衣料,既过于艳俗又十分唐突,幸亏这些都是纸裱后着的色,有脱落的地方仍露出了当初淳古的色泽。
宁公遇称“佛殿主”。与她的姓名同列在一梁下的,还有“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后人推断,这个功德主大概就是元和长庆间的宦官王守澄。宁公遇与王守澄的关系看来颇深,唐代宦官多有娶 “妾”的,很有可能宁公遇或是王守澄的“妾”, 或是王守澄的“养女”,至少也是深受王恩宠的。
佛光寺另一守寺人愿诚和尚,他的等身像身披袈裟,盘腿打坐,看起来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表情宁静凄戚,弧弯的眉毛,扁长的眼睛,显出虔诚专注的样子,前额隆起,颧骨突出,蒜型鼻子,和棱角分明的嘴唇,又显出刚毅的性情。
《宋高僧传·愿诚传》记道,其“少幕空门,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志。……礼行严为师。……严称其‘神情朗秀, 宜于山中精勤效节。’”他落发为僧,在会昌五年灭法时,寺僧多亡奔,“唯诚志不动摇” 。
宁公遇自此在佛光寺盘腿安坐了下来,她清澈的眼神,淡然又坚定,纯净地凝视着这个世界的变迁。
一切因为不动摇,唯有不动摇永恒不变。
五、佛光寺在树荫里丰盈着人心
建寺和护寺同等的重要。
七间木构建筑的普贤殿、五间木构建筑的天王殿,都是因护理不慎,先后于明崇祯年间和清光绪年间被火焚烧,同期的金代建筑仅留了文殊殿。唐代瑰宝东大殿,在现代也曾历过险。那是在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殿内香斗里的香头被煨着后,越煨越旺,靠着香斗的金柱也同时被煨着了。正当危急之际,正好老和尚澄溪(他每天晚上要到东大殿的殿院拜佛)发现殿内有火光,从门缝看见烟火已在经案底下直冒,柱底也有了火,急忙呼叫众僧,全寺僧人迅急赶来,凑巧殿院存有积雪,众僧齐心铲上冷雪扑灭了火焰。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到来,犹如明月降临。
寺庙建筑中,殿宇的建造年月,多写在脊檩上,这座殿因为有顶板,梁架上部结构都被顶板隐藏,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留存着些许字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在“春归如过翼”“流年暗中偷换”的丝丝怅惋中,感叹只有比火还热烈的寻找,只有那双专注着的眼睛才能闪耀出天地间的传神秋波。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出现也许什么也不表示,只显示了黑夜的纵深。
1953年,佛光寺成立了古迹保养所,到1961年,又第一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与他们夫妻二人的探寻有很大关系。一次虔诚的探寻,让人类瑰宝得以再现。什么都可以变,唯有一张两位人物时隔一千零八十年,林徽因和宁公遇合影的照片并没有到风烛残年。
林徽因说:“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让自己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供养人,是指信仰佛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像、开凿石窟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正是因为历代“供养人”的虔诚,才在经年累月后修建了大地上的庙宇和洞窟。供养,是指佛教信徒施舍资财,或以崇敬、赞叹、礼拜等精神性活动来供奉、礼敬佛教三宝——佛、法、僧,是佛教僧俗信徒的一种重要的修行功德活动。佛教十分重视造佛形象来用以供养、礼拜。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阙译人名出《后汉录》的《佛说作佛形象经》载优填王说:“佛去后我恐不复见佛,我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之。”这表明了造佛形象对于佛教信徒在佛涅槃之后礼拜、供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中国佛教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佛教僧侣信徒造佛形象、供养的记载,一般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为集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每人一像;
第二种,为结社合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为“邑社”社人;
第三种,为一人或一家出资独建洞窟。
佛光寺的守寺人,支撑他们灵魂的是他们至今依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他们守着时间,那是多么宁静而又充满自由意志和铺排的静守,时间从他们的眼睛中流走,从盘腿合掌的指骨间滑落,从肌肤上漫过。这个守护的过程其实是空虚的,对生存的实质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们的生命却为着这个守护而穿越了世事沧桑。
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我被他们非凡的执念“不动摇”所吸引。
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是不动摇,是时间。
梁思成说: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