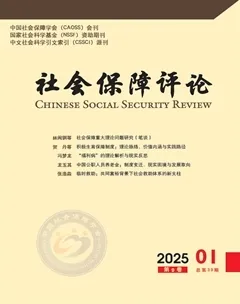儒家慈善救济思想的伦理意蕴及当代启示
[摘 要] 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及其活动源远流长。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中心构筑的慈善文化,其所蕴含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等内容,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印记和文化性质。儒家慈善救济思想以伦理为本位、以教化为途径、以“同善”为理想,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义务关联和伦理关照。这一伦理指向针对传统社会中的贫富差距问题、慈善救济的原则及理念等问题,提供了深刻洞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扶贫济困的救济精神,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塑全球伦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儒家;慈善;同善;教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主要以伦理本位为特点,以血缘亲情为基点,不断扩充而形成“亲亲-仁民- 爱物”的伦理共同体,其中的共同体成员被置于各种“伦”的相互关系之中并形成相应的情感联结和义务关联。在这一相对稳定的伦理结构中,如果其中的成员一旦陷入类似“鳏、寡、孤、独”的穷困境地,家(宗)族其他成员则有责任和义务对其伸以援手,或在经济上彼此照拂,或在伦理上相互顾恤,从而保障整个家族共同体的伦理和谐及共生发展。由家庭(族)血亲之间的相互顾恤亦可不断推向社会,形成一种“社会的家庭化或曰伦理化,乃使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也对他负有义务。”a 总体看来,以儒家“仁爱”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慈善救济具有明显的伦理救助取向,具有与西方宗教救赎不同的文化性质与文明意义。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伦理观念不仅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慈善领域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贫困”问题的伦理关照
扶贫帮困、守望相助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内在向往和追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a“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b 皆是传统社会对“大同世界”的美好设想。然而,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作为人类社会固有的顽疾,却始终与这一“大同”理想形成现实性鸿沟。因此,历史上针对贫困人口的救助向来是传统社会救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历代以来扶贫的救济理念和措施仍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一)“贫”“困”等相关概念及其价值导向
从词义上看,“贫”一般与“财”相关,与“富”相对,财乏曰“贫”。《说文》中对“贫”的解释是“财分少也”;《庄子·让王》中也提到“无财谓之贫”。c 与“贫”相关联的词语有“贱”、“困”、“穷”等。“穷”、“困”二字含义相对较为丰富,既有物质上的匮乏,也有精神上的困境,如《论语·卫灵公》曾提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d 其中提到,孔子及其弟子在陈国滞留期间,遭遇了粮食断绝的困境,跟随孔子的弟子们因饥饿而病倒,子路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和困惑,便提出了“君子亦有穷乎?”e 这一问题。孔子的观点是,君子即使在困境中也能坚守道德底线,保持节操和本分,而不是因此自卑堕落。一般而言,由“贫”可生“困”,反之亦然;不过“贫”或“困”却未必一定导致“卑贱”处境或心理。“贱”本为“买少”之意,与“贵”相对,后指地位卑下,即“乏财曰贫,无位曰贱。”f“贱”一开始并无贬义之谓,而仅与社会等级的分层有关,贫者并不必“贱”,而且士人往往赋“贫”以“义”,从而保持精神上的满足,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g 的“安贫乐道”之追求。可见,与“贵”相对的“贱”并无道德上的贬义,主要指“无位”之属,而与“良”相对的“贱”则带有较强的道德身份并让人引以为耻。h 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上述词语所指之义实际上是交互综合使用,并构成“贫困”、“贫贱”、“穷困”等特殊语境,它们既具有事实指向如无财、无位之属,也存在某些价值导向如由于某种伦理关系缺陷或由自身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生活困境。孔子与弟子子贡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i 孔子在肯定子贡观点的同时加以提升,并指出关于贫富的不同精神层次。一种是“贫谄而富骄”,即朱熹所谓“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的病症;其二就是子贡所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是知“自守”却仍然困于“贫富”之囹圄;第三种则是孔子提倡的“贫而乐,富而好礼”的超越境界,贫富的关键不在于贫富本身,而在于能够“安贫乐道”。孔子以“仁”为判断标准来衡量君子德行,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j 不仁之人既不能久困于贫,也不能久处于乐,因为两者都可能使其失其本心,久贫则“为非”,久乐则“骄佚”,故“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a 在孔子看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还不够,最好是做到贫而乐、富好礼。从个体角度来说,仁者安仁,富贵、贫贱皆以“道”处之,如颜回虽贫却乐道,尽管其处于“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生活境遇,却不以贫为忧,不改其乐道之志;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孔子则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b 国家有责任治理贫困问题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为“慈善事业的起源是贫富不均,其作用就是缓解这种不均所带来的痛苦——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
(二)伦理的救济原则和“养民”措施
根据儒家所强调的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对每一个体(无论贫富与否)提出相应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要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实施适当的养民措施。因此,针对“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d 抑或“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e等情形,儒家希望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规范来应对,既强调个体层面的道德自觉,也强调社会、国家层面的伦理关照。
其一,伦理上的救济原则。在以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族)在个人诸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则以“情理”彼此顾恤,并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社会的“贫困”之所以构成社会问题也是因为某种伦理上的“缺陷”,而不只是物质上的匮乏。例如,孟子曾提到鳏、寡、孤、独此四者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f 之所以是“无告”,意味着此四种情形是人生之最苦,身处苦难境地却无亲可诉、无人相依。《礼记》中也将“鳏寡孤独废疾者”作为日常生活中贫困人口的界定,g 而《周礼》中所提到的“保息”政策中也同样涉及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方面。h《管子》一书中所提到的九惠之教就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和“接绝”,其中还对“匡急”和“振穷”作出区分:“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i 长老、幼孤、鳏寡等为“匡急”之事,此为民之所急而不可无者。相比之下,“振穷”、“恤贫”之事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前者那么紧迫,但皆属传统国家治理中“养民”的重要范畴。由此观之,中国传统社会多把贫困问题视为伦理问题来处理,既然贫人的产生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具有密切关系,若政府能够针对这种伦理缺陷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补充,在理论上则可消除社会上的无助贫人现象。在此视角下,贫困问题也就从社会层面转化为伦理关系的问题了。
其二,经济上的“养民”措施。只要社会上存在贫困问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国家都有义务对贫困者进行救济,更要从源头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养民”,而“养民”的关键在“富民”。《管子》曾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a 孟子也认为仁政应该提倡“爱民”、“保民”:“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b 人民富裕是政治稳固、国家安定的基础,如果老百姓一旦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容易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由贫生困的群体,如孟子强调的“无恒产者”所表现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等特点,管子亦认为“民贫而难治”。历代统治者深谙此理,对于贫困者的救济就不能仅仅是防止饿死而已,更重要是通过系列富民政策使老百姓能够自谋生活:农事生产无失其时,故老者可衣帛食肉,黎民则不饥不寒。例如,以轻徭薄赋、赋予田产等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或以仓储制度如社仓、义仓等措施以备不时之需;或建立相关社会保障体系以救助穷困者,等等。除了官方的富民、济民措施,家族救济在传统救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家族在经济上以“共财”的方式彼此共济。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慈善主要是以伦理关照为特质,这种伦理关照不仅体现在对“仁爱”的追求上,还体现在对宗法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及对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上。对行善者而言,“社会救济本身有重要的道德上、精神上的意义,政府的救济政策也有安定社会及稳定政权的作用”。c 通过伦理救助,一方面实现个体道德的自我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对穷人的帮助及其道德改良来维持一个良序社会。
二、“善与人同”的救济理念
传统社会的慈善救助首先指向那些具有伦理“缺陷”的人群,救济所涉及的范围主要以家族内成员为主,但在实际运作中,也惠及宗族之外的乡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家族荣誉,强调对血缘共同体的道义责任。散财同宗、救恤邻里“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贫穷族人乡邻发展生产的效果,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穷族人乡邻的生活困难,保障了贫穷族人乡邻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地方秩序的稳定”。d 历史上除“范氏义庄”式的典型家族救济之外,也出现不少宗族、乡里之间的互助性救助形式,如《吕氏乡约》所提及的患难如水灾、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情形,乡邻有责任互相救助抚恤,共同救援。从家族、宗族式的救济形式到乡里、团体之间的互助模式来看,说明传统救济范围不只局限在“亲亲”之济上,而是展现一条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救济理路,强调一种与人为善、善与人同的救济理念,这正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志,e孟子则以“养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f 体现了儒家“仁爱”的“悱恻之感”“安人之志”以及“万物同体”之意。a 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孔夫子从“不安”了解仁,程明道用“不麻木”说仁,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心灵。b 理由在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能感通万物、滋润万物。明朝理学家杨东明将天地生物之心视为“仁心”,并认为人应存此“仁心”,去关怀帮助他人,因为“夫人虽万有不齐,实天地一气所生。古人父母乾坤,胞与民物,疲癃残疾鳏寡孤独皆为兄弟颠连而无告,是合天下人本同一体也。”c 因此,杨东明所倡导的“同善会”、“广仁会”皆是以“生生之理”为核心理念,以“生”名“仁”,以“仁”扬“善”。他将扶贫济困、广为善事视为“仁”意的充分表达,并且认为人之积善,就如同农之力耕,多种则多获,少种则少获,不种则不获,故推“善”于天下,全“仁”于万物,既是天地之“仁”的自然显现,也是人应当所为之事,并以此不断益培“生生”之理。
(一)生生之德作为“同善”的前提,强调“万物同体”
《周易·系辞》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此“四德”所体现的是天地化生养育万物、天地大化流行的自然运作。正是这一“生”之大德,使得人与其对象世界和他人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联结,并为仁爱、仁德的实施提供不竭的动力,其中预设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以说,“《易》文化所包蕴的生生之道,塑造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规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路向,同时也成为影响和制衡整个民族精神发展和心灵世界构建的重要力量。”d正是这种上下通达、内外兼修的“生生”之理构成了传统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学,“生生”所蕴含的正德、厚生、利用、惟和等精神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独到理解,构成了传统伦理生活的重要价值指引。孟子曾通过“以羊易牛”的例子来说明“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其中的关键并不是“易”的问题,也不是因牛羊“无罪”而得以幸免,而是因为“见牛未见羊”之故。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e 之所以会产生“不忍”之心,是因为生命之“共通”性,人与禽兽虽“异类”却“同生”,故“见”之“觳觫”等痛苦之状则起“恻隐”之心,此乃“仁”之端。对于儒家来说,要“‘使人成为人’,必须使‘天赋之仁’得到充分发挥,即将‘仁’的属性或要求充分实现”。f“仁端”以“仁术”扩而充之,以推恩四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二)推己及人作为“同善”的方法,强调“主体能为”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之心在行动上则表现为“推己及人”。天地之性,以人为贵,而人与人之间以同类同根而相亲。因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掌中之事,关键在于个体“做”与“不做”的差别。针对这一点,孟子曾指出,类似“挟泰山以超北海”属于“不能”之事,而“为长者折枝”却属于“可为”的范畴。至于如何“可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善推”。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a 朱熹指出“仁”作为“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b 这与孟子所提出的“善与人同”的理念并无二致。孟子认为,君子的最高德行在于与他人共同行善,强调了在社会生活中与人为善的重要性,“善与人同”的关键就在于舍己从人、乐取于人并不断扩充、推广,以此达到尽己之善、尽天下之善。可以说,“推己及人”为“与人为善”这一道德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方面强调“尽己”、“舍己”,另一方面则强调“推己”,因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c 这里所谓“推恩”可及“四海”,意味着将个人的仁德和恩惠不断推广,通过自己的仁爱善行来帮助和影响他人,其逻辑起点为“亲亲”伦理,在此基础上,将仁爱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乃至万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自然的和合共生。
(三)博施济众作为“同善”的愿景,强调“道济天下”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d 博施济众的意思就是广施恩惠,拯救民众于水火。孔子在高度肯定“博施济众”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难点,认为尧舜都可能做不到。朱熹在注解中提到两点理由,既“施之不博”和“济之不众”。因此,孔子认为应该掌握“博施济众”的方法,既以“近处”为切入口,一方面“以己所欲譬之他人”,另一方面“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孟子也同样认为,君王作为民之父母,应该体恤其民,改变“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情形,以“仁政”的方式实现“民养生丧死无憾”、“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e 的社会愿景。但这一愿景的实现不但需要直己守“道”,而且还需要以“权”宜之,以“道”济之。《孟子·离娄下》曾提到: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f 孟子认为小恩小惠是不知为政的表现,故指出子产只知“惠”而“不知为政”,因为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此乃私恩小利,真正的治世当以大德施之,而不以小惠予之,所以孟子认为子产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修桥而不是一个个地助人渡河,私恩小惠显然难以达到天下同善,而应该以“道”济天下,以“教”化万民,从而真正实现“善与人同”的理想愿景。
三、“施善劝善”的教化之道
劝人为善作为传统慈善救济的重要目标,在儒家慈善观中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曾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a 子贡与子路同为善行,一个从别国赎回鲁人却不领取本国所规定的奖赏,本应是值得提倡的无私之举却被孔子认为是“有失”之行;一个救了溺水之人而接受了厚报,孔子却非常赞同。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个体德性,而在于社会教化。子贡本较为富有,他不受领赏情有可原,但这种个体高尚行为对于当时社会现状(富者寡而贫者多)而言,则可能带来不良后果,个人无私的举动无形增加了行善的成本,效仿的结果也许就只是“不复赎人”了。所以,圣人举事不单单是“修己”行为,还要承担起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之责。
(一)“富而教之”的治理策略
孔子指出安置百姓首先应使其“富之”,然后“教之”;孟子强调“制民之产”的重要性,并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b 为何“士”可以做到无恒产却有恒心?朱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士”知义理,但普通人非但做不到,反而胡作非为。荀子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c 因此既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拥有“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d同时还要“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来教导老百姓。e 可见,“富而教之”是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一贯理念。纵观中国慈善史,尤其是从明末到清末,虽然善堂组织发生了各种变化,如育婴堂、惜字会、清节堂以及施棺善会等慈善组织的多样化发展,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慈善团体“一直没有将救济问题变为经济问题”,其“重点仍在‘行善’,即以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换言之,慈善组织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上,而没有转化到经济层面”。f 尽管这种“教化”大多只是局限在忠孝节义等领域,但因“慈”而“善”,因“仁”称“义”,一个人的善行不仅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还具有推动社会向善的力量。一方面以“己善”推“同善”,以“公”天下之善;另一方面则以“君子之德风”偃“小人之德草”,以德化民,而民相率从善,各安其分。
(二)“安伦尽分”的教化目的
如前文所述,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客观条件所致,或为主观懒惰所致。根据情形的不同,所采取的救济原则显然有所区别。孔子曾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g 好勇且不安贫者,一旦不仁且疾恶太甚,则容易滋生事端,显然不利于社会安定。由于自身的贫困,相当部分的贫困者由一种客观的贫困境遇沦为主观的精神贫困,以至于产生嫌恶劳动、邪僻乖戾的消极情绪。原因在于,如果人们既失去了家庭纽带的天然保护,又丧失了国家实体的普遍保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他们也不再抱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便可维持生计这样类似的信念,而是自甘堕落,于是贫困者由现实的贫困进而转化为心理的贫困,并恶化为“好逸恶劳”的伦理人格,甚至沦为“暴民”。针对这一问题,在慈善救济层面一方面要向贫困者提供物质援助,但同时也要提供伦理关怀及精神安顿。尽管物质援助是较为常见的基本救济方式,但容易限于循环救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救济原则上,一方面要从贫困者的现实处境出发去施以救济,在物质救济的基础上加以伦理教化以及精神安顿;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在个体层面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在社会国家层面则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a 即朱熹所谓“各得其分、上下相安”b 之意。“均”在这里并不是“平均”的意思,而是指贫富与伦理身份的相契合,如此便可不患而安,各守其分,并“使万物莫不遂其性”。c 从中国传统慈善救济的特点看,“慈善活动似乎是次要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升道德来维持秩序”。d 传统民间自发的社会慈善机构往往由乡绅阶层所组织,这些乡绅通过其特定的社会地位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与财富,他们通过组织参与慈善活动,一方面为家庭与国家这两个普遍伦理实体之间架起了桥梁,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己的特殊地位得以重新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可,从而促进个人理想以及社会伦理价值的实现。如此,富者依“礼”行善,而贫困者也因救助规定上的道德优先性而遵守日常伦俗,这样传统救济就完成了道德教化功能,传统“善会的最终目的,乃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相当快速之时,以道德的诉求来维持既存的社会规范。而所谓道德的诉求,是围绕在财富和贫穷的概念之上,从而重申传统的‘安分守己’原则。”
(三)“劝善化俗”的道德理想
伦理救济与道德教诲是儒家慈善救济理念的两个关键,前者主要根据受助者的伦理处境及其相应需要来进行施善,后者则主要根据受助者的道德状况来决定是否予以施助,而且救济只是方式,最终的目的则是落实在劝善,以此维系社会的稳定。一般情况下,施善者根据自身的伦理感来区分救济对象并对其加以选择、排序,并以伦理的标准实施救济,试图以此缓和贵贱矛盾,达到移风易俗之伦理教化的政治及社会效应。例如,明清时期由地方精英所领导的慈善组织所坚守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将贫困者进行区分,即区分为法律上的贱民和道德上的贱人,在救济原则和实践操作上皆有所分别。夫马进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贫民救济事业是“以劝善为目的的,所以有必要区分救济对象,甄别善恶。”f 而且,“寓教化于救济的模式,即根据同善会组织者的伦理感选择救济对象并加以分类,不仅在同善会,而且在小于同善会的同心圆——义庄中也可以见到。”g 对于那些孝子节妇、贫老困苦的人,显然是优先救济的对象,而那些无视伦常的人,比如不孝不悌,赌博、酗酒无赖、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则不被视为应该救济的对象。如高攀龙认为“同善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劝人为善”,因此善会救济的对象也不限于家族内成员,其目的虽是“济贫”为主,却兼具教化之责,两者相得益彰。以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等创立的嘉善同善会都留下了章程规则,分别称为《同善会规例》和《同善会会式》,其中均有一则规定:“受助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该会是否予以救助的一个重要前提,‘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a 不过,按照梁其姿的观点,这一类慈善团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解决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混淆和伦理身份认同等问题。一方面,善会通过“济贫”的手段以维护“贫穷”的道德中立性,并在救济实践当中对受助者加以道德考量,对于一些道德败坏者不予救助而优先考虑那些忠孝节义之人以劝人向善;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拥有财富的施助者而言,散财行善、广积福田才是对待财富的最好方式。这两个方面在重塑传统社会秩序、维护道德价值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启示
儒家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生、仁爱、同善等为基础,以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为特征,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而且对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文明互鉴有着重要意义。朱友渔曾指出:“从中国人携手扶贫济困、乐于互助、自愿合作改善民生的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向心力。”b 这一“向心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并在实践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c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既要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滋养当前道德建设,也要不断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其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以及复杂而深刻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也需要通过不断对话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积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和精神价值,在继承和弘扬中赋予其时代新义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化解文明冲突的合理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一)从熟人到陌生人:儒家慈善救济思想的当代调试
儒家传统慈善救济思想根源于血缘亲情伦理,发生于熟悉的乡土社会之中,在这个以熟人为主的共同体内,人们以“推己及人”的方式——以“生生”为内核,“推”而扩之,构成“仁”之实践进路:亲亲、仁民、进而爱物——进行修己安人、守望相助,最终达到“善与人同”的理想目标。不过,这一传统慈善救济观念却遭遇来自现代公益理念的质疑和挑战。有学者提出,以儒家“仁爱”思想为基点的传统救济形式与现代公益理念相悖,其秉持的“亲亲之爱”的理念并不适合现代陌生人的社会。a 在这种背景下,慈善行为就不应仅仅只是基于同情或亲情的自然反应,而应转变为一种公共责任。因此,需要将慈善的焦点从对亲人的关爱扩展到对陌生人的关爱,从同情心的驱动转变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并将传统的仁爱观念更新为现代的权利与责任意识。简而言之,慈善应当从基于血缘和亲近关系的“亲亲之爱”转变为对所有人的“路人之爱”,从情感驱动的“恻隐之心”转变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责任”,并从传统的仁爱观念转变为现代的权利与责任意识。诚然,现代公益事业并不局限于熟人领域,家庭、宗族式救助也不是现代慈善的主要路径,但儒家所强调的恻隐、仁爱是否与现代公益理念相冲突、一时的救急救贫是否能够成为现代公益文明的重要内容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
从慈善救济的理念或行为来看,儒家所倡导的慈善事业实际上并不仅局限于“亲亲之爱”,尽管出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只能惠及亲人、家族或者乡里等范围,但实际上也常常帮助除族人、乡里等以外的群体,不少慈善团体也涉及公共事务如社会服务、教育等范畴,并对中国人的慈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还是一个以“熟人”伦理关系为主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由无数私人关系所搭建的网络中,维系其中的社会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b 其“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c 这种以熟人圈建构起来人伦差序结构,以个体私德为基点,以亲亲伦理为依据,并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我及他的伦理互助体系。一方面,这一互助体系如果要得以维持,需要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尤其是需要某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身份地位、道德声望并愿意行善的核心成员来组织和推动。此外,由于血亲关联的原因,对救助对象进行价值排序是有必要的,除道德考量之外,一般优先考虑家(宗)族内部成员并逐渐向外扩展。不过,这种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对族外人或者异乡人的伦理关怀,以至于“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d 这一特点正是被诸多现代批评者所着重诟病的重点,理由在于现代公益更为强调对他人(包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福祉及其公益的关心,强调“在这个领域中的行为(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公共目标及其使命”。e这一公共目标的范围并不限于血亲成员,其方法和手段亦不只是扶弱救贫,公益事业对社会对社会存在长期的正面外部效应,长远地看,公益事业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f 现代公益事业作为人与人或社会之间新的联结方式,试图通过“善”的力量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社会生存环境以及推动社会改革,并最终增进所有人的幸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熟人模式下的互助理念在现代社会中依旧有其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借鉴价值。在互联网构成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今天,各类新型媒介的传播让人们彼此相联,并形成一个人人互联的网络社会,其中熟人和陌生人交互存在。在以轻熟人社交圈模式为重要特征的互联网求助或众筹行为中,一方面,微信朋友圈等熟人交际网络增加了信任的因素,尤其在媒介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增多且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熟人圈”的捐助意向,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大致确保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规避了捐赠风险;另一方面,传统以个体、家族或某一区域小团体为辐射的救济精神,在当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人民正拿出对宗族、故乡、行会的无私奉献精神,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当下,中国人在社会小团体里孕育的互助合作精神正在更大范围的国民慈善事业中发扬光大。”a因此,应当善用这种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救济模式,因为可以通过私人的力量逐渐影响周围的人并逐步向外扩散,从而产生相应的涟漪效应,形成联动、持续、有效的社群公益。
(二)从私恩到同善:助力共同富裕的文化底蕴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b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底线,公平和正义、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是原则,而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则是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了系列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强调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c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公益慈善事业在三次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儒家慈善救济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所蕴含的守望相助、扶贫济困、仁爱同善、道德教化等理念和实践包含着对共同富裕这一普遍价值的积极探索,继承与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慈善文化,能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建设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管子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难治,因此提倡“积贮”,让百姓生活富足;孟子则认为仁政必从“经界”开始,既给百姓治地分田,以保障其生产生活,但仅有这点还不够,还要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因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d 在传统社会生产力相对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农事生产是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庠序之教则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措施,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这一理念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针对社会贫困问题,仅是凭借物质救济单纯地解决社会贫困现象是不够的,如果可以借着施善“尝试从道德层面重新塑造‘贫’与‘富’、‘良’与‘贱’的差别”,e 以此重整社会秩序,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f 或许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从而实现一个贫富均、上下安的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
具体到实践层面,儒家所提倡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物质援助如平籴、施粥、施谷、施棉袄等情形,也包括诸如助工修学、助婚、敬老、收养弃婴等伦理救助层面。明末兴起的“同善会”、“广仁会”等民间慈善团体强调共同行善,将“慈善概念化为一种完成一个包含穷人和富人的有道德的社区的手段”,a 施者自乐,受者相安。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慈善活动吸纳受助者一起行善,这才是“同善”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因此,施善者在物质救济的同时倾向于将视线集中在精神启迪和道德教化上,通过现场道德宣讲、发放各类与劝善相关的书册、歌曲、图片等进行道德教化,告知人们因何贫富以及应如何行动,主张富人应当克己向善,穷人则应积极向上等观点。如此一来,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因道德行为而缩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通过慈善事业获得广泛认可,以此吸纳更多人共同行善;随着“同善”理念的不断推广,行善已不仅仅局限在贫困救济和道德改良上,而是通过行善构建起一种地域式的团结,并“支撑起了一个秩序良好、稳定的社会的观念”。b 可见,儒家所倡导的救济理念不但注重物质救济与精神救济的统一,也强调贫富之间的公平正义以及伦理关照,同时主张可以通过主体道德改良、人人参与慈善、地域联动机制等措施来改善社会贫困问题,这些理念对于当前公益慈善事业、社会基层治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伦理“救济”:文明互鉴中的中国智慧
儒家慈善文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资源,其所蕴含的思维传统、价值观念对于构建全球慈善伦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前文所述,慈善事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极具世俗色彩,主要表现为基于家族互助、宗族族缘的慈善行为,展现了一种人我共生、家国一体的基本理念,为“中华民族形成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奠定了基础,滋养了‘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助人为乐、风雨同舟’的道德情怀”。c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慈善本质上或者首先是个体与社会的伦理“救济”,具有与西方宗教救赎不同的文化性质与文明意义。西方宗教慈善观点具体到行动上,人们首先要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坚信获取财富不过是伦理上的责任或天职;其次是要求自己在尘世活动中力行“善举”,要“爱上帝”、“爱邻人”,积极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同时强调“人的德性 、人的生活品质、人的能动性,并相信改变个人的品性、道德就能改变个人的贫困状况”,d 所有这些都是对宗教信仰的最好实践。较言之,儒家并不关注“彼岸”世界,也没有宗教式的“救赎”概念,而更多的是关注此岸生活,关注人自身的德性修养,并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为此岸生活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
韦伯曾指出儒教“不过是一种伦理”,e 是一种“俗人道德”,f 其主张的“生活导引全然是此世的,它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或‘人的堕落’之类的被拯救的渴望。儒教徒的‘救赎’是从无教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读书、学做人,追求道德的完善圆满”。g 通过个体的德性修养,修身齐家、成仁成圣才是儒者在世的“救赎”之道。在韦伯看来,儒家这种道德“救赎”存在一定局限,一是缺乏救赎宗教所具有的超越性先知系统去指引人们的生活;二是个人伦理纽带将导致社会伦理的冷漠性质。他指出,救赎宗教的伦理“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a 尽管韦伯看到儒家入世性格、伦理和教养、对秩序的理性建构等方面,但他主要是将儒家伦理与救赎宗教的“精神”特质进行比较并得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优秀”品质。面对这样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特别指出要对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错误论点予以澄清,其中提到儒家的天理世界、精神修养、入世苦行等精神品质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儒家慈善救济思想尽管没有宗教救赎之义,却有安顿生命之效,其对生命的正视、弱者的关怀皆是过去儒者所倡导的力行之事,这种伦理型的文化结构既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责任编辑:高静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慈善的伦理风险研究”(21BZX113)。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