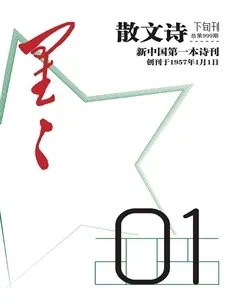灯下走笔(组章)
宁 静
我打破了宁静。
我在应该宁静的时候无法宁静不能宁静。
我邀请宁静来做客却鬼使神差轰散了宁静。
我以为我可以支配宁静拿捏宁静控制宁静。
我亲手创造了宁静又亲手毁灭了宁静。
我以为与宁静达成和解它就能重新回到我身边。
动了妄念,我就不可能宁静。
不安在心巢里进进出出,我就得不到那种自律、慎独的宁静。孤独,寂寞,沉默,三股拧成一股,结实的宁静。
咖啡一样提神的宁静。砒霜一样中毒的宁静。
一分钟过完一生,死亡一样的宁静。
我听凭宁静被噪音强拆,却捍卫不了宁静。
我放纵喧嚣活埋了宁静,却拯救不了宁静。
我守着一件叫宁静的瓷器,却失手打碎了它。我以为只要使用思想强有力的黏合剂,假以圆熟的技艺,它就能完好如初。
当它被重塑成型,我就知道,那种完美的宁静已有了裂痕,已从极品沦为次品。
六 月
榴花喷火,也喷大自然生死契阔的箴言。
当痉挛的风推动一堆高烧不退的石头,我正在陋室反复练习语言的必杀技。
那场高烧我已经感染过了,在痛与非痛之间,已获得强大的免疫力。
因此,我有足够的忍耐在案头枯坐,在虚空中勾勒火花一现的心,一首诗若隐若现的轮廓。
如果六月是一部言辞激烈的躁动之书,我就是动中求静的那粒词语,正以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为命运泄火,败毒,疗疮。
声 音
隔壁在拉琴。一种半生不熟,痛苦的声音,穿墙而来。
这声音,捅破词与词之间的寂静,撞击我。
这声音,隔着几十米的训诫和夜色,操纵我。
这声音,把它的愤怒、抗拒、憋屈、厌倦,乃至仇恨,强加于我。
这声音,像锯,来来回回切割,我敏感脆弱的神经。
这声音住在隔壁,不是友好睦邻,而是为了让我不得安宁,在精神层面彻底击垮我,摧毁我。
尘 埃
低头静心,守方寸之间拂去又慢慢缔结的时光之尘。
它们在橱柜,在案头,在坚硬的书脊上抱紧泛黄的记忆和内心的波澜。
如果我知道,自己就是一粒易碎的尘埃,终难逃过生活之手清除的命运,我就不会对生命抱有那么多期待。
如果我知道,一个人漫长的一生,终将化作一粒侘寂的尘埃,我就不该产生那么多非分之想。
如果我知道,累累不绝的时间,都浓缩在一粒无声的尘埃里,我就不该放大痛苦,把自己过成累赘。
如果我知道,那些耀眼的东西,终会沦为一粒暗淡的尘埃,我就会放下虚拟的幸福,活得更真实一点。
如果我知道……如果我知道……
在秒针急切的提醒中,在时针缓慢的告诫中,其实我早已明白,我就是那粒没有分量没有意义的尘埃。
一阵最小的风,就能推翻我的过往,爱恨和悲欢。
微不足道,不足挂齿,小小不言,这些廉价的词就是给我准备的。
梦里兑不了两分光明,梦外照不见三分辽阔。
在这间陋室,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丧失了什么,用语言祭奠了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寄身人间一隅,在文字里短暂停留,只为你匆匆一瞥,就能读懂我浮尘一样又凉又薄的一生。
伤 疤
我左手上有一道伤疤,那是小时候割草不小心留下的。那是刀锋对我的一次深刻的教育。那是受伤的童年,在生命的底板上烙下的痕迹。
当时没有哭,因为周围没有安慰的声音。也没有包扎,因为所有的伤口最终都会愈合。
但这道伤疤,为流出的血保留了证据。
它陪我一起长大。为了更好的未来,它陪我一起背叛生养我的村庄。
我带着这道伤疤投奔另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带着这道伤疤争取我想要的东西。我带着这道伤疤恋爱,结婚,生育,完成一个女人的蜕变。我带着这道伤疤在最深的夜里挖掘内心的独白。
这道伤疤,是与我血肉相连的另一个我。它见证我的成败,悲喜,是非,歌哭。它亲历了我全部的痛苦,希望和失望。
这么多年,我一直活在这道伤疤里。
这么多年,我一直攥着这道伤疤表达自己,它泄露了我的宁静,我的懦弱,我的悔恨。
这么多年,我以为它早已愈合,其实它一直张着彷徨的眼睛,注视这个世界。
我要用一生来修复这道伤口。
我要它成为不可分割的那部分,陪我一起变老,一起死去。
和 解
我把我弄丢了,当我翻阅一部叫“时光”的书,才发现这个已铸成大错的事实。
我弄丢了我的热血,胆魄,野心,感受爱和苦的能力。
甚至弄丢了投奔未来的地址和开启远方的钥匙。
我站在茫茫的世上惶惑不安。
我把我弄丢了。
我还弄丢了还未抓紧就荡然无存的那点激情。
我过早地暴露底牌,致使我丧失了与命运谈判的资本和斡旋的勇气。
我已沦为光阴的囚徒。我把我交给了虚无。
除了疾病,我一无所有。除了疼痛,我两手空空。
我不能原谅我,我要与那个把我弄丢的我对抗到底。
我要到处张贴诗文寻找我,我要让流浪在外的我听到我的召唤。
我要找回属于我的愤怒,欢喜和悲伤,找回摇摇欲坠中扶正我的骨头,找回悬崖勒马的那根缰绳。
我要失联多年的我,在百感交集的语境中叩响门扉。
我要开门的刹那,两个冰释前嫌的人,眼含热泪,无语凝噎。
白玉兰
绽放的白玉兰,让草木的颜色尽失。
她们越极致,周围的仇恨越深。周围的仇恨越深,她越肆无忌惮地开。
即使置身事外,隔着意象的栅栏和一大堆词语,都能感到一座平静的花园,暗藏危机。
白玉兰的美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一种罪过。一种违背。一种忤逆。
那些无辜的白玉兰。污垢和瑕疵永远都望尘莫及的白玉兰。
她们像伤口一样把自己打开,像伤口一样被周围的仇恨催熟,像伤口一样从身体里掏出绝望和芬芳。
灯下走笔
灯下走笔。夜晚只剩下大面积空白。
纸上一马平川,走起来却异常艰辛。那些看不见的篱栅,荆棘,木桩,陷阱,设置关卡和障碍,阻止现实向梦的深处推进。
一支笔画地为牢,被枯竭的想象力死死摁在原地。
就这样,时间在纸上白白地流失了。你甚至听到那滴滴答答的声音,一点一点卷走了纸的激情,热望,期盼。
一张纸落空了。一颗心宣告破灭。夜晚只剩下疆域辽阔的失望,剩下这间坟墓一样的孤岛,剩下身体里一口枯井。
只有灰烬,能结束一张纸的焦虑,沮丧和痛苦。
于是你擦亮打火机,把它交给了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