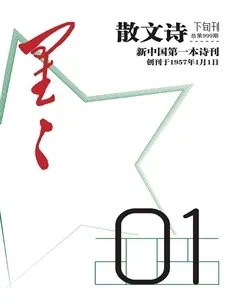南充非遗(组章)
“熊猫队长”背后的他
嘉陵江畔,我抚摸着两只从韩国归来的“熊猫队长”。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他藏在碳纤维制成的木偶体内,操纵着“熊猫”在冰面游弋,同机器人穿梭时空隧道,向世界发出中国邀请。
300多年前仪陇县石佛乡,幼时的他向杨姓移民学习耍“木脑壳”。如今,年迈的另一个他,正在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传袭木偶的制作和表演。流传至今的川北大木偶,偶如真人大小灵活,是全球唯一保留下来的大木偶。
从稚嫩的小手,到布满青筋的老手,制作杖头木偶的那些他,找好木料,刀斧锯戳勾锉并用,木屑翻飞间,不同人物头部五官通过雕刻描绘化妆后成形。再按身形尺寸制作身腔、关节,然后组装、安置机关、粘贴黏合,再佩戴服饰,形态各异真人般的木偶,从他手中诞生。
他与他举着木偶,走上舞台。凭着熟稔于心的操控技巧与力气,紧扣剧情运用机关,双手操纵手签和脚筒,变脸吐火,吹灯点蜡,书法盖印,翎子功扇子功水袖功运用自如,恍若真人。
无数的他举着木偶,如举着有血肉情感和灵魂的自己。穿行尘世,巡演世界,浑身沾满光环。他与木偶,这孪生胞胎,背影辉映出神秘的光。
灯火里的喜乐人生
一盏灯敲锣,一盏灯打鼓。滚灯的人在板凳间上下飞舞,嘴里含着灯,眼里映着灯。灯戏吸引着童年的我,跟随人群翻山越岭,潮水般举着灯,花团般簇拥在夜晚。
川北灯戏,唱着傩戏从嘉靖年间来,跳着巴渝舞从乾隆年间的志书来:“上元,放花灯、演灯戏”;敲锣打鼓从嘉陵公子《看灯戏》中来:“一堂歌舞一堂星,灯有戏文戏有灯;庭前庭后灯弦调,满座捧腹妙趣生。”
主灯耀眼。画着花鸟人兽、写着字符的彩灯,既是道具也是角色。堂屋与街沿的地灯戏,正戏苦戏有滋有味。民歌、佛歌、嫁歌、清音、端公调,像月亮的药片,祛除劳动带来的疲累。广场与院坝的天灯戏,笑戏闹戏巴适过瘾。杂技木偶皮影猴戏跳端公,滑稽喜剧闹剧,像生活的盐粒,添加日子该有的滋味。扮灯的演员,看灯的观众与灯共舞。
扮丑与找乐,都是生活的主角。小花脸、三花脸的男丑,彩旦、摇旦的女丑,赞孝德善行,讽假丑恶态。“七里灯”“豆叶黄”嬉笑怒骂,都是“喜乐神”,“对花”“猜灯”讥讽戏谑,都唱“欢喜调”。
无灯不成戏,从桐油灯煤油灯到电灯,每一盏灯都照亮过我的脸。无戏不成群,从泥土坝子混凝土到新农村,每一场灯戏里,都有快乐的身影。
“电影之父”让灯影更红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死后,方士李少翁用纸剪李夫人侧影像,以灯投影于蚊帐,李夫人呼之欲出,汉武帝聊慰相思。据说这是皮影的雏形,皮影戏也被誉为“电影之父”。
三百年前,从上元夜的土院坝,到今年中秋夜古城的皮影剧场,从一九八八年王文坤作为唯一站上维也纳金色大厅舞台的中国皮影艺人,到今夜他的孙子王访正在进行的皮影表演,“阆中王皮影”自康熙初年第一代传人王家禄到今,已历经八代逾三百年。
皮影薄如纸,岁月多沧桑。一张嫩牛皮,王氏传人融蜀锦蜀绣之美,沿剪纸篆刻之技,鉴阆中汉代帛画画像石砖和寺院壁画之法,绷皮发汗擂皮裁料保水,刮磨削刻钻剪,反复雕刻着色。人物栩栩如生,景致惟妙惟肖。
小小一张皮,短短一幕剧。鼓锣钹胡琴唢呐伴奏,川剧民歌帮腔,光线投影在幕布后,手提控制四肢和关节的三根木棍,透明牛皮的场景、道具和人物出场。边提影边说唱,巧舌如簧,一人饰演多角色,十指灵巧,双手摆弄百万兵。
阆中王皮影博物馆,我曾和几位法国诗人一起玩过皮影迪斯科。舞台上手提牛皮人形,幕布上拽得不亦乐乎。入夜,霓虹灯投射在天幕,我们跌跌撞撞,像皮影在走路。
迎面而来的王访,用祖传技艺,纠正着我们的步态。还用独创的灯光,把我们照在夜幕里,像通体透明的皮影一样红。
刀尖与火焰上的脸
时间一压,生活如纸。伸进日常的手像剪刀,给日子剪出天窗。新春贴窗花,新婚贴双喜。仪陇剪纸自汉唐始,至今还贴在人们的生活里。
何作霖先生说北方剪纸粗犷豪放,磨平了生活的粗粝,南方剪纸纤巧秀丽,秀出了生活的妙趣。然后手把手,教我剪出一个草书的虎字,贴在我书房中间,至今虎虎生风。
天下剪纸一把刀,仪陇剪纸用火烧。
从传统的阴阳互套、黑白粘贴、暗刺相排、折叠曲沓中,何先生另辟蹊径,独创火烧烫绘法。利用张张彩纸,集剪刻钻刺撕烧烫多种技法,手撕火烫,成型的作品如书法似绘画,像木刻像版画。五谷六畜飞禽走兽,自然景观梦中物事,脸上的刻纹,腮上的红晕,惟妙惟肖,呼之欲出。
剪开生活的疙瘩,剪出历史更迭。在纸上翻来覆去折叠,剪去滞涩冷漠,剪出安慰期许。
仪陇城乡人们手手相传的生活习俗,化为窗花,贴上年关或日子的开篇,化为鸳鸯,贴在花轿檐口或新娘眉梢。在剪纸博物馆,何氏传人说:剪纸,其实就是把生活剪出趣味,贴在自己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