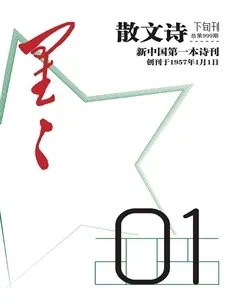古城脉韵(组章)
阆中古城
临水而居,难免被水灌醉。
缰绕合护,形胜之地。始终处于微醺状态。
城门,一直开着。门内有绣花鞋,有良家女子?
江边舟楫,被时光镂空,又被川北道署的鼓声惊醒。
双栅子街的青石板上,远去的脚印堆积如山:车夫、商贩、货郎、匠人拖着艰辛的赤脚印;贡院里,考生们散发书香的布鞋印;王皮影掌心里形形色色的小脚印;红四方面军疾驰而过的草鞋印……
一路走来,沿途的风水和春天,次第绽放。静听流水回声。江光可抱城廓,山势却难锁烟霞。春风不倦。汉桓侯祠里的香火,愈燃愈旺。翼德的脸,由黑变白,由白变红。被落下闳星命名的天空,夜晚也是白昼。
长公在上,上善若水。一位老人捧出春节,敬献苍生。与水结缘,阆苑自成仙境。
等我两千三百年,佳人痴心不改;我只轻轻一瞥,便白发苍苍。
相如故城
在花蕊里,返老还童。用朝拜的目光,轻叩门扉。此刻,我泪眼蒙眬。
堂前檐下,风在随意翻动春天。高兴处,还笑出了声。玉环书院依旧正襟危坐,仿佛仍在默诵上林、长门或美人中的名言金句。背阴处几株花草灌木,口中念念有词。一阕汉赋的密码,谁能轻易破译?
江水和文君可以作证。那枚奇异的卵石,曾被两千多年前那个乳名犬子的顽童,打过水漂,做过定情物。剔透的玉指,在料峭春风中抚琴而叹。衙鼓的诉说、衙役的吆喝,早被浪花淘尽。嘶哑的蝉鸣,却经久不息,从长卿祠旁那棵千年古树传来。每一声,恰似赋圣深情的吟哦。
阳光,在古城墙上涂抹温暖与寂静。有必要对每一块饱经风霜的汉砖,保持仰望的姿势。
它们字字珠玑。用人间最美的汉字,细数前朝月光,或者,用虔诚厮守子虚、乌有的宫殿;临摹辞宗绝世的孤独,和光芒。
淳祐故城
一杯浊酒,独饮寂寥。
缄默七百多年的石头城,终于开口说话。
恰似雄辩的思想家,一字一句,入石三分。
山岚,不甘寂寞。总想从古城墙坚硬的表情里,抠出马蹄声,抠出光阴里的每一粒疼痛,抠出早已风干的血迹。
江水,也不想再隐瞒真相。总想从曲流环抱的牛肚坝,古渡的前津后津、上下码头,复原长鸣的汽笛,复原金戈铁马的厮杀、刀枪不入的传说,和三千抗蒙将士舍身跳江的呐喊。
“山峙两岩南北峭,地盘一水古今流。”唐朝的姚昂不知道,一江春水流到今,依然如泣如诉。
黎明,迟早被春天占领。
刀枪剑戟迸发的火星,也早已风化成无言的结局。
在这里,我不想惊扰青居烟霞,更不愿让青居山人①《游灵迹废寺》的完整与精彩,搁浅岁月的沙滩。
我只望一场远去的风暴,能留下时光的胎记。
最好,让石头开花,或者在阳光下沸腾,升华为历史辉煌的断章。
① 青居山人,明朝中期名臣、四川顺庆府人陈以勤的别号。
周子古镇
一部发黄的线装书。扉页上写着:嘉陵江上最后的码头古镇。
一枚光阴的戒指,佩戴在吴道子三百里锦绣画布上。
古码头的背影、古民居的灯火,在画布上点亮;古商铺的吆喝、古客栈的钟声,从画布上传来。一群复活的精灵,从历史襁褓里跳出来——
下河街的脚印川流不息,反复丈量着深藏不露的时光;画江楼上,颜鲁公毫笔扯出的纤绳,在岁月的礁石上晃悠;火星四溅的铁匠铺里,许多生硬的词语,已熔化成水;爱莲池中,每一片荷叶上,摇曳着依稀可闻的蛙声……
万寿宫内,谁在一抹夕阳里修补残缺的歌谣?
临江阁里,那些似醉非醉的眼神,早已看惯帆影,阅尽苍生。
苦难与蹉跎,从老戏台前躲到幕后。我不知道,在你内心深处,还有多少柔软与温存,正在塑造龙角山的瑰丽与风骨。用星光繁衍渔火。用浪花冲刷苦闷。
一枚桑梓,早被一条江吟咏成隽永的绝响。
马鞍古镇
身着朴素,像朱德的草鞋。但穿斗式木结构肌理,足以使你身板硬朗,精神矍铄。
客家风情,本是骨子里的天性。但好长一段时间,你既没客家,也无风情,甚至连一套合身的石榴裙都没有。好在,盘缠花光,还有更多孳息。
走出夜色那天,你印堂发亮,面色也越来越红润。是琳琅山下那个娃子最初的啼哭和战马的嘶鸣,喊红;是红军街上饱蘸激情和鲜血的石刻,映红;是无数火凤凰浴火腾飞的丹心碧血,染红……
那些红,是井冈山上蔓延开来的满江红,华夏子孙血脉里汹涌的中国红。那么多红映入眼帘,不难想象你当年的盛况——
天空明朗。手搭凉棚,就能望见北斗。
就像那些入乡随俗却不懂风情的红五星,熟谙客家檐下炊烟缘何袅袅不绝,子弹和刺刀怎样势如破竹。他们簇拥着镰刀斧头,用枪杆子诠释一句著名的箴言。尽管,好多鲜血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但他们却以丰碑的方式,走进德乡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