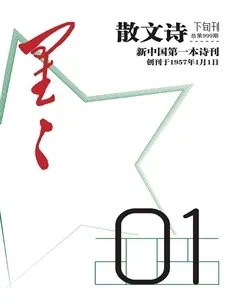南充:美食册(组章)
川北凉粉
铜旋子过处,胶状物满布一条条刮棱,辙痕浅浅,挟日影,晃进大街小巷。
而葱花、味水、姜水,如词藻加持,不断丰盈着被分解的凉粉的词条;舌尖颤动,你听见的纳食,仿佛浸染浪花之人,从码头,一味扎进城市心脏。
红油下,八角、桂皮、辣椒面、茴香……再一次生动起来,活泛各自的山川,各种的水域,层层叠砌,谢凉粉与薛凉粉在河坝农舍的爱情。
你忍不住,回望:人头攒动,浪花隐隐。
瞬间,麻辣嫩鲜,诸般乡愁,恍若云烟。麻布渗出的淀粉味,又会于一只只盛满的细碗蔓延。
川北凉粉,我将蘸水滴说出,你独属自己的南充造。
一辈辈人在风雨中深耕。起于农业,无限延伸于工业、服务业,商业的吨位在加重,而巨轮在融合的黄金水道迎风逐浪。直营,加盟,股份合作,是张翼的帆,可匠心,总是在传承中时时擦亮。
多么好,我拙于馈赠的精美辞章,就予以这半透明晶体。烟火碗盏里,豁达爽性,相亲相爱。
张飞牛肉
在阆中,张飞持续被放大。连同勇猛忠义,和怀念。
皮影的、剪纸的。包装袋上,任头像占据封面的大半个江山,而食品匿身,只能隔山问樵夫。樵夫改行,钝刀从店铺颤出清音。
但牛肉不钻牛角尖,它只释怀,只快意江湖。
闻香识物,我必须略过“百草霜”的印渍,略过黑,一个切面一个切面看到它的红,它内在的光亮。味蕾紧贴,于致密,于咸淡,于椒香麻辣中摩挲它的风味。
干、燥,软、硬,绝非简单的二分法,适中,一直是它安身立命的法宝。
在阆中,一块牛肉的香是可以转弯的。屋檐,而瓦片;三角梅,至银杏;八面楼阁,漩入镇水兽。若即若离,像怀念镀上的淡淡唇印。升降,飘逸,沉淀,系于一念之间。哦,陌路人,我们完全可以提着这香,彼此慰藉。
反过来,周遭风物也是香的知音。漫步街巷、庙观、水榭,有时我会跌进往事的深渊,青瓦之下,一张张面孔浮动,优雅从容,粲然洗练后的反光。就像细嚼慢咽,一块牛肉变得更加醇厚、绵延。
事物之间,隐隐的关联,像土壤,或另外的佐料,在背面蛰伏、潜泳,搅动着深喉。终究,我会从风景回到牛肉本身,它自带的嚼劲,与回响。
狮子糕的故乡和远方
我有两个故乡:西充,(杭州)西湖。
一个腆着受孕的胚胎,一个嘴衔恩情,像叨了千年的忠义,结草,落籍。
水稻盈盈,菜苗青葱,阳光从仁和、占山、常林这些丘陵的间隙找回我的青春,而月光恩典,一粒粒糯米始终如一地清白。
碓窝里放下坚硬,擀面棒下,柔情,抱团取暖。
必要的切割。必要的分离。犹如返回独立,还给局部的自由。在通向自我的道路上,接受沸腾的洗礼,和挤压,也成为必然。
必然的滑轮转动。必然的流水线轰鸣。
一枚狮子糕,有了自己的远方。
小磨油里漾出香,玫瑰、芝麻、葡萄干在芬芳中学会了侧身轻嗅,像一头狮子从金发绕过自己,眸子分泌柳丝、绿杨……微波里醒来的钱塘潮,涌向异域。
也像荒草接受挖掘机劝谕,蜗居在楼盘里转身,发射台,把自己拔向高远的天空。
黄生生,脆崩崩,我消融在一片片舌尖后面。
没有诺言。
故乡和远方,一同,繁星浩瀚。
肥肠记
叫我“旺子”就好。如此简单地开篇。
一甩挑,一大河,一些颠簸的船,明暗交织。
简单到抢眼。
一锅猪血旺,小菜,外加毛干饭。就会从纤夫、搬运工的喉结,或毛孔,窥出饥肠。
另一层意思是:挑夫,谢继光。
露在满福坝。
百年前,河滩广大,而空出来的寂静,如此潦草。
我的混沌,源于乏善可陈。
而豆腐、香料、猪心肺的说辞,让我身陷“杂烩”。
“斑驳里藏着迷人的心跳!”
如是所闻:谢邦喜从檐口下拔出吆喝,又在谢家礼的唇间,反复唱傩戏,绘皮影。
——像接力。也像派生。
紧跟着,那些心怀火焰的人呵,生生不息。
迁徙。繁衍。按下烽火,也从来不会按下烟火键。
几瓣蒜,数片姜,海带,兼萝卜。
头顶“南部肥肠”,我自有我的黑红青白。相较红烧火爆,我更偏爱不疾不徐,文火里,守着这荤素人间。
一锅鲜汤,四十年。在乐群路,谢瑞礼,支起第四代门匾,身后,一幅偌大的市井图。
——举着走马灯,就这样步入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