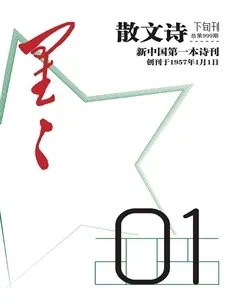甘南:行吟的长短句(组章)
草原小城
万波霞光向一个方向汇聚,顷刻间,火焰激活苍穹。
夕阳下,远望阿尼念卿,身影状如一条火龙席卷而来,将这草原腹地精致的城镇瞬间唤醒。
羚们迅疾地消失在山冈上,遗留下几缕神秘的飞尘,在一个诗人的纸笺上来回跑动。
借旷野夕照,将目光伸向烟雨蒙蒙的扎油沟和当周山,那片片绿荫深处,是否还留下红狐和狼群追逐的声响和贪婪的鼻息?
众生都在夕阳下的羚城鲜活生动地成长,连同他们清澈闪亮的眸子,都在这深秋的黄金大幕上涂抹着羚城最精彩的情节和光影。
羚城夜色
我的视线不经意间就停留在秋日羚城之夜。
多么孤寂而沉默的夜,一幅横空出世的水墨画打破了这秋歌浩荡的天空。
一群鹰隼在厚实的云层上卸下沉重的翅膀,以及隐藏在羽毛深处的计划。
已是深夜的羚城,在辽阔的深空遭遇一场蓄谋已久的云墨和闪电的洗礼。
仰望天际,我瞬间震撼于时空的精妙转合,东边荡漾的清明之水,与西边泼墨泛动的水墨画的神韵交织着红月亮的微光,顷刻间这巨大的画卷覆盖了小小沉静的羚之城,一场突如其来的浪潮自天界奔涌而来,迫近我的视线,令人刹那间失去喘息的机会。
我被这瞬间的无穷演变惊愕得不知所措,这个秋天最令人心跳的歌唱不是黄河的咆哮,不是白龙江的长啸,更不是那秋歌里沉甸甸碰撞的累累硕果,今夜这羚城上空的奇观在深秋的露霜里飒飒作响,颤动灵魂。
伫立山冈
聆听到野鸡、马鸡和云雀的鸣叫,声音是从泛着白光的树林里散发出的。
清晨在折合玛村游走,远处有云海飘弋在帐篷城和如梦如幻的海螺弯。
在录豆昂山坡上沿栈道攀爬向上,眼眸里闪动着层层霞光。
回望来路,那羚城已身披霞蔚,瞬间湮没在苍烟中。
山冈上有羚群在荒草中鸣叫或喘息,仰望高处的羚城西苑已是另一番璀璨的光景。
我的脚步贴近晨露,那挂满草丛和树叶的风声,是谁在等待朝霞顷刻间的安抚呢?
秋风萧瑟,将我素薄的长衫和硬朗的身躯吹奏成呜呜作响的号角。
远望一片塬上翻腾的云海,倏忽间被阳光划开豁口,大片火焰跳跃而出,迅疾地卷走大野整片阴霾。
晨练的人群在高处亮开喉咙,我收住步履,谛听那清脆而迷人的民谣,把韵律涟漪般伸向一座座耸立的楼群和宽敞发亮的街道。
在初春的塬上
在尘埃里哀怨和滚烫的文字,都埋没于草原苍凉的月光和时光的背影里。
一切都在三月被涂抹上暮春的洁白,在羚城南边的塬上,桃花还没有绽露芳容,而探春快饱满成季节的盛宴,只有群山黑影幢幢,哪里遇见的花朵,雪白的身子透着光影,在逐渐长成咆哮的河流身旁,我要把自己凝固成一棵伫望的树,或者隐没成几瓣透亮的雪,其实我只想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哪怕是稍纵即逝。
雪时光
我怀揣着一片执念,爬上故乡的屋檐。
雪时光迅疾到来,亲人远眺的眼神瞬间被白光洞穿。
严寒和落雪包裹的小城镇,在渐次丰腴的诗意里舒展身子,敞亮心扉。
踯躅前行在雪塬上,我就像重新投胎的新生命,惊奇地环顾周边。
我展开双臂,拥抱跌落眼眸的故乡,拼命呼吸和咀嚼着乡愁的味道,那久违的激情在雪白中瞬间燃烧。怀揣炽热把灵魂安放在偌大的白瓷上,那鲜活的词语一刻不停地抚摸大地跳动的心脏。
在黄河岸上
晨曦被鸟声撩开惺忪的眼,铺开一张黄河的画卷。
瓦砾和石经堆砌的痕迹,跨越时光,在一幅幅陈旧的灰光里,浮现上古年代草原沉重的背影和迁徙的脚印。
一片雨水里长高的白杨和红柳,吐露彼此呢喃的呓语。那镶嵌在时光里的岩画一直在坚韧地拔高自己。那岁月抹不掉的印痕翻过几个世纪大批游牧者的行进史,在今夜养育河曲马的草原上急切地倾诉。
眺望那片天边一隅的风景,小小藏寨孤寂的影子,在我深情地远望中泪眼蒙眬。而诗人们扬起牛角酒杯,把游牧的月光与格萨尔的弹唱催化成辽阔和壮美。
众神在柔美和阳刚中编织阿尼玛卿的神威,而鲜活的格桑将我的视线,无限延伸到爱情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