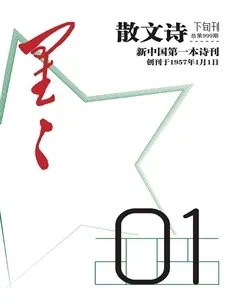洮州城(组章)
西大街
晨光下,高原小城逐渐醒来,环卫工和学生的身影牵出一天的斑斓。
穿城而过的西大街是一条河流,打开小城古老与现代融会的画卷。
江淮遗风的古建筑和高楼大厦错落有致,西门十字路口,摆满带着露珠的蔬菜,香气四溢;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和广场舞的音乐,此起彼伏,在生活的舞台上,演绎着小城的生机与活力。
无数的小巷溪水般,携着明亮的浪花,汇入河流。小巷的青石和水泥路,磨光岁月的棱角,千百年的沧桑与光芒静卧于白墙黛瓦和砖雕门柱的光影里。花格木窗上的柔情与斑驳,像一股温热的气息,涌入内心。
在西大街,或仰望或赶路或驻足的人,都有不易察觉的念想。他们,是你,也是我,浪花般涌现于各个角落,泛着无数微光,驱散生活的迷茫。
直到夕阳洒落,夜幕低垂,车灯、路灯、霓虹灯……替他们繁星般闪耀映入河流,照亮一座城。
静谧的夜色里,停止流动的街道上突然有风穿过,像谁蹑手蹑脚地替我们拽了拽生活的被子。
高原之春
我所住的城郊,窗外是一片片田地,像时间留下的补丁,刚好遮住目光的空洞和心灵的空白。更远处是矮矮的雪山,起伏于永无止息的风中,在城与郊的缝隙,野草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是一簇簇异乡的野草,在生活里游离。白天进城,夜晚归郊,循环往复。
当山上的积雪消融,城郊向阳处,阳光温热。探头的草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们,最先感知高原上的乍暖还寒,像一把生锈的钥匙,需要一滴油的润滑,打开被困于泥土的万物生灵和被封于冰块之下的清澈。
而春风,是一把行色匆匆的剪刀,无须时光的磨刀石,也能剪出满坡的桃花、杏花、樱花、梨花……剩下为数不多的冰块,在陡峭的河岸像一个个湿润的词语,滴落水面,率先组成一行行春归的身影。而清脆的波浪,在春风中鸟鸣般一遍遍擦拭着倒映在水中的天空。
转瞬之间,已是遍地青草,遍地花儿,遍地鸟鸣。
窗外的油菜金灿灿地盛开,而青稞和燕麦业已长大,等待出穗。我们像一个个用旧、遗弃的词,绕过发白的时光,在高原城郊,重新被春雨洗刷一新。
洮州卫城
高原如海,群山如浪,而洮州卫城是海浪上的一艘帆船。
六百年的风雨侵蚀,像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洮州大地上生生不息;六百年的荣辱沧桑,像一条汹涌的洮河,在西部大地熠熠生辉。
宏伟的城墙,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痕迹;高大的城门内外,呈现着古朴与繁华。
穿越迎薰门,巨大的褐色条形石块上,斑驳的纹路和痕迹,似乎流动着戍边将士的温热气息。行走于城墙之上,城内栉比鳞次的洮州民居,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江淮遗风,袅袅炊烟萦绕着白墙黛瓦和雕花的木门木窗。而城外的山坡上,烽火墩像守望者,在风中呵护着梯田和牛羊。城前是南门河不息的奔跑,城后是海眼碧波荡漾的幽静。
它们,构成时间的流逝之憾,空间的交错之感,生命的坚韧之力。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洮州卫城休整,并建立了甘南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开启了洮州人民的崭新史篇。
每一次穿越卫城,都是与历史的邂逅。依山蜿蜒的城墙,需要你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凝视,去攀登。而每一个眼神,满含坚毅,星火般点燃生活——
与山相依,与水相伴,与万物相融。
山 歌
山的近处,是山;山的远处和更远处,还是山。
那么多的山,像我至爱的父老乡亲,互相搀扶着,冷了,就彼此依在一起;累了,就彼此靠在一起。
他们,在洮州大地血脉相连,像一条条溪水汇入洮河,汇入黄河,哺育万物生灵。
每年六月,莲花山就是歌的海洋,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不分昼夜,男女老少,以山歌的方式抒怀,表达对时代、生活和人生的态度。
山的上面是山,山的下面还是山,再往下就是平川——
“上不起山峦就下不来平川,经不了苦难就分不清香甜。”
时代的春风,吹遍高原。坚定的目光中,一座座山说绿就绿了。
山坡牧羊,溪边饮马。清冽的溪水,荡尽心灵的灰尘,一片草原上的花儿说开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