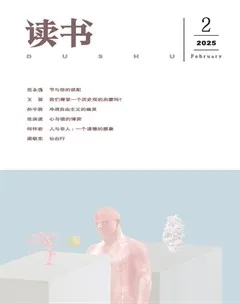什么是戏剧中的“幽灵出没”
马文·卡尔森教授的《幽灵出没的舞台—作为记忆机器的戏剧》(以下简称《幽灵出没的舞台》)一书主要讨论了戏剧如何被过去的幽灵萦绕,被过去的记忆影响的问题。具体而言,《幽灵出没的舞台》探讨了戏剧文本、表演、制作、剧场(空间)都是被过去的文本、身体、道具、剧场等的记忆影响的。卡尔森认为,戏剧文本以及具体的表演、制作、空间等总是以它们与以前的文本(文学和非文学)的关系为特征,并且从字面上和形象上都受到过去幽灵的萦绕。马文·卡尔森既将“幽灵出没”视为创作者对过去元素的再利用,又将其视为能影响观众观剧体验的记忆,因此本书的学术兴趣为探讨戏剧和记忆的关系。
《幽灵出没的舞台》不仅在文字上生动而又深刻,而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作者在探讨“幽灵出没”(haunging,ghosting)这个概念时使用了“recycle”这个词。“recycle”意为重新使用,即再一次利用,而不是抛弃。在此基础上,本书与之类似的词还有重新扮演/ 重新经历/ 重述等,这些词都具有重新(re)的意思。作者在《幽灵出没的舞台》(英文版)第九页的一段话,“重述讲过的故事,再现发生过的事件,再体验经历过的情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并且一直是戏剧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该书的核心论点。我们经常称戏剧是活态的、新的,看向未来的,但卡尔森认为并不是这样,戏剧往往关注过去,是一种生动的重述。
值得注意并且极为重要的是,作者不仅讨论了艺术家对于材料的重述,而且着重从观看戏剧的人,即观众的角度入手,探讨观众如何利用他们对于过去剧目、表演、制作、剧场等方面的记忆来欣赏戏剧。作者以《哈姆雷特》为例,说明了当观众观看其他的莎士比亚作品时,与这个剧目有关的记忆就会浮现出来。观众会记得他们在学校曾经讨论过这个,也会记得此前观看时的演员、制作、剧场的情况,因此观众的个人生活显然会影响戏剧的观看和体验。显然,这里的记忆既包括个体记忆,也包括更为宽泛的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文化记忆使得戏剧成为一种记忆机器。
《幽灵出没的舞台》是在探索戏剧形式、寻找戏剧意义的时代创作而成的。马文·卡尔森在创作该书时,显然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作为哲学问题,结构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理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这一名词,由法国文学理论家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等建构并阐发出来。哲学和文学上的“后结构主义”进入戏剧研究领域之后,使戏剧研究不再讨论剧本,而是讨论戏剧结构的问题。该书创作的时代,戏剧理论研究正处在文学理论向形式分析转型的末期。
这部著作非常关注戏剧结构,即戏剧是什么的问题。作者探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呈现系统(使用表演、制作、故事等),戏剧如何作为一个交流系统发挥作用?戏剧的形式是如何制造的?戏剧形式的制造是如何影响我们观看和体验戏剧的?卡尔森借鉴了文学和文化研究上互文和符号学的研究成果来展开自己的讨论。在《幽灵出没的舞台》之前,戏剧理论界并不关注戏剧的形式结构问题,当时的戏剧理论家的研究集中在创作和制造戏剧艺术方面,而《幽灵出没的舞台》一书让我们关注到戏剧的结构问题,并认识到戏剧的制造方式会影响我们对它的理解。
书名中使用的“幽灵出没”这一短语,显然受到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 一九九三)中提出的幽灵学理论的影响—过去的事情仍然与我们同在,也许肉眼看不见,但它们就像幽灵一样出没。由于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以这样的一段话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因此德里达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的留存问题时,用了“幽灵”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德里达所说的幽灵并不是有形的,却时时刻刻地存在着。
在文化理论的范畴内,这种观点非常受人关注。巧合的是,这一观点或许与东亚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因为在东亚与佛教有关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现实世界和死后的世界并没有完全分开,幽灵可以出没在人间。但在欧洲文化中,十五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得人们认为现实世界和死后的世界完全分开了。德里达说,死去的人即幽灵,从未消失过,它们只是在文化上受到了排斥。在德里达之后,当人们提到“幽灵出没”这一概念的时候,就是在谈论“仍旧在那里的东西”。
《幽灵出没的舞台》一书从以下这几个章节探讨了上述问题(一)幽灵出没的文本,(二)幽灵出没的身体,(三)幽灵出没的制作,(四)幽灵出没的剧场,(五)幽灵出没的丰富画面并共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戏剧重述。
卡尔森首先讨论了文本中的幽灵出没,这是因为文本常常就是在复述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即它是对另一个故事的重述。在讨论“幽灵出没的身体”时,作者谈到了演员的问题。比如,我们观看一位著名京剧演员的表演时,会记得其他演员扮演该角色时的样子。我们观看哈姆雷特或者其他著名角色时,会想起他被不同演员扮演的历史。我们可能不是在有意识地比较,尽管很多人会进行这种比较,并且会得出某个演员比这个演员演得更好的结论。除了谈到这种身体记忆之外,作者还谈到了更宽泛的身体记忆,即与身体有关的文化记忆。在“幽灵出没的制作”一章中,作者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制作团队制作了一个剧目,观众想要看到一个剧目的新版本,这在逻辑上意味着事实上一个剧目的制作是有历史的。它并不是全新的,而是有来路的。然后作者谈到了剧场,戏剧建筑也具有记忆。如果你去非常古老的剧场,如加里克(Garrick)表演过莎士比亚戏剧的剧院,这种建筑本身就具有记忆,这些记忆就像幽灵一样出没其间。
西方人用很多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种记忆,也就是剧场中幽灵的存在,其中最著名的是剧院魅影,即住在歌剧院的幽灵。关于剧场,西方人有很多迷信的说法。比如在西方的剧场中,有一种特殊的“幽灵灯”的习俗。技术人员在戏剧结束时,会将舞台上的一盏灯打开,这盏灯也叫幽灵灯。幽灵灯必须一直亮着,这可能是为了帮助幽灵看见表演,也可能是为了不让它们看见表演。此外,剧场中还流传着许多其他的说法。比如,演员不能在剧院里吹口哨,这一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演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时,剧院里不能说“麦克白”这三个字,人们用“苏格兰戏”指代那三个字。我们不喜欢剧院出现绿色,绿色的演员休息室不能出现在舞台上。在日本的能剧剧场中,他们也很迷信,因为能剧的剧本是讲述一个人如何变成幽灵的。所以,剧场里面的幽灵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幽灵出没的舞台》的最后一章即第五章中,卡尔森认为当下的后现代戏剧也展示了这种幽灵出没。伍斯特剧团就是后现代主义戏剧团体的案例,正如卡尔森所说的那样,这个剧团确实是重述性的,是幽灵出没的。
一般的戏剧学者会研究某个特定的戏剧时期或是某种戏剧文化,但《幽灵出没的舞台》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所涉的范围显然都更加开阔。它的视角是全球性的,作者借鉴了许多不同的戏剧文化和戏剧形式的例子—从能剧到法兰西喜剧,从彼得·布鲁克到伍斯特剧团。此外,书中不仅论述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戏剧形式和戏剧潮流,如古典时期的戏剧、文艺复兴戏剧、新古典主义戏剧、浪漫主义戏剧、现实主义戏剧等,还谈到了如今还在影响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戏剧,并涉及塔德乌什·康托尔(TadeuszKantor)、彼得· 布鲁克(Peter"Brook)、丹尼尔·梅斯基奇(DanielMesguich)、阿里亚娜·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等当今的重要导演及其剧目。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研究戏剧历史,而是将戏剧历史与当下戏剧现状结合在一起,总结出一种普适的戏剧现象,因此,作者的视野显得非常宏阔而又深刻。
在此基础上,《幽灵出没的舞台》提出了一种全球化的戏剧理论。卡尔森借鉴了英美戏剧、法国戏剧、德国戏剧、阿拉伯戏剧、印度戏剧、中国戏剧、日本戏剧中的实例与理论,对这些实例和理论做了大量的概括与融合,从而提出了他的观点,即所有的戏剧都是关于过去的记忆的。也就是说,如果观众观看一个著名的剧目,他们经常会想起这个剧目悠久的历史。仍以《哈姆雷特》为例,这个剧目从来不只是它自己,它总是带着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在出没。我们都知道《哈姆雷特》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 它发生在欧美的舞台,也发生在中国的舞台上,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幽灵在出没。卡尔森写作该书时,戏剧理论家都在试图提出一种普适化的戏剧理论,作者在这一点上正符合了当时戏剧研究的总体潮流。《幽灵出没的舞台》一书认为所有的戏剧都是有幽灵出没的,但是幽灵出没的方式很不一样,这是因为不同的戏剧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该书之所以如此著名,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探讨了戏剧如何利用记忆和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来进行互动。
我认为该书的研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会进入当下。作者认为戏剧不仅是现场的、当下的(短暂的),而且是“幽灵出没”的—我们通过借鉴过去的记忆和经验来理解当下。从关于《幽灵出没的舞台》的评论来看,由于作者的观点体现了一种批判,因此它引起了一场戏剧理论的讨论。当时有一位戏剧理论家佩吉·菲勒(PeggyPheeler),提出了戏剧(表演)总是体现当下的那一刻这一理论。佩吉最著名的论点是,戏剧总是在形成,它关乎当下,而并不关于历史。卡尔森创作《幽灵出没的舞台》,意在反对佩吉的观点,他认为戏剧是一种记忆机器,著名的戏剧、角色、制作、剧场都是重述性的—我们观看和感受它们的发展,而我们的体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比如,我们一生中观看一部著名的戏剧作品, 可能有五次、十次之多,所以当我们观看该剧的时候,会想到当下的制作,也会想到之前看过它的历史,会记得它的不同版本,也记得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因为观众观看它的时候可能是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光,也可能是非常糟糕的时刻,因此他们会记得快乐或者悲伤的感觉。由此可见,戏剧从来都不只是故事,也不总是身体、制作和剧场,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关于文本、身体、制作和剧场。这些符号系统相互作用,创造出许多不同的感觉和意义,这就是作者称戏剧为记忆机器的原因。
马文·卡尔森创作《幽灵出没的舞台》的时候,戏剧本身也在经历着变化,因此作者也受到后现代戏剧美学和互文理论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探索。总体而言,卡尔森采用了一种非常古典的传统风格创作了该书:在该书中,戏剧就是戏剧,故事就是故事,历史就是历史。另一方面,卡尔森也把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是对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互文理论的思考,带入了古典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作者实际上把他的思考从非常规范的、历史的角度转移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之中 (孔繁尘初译,朱夏君整理并校订)。
(《幽灵出没的舞台:作为记忆机器的戏剧》,[ 美] 马文·卡尔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