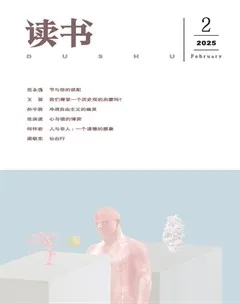“笨蛋,问题是经济!”?
一九九二年,比尔·克林顿以“笨蛋,问题是经济!”切中了大部分美国选民对高税率、收入不平等、财政赤字和失业的关切,成功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回归民主党阔别十二年的白宫。二〇一六年,经济议题的魔力似乎消失了。希拉里·克林顿强调奥巴马执政期间相对良好的经济表现、失业率的降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强调稳健且促进平等的经济政策,却未能成为打动选民的王牌。甚至,立场相对温和的希拉里·克林顿在中间选民中以4% 的差距输给特朗普。究竟是政治极化改变了选举政治的重心,还是中间选民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抑或是争取中间选民的背景发生了变化?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分析、理解中间选民的结构、观念和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
一
新世纪以来,以中间选民的偏好解释美国大选结果的最大困扰在于,中间选民支持的大量经济政策似乎与民主党人相契合,民主党却未能从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5% 的美国选民支持提升最低工资、扩大医保补助、减少收入不平等、对富裕人群加税。这些几乎都是民主党主张的经济政策,而在实际选举中,大量支持此类经济政策的白人却流入共和党阵营。对此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强调选民的经济认知受制于短期的经济表现,且中产阶级和高收入群体在选举的政治回应性中表现更加显著。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共和党利用文化保守主义政策“锚定”了大部分持有保守世界观的白人基督徒,以文化议题分裂经济投票。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经济解释”和“文化解释”。以拉里·巴特尔斯的经典著作《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Unequal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为代表的一批研究侧重于经济解释,而约翰·赛德斯、米夏尔·特斯勒、莱恩·瓦弗莱克与克里斯·陶萨诺维奇等人的新作《身份危机:二〇一六年的总统选举和美国的意义之战》(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和《苦涩的结局:二〇二〇年的总统选举和美国民主的挑战》(The Bi t ter End: The 2020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则侧重于文化解释。前者上承马丁·李普塞特和罗伯特·达尔等人的研究,分析在多元主义民主,尤其是有偏向的多元主义民主框架下中间选民的选择和代表性如何受到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后者则建立在对茶党运动和共和党、民主党间不对称极化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传统意义上的中间选民的种族焦虑情绪如何改变了两党的选举版图,使得特朗普能够进入白宫。这些研究跨越三十年,关注了里根革命后美国政坛的变迁,尤其是注意到选民结构的变化和两党对中间选民以不同方式展开竞争的特点。深入分析这两个分支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中间选民的结构与行为的密码,正隐藏在三十年来美国政治版图的变化中。
拉里·巴特尔斯长期关注民主与不平等,以解答为何既有的民主选举制度无法实现有效的再分配。《不平等的民主》是对二〇〇四年出版的经典研究《堪萨斯怎么了?》(What Happened in Kansas? )的回应。后者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以堪萨斯州为代表的中西部白人主导州的大部分选民支持民主党主张的经济政策,但在选举中大面积倒向具有亲商业、亲富人形象的共和党?《堪萨斯怎么了?》的答案是共和党通过将民主党塑造为精英党和文化自由主义政党,通过文化议题拉拢了持有社会保守主义倾向的白人。巴特尔斯怀疑这一解释过于简单,在著作中证明相比下层白人,是上层白人选民群体更重视文化议题。收入程度较低的白人更关注的,始终是经济议题。至于中产阶级白人,其行为方式则相比高收入白人,更接近低收入白人。巴特尔斯进一步以定量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九十年代以来,白人选民不断倾向共和党,主要是由上层及部分中产白人的转向所致,低收入白人依然是两党竞争的对象。
那么哪些因素使得共和党正在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呢?巴特尔斯全书既包括对两党治理绩效的检验,也包括对两党议程和选举议题、两党对选民回应性的检验,从三个角度指出了中间选民选举行为的特性:
其一是选民的短期经济关注。巴特尔斯以纵贯历史的分析表明,民主党在经济绩效上相比共和党有更好的表现。但是,选民更关注在选举日之前一年的经济表现。也就是说,选民在评估经济表现时要更加“短视”。由于共和党人更频繁地在选举前采取货币和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他们在中间选民的投票考量中拉平了经济绩效上的“劣势”。换而言之,虽然民主党执政有更好的经济表现,但共和党在中间选民的评估中也不会因此失分。唯有当共和党总统在执政末期有严重的经济政策错误,如一九九一年老布什总统为海湾战争而违背竞选承诺加税,才使得克林顿能够用“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名言顺利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
其二是选民对议题的关注度受其相关知识的影响限制。巴特尔斯证明,对大部分中间选民和民主党人来说,当其对降低富人税率的税收改革了解越多,对税收改革的支持度也越低。小布什总统的两次税收改革为富人降低的税收要远多于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降低的税收,然而,大部分中间选民,乃至部分倾向民主党的选民都缺乏对税改的全面知识,因此简单地基于“减税”这一观念支持共和党的税收政策。这一解释强调了“信息”的重要性:以中间选民为代表的、大部分可以被争取的、立场倾向并不固定的美国选民掌握的经济政策知识有限,因此能够用更简单的信息,如减税、降低通货膨胀、降低官僚主义等直观性强的议题争取选民的政党,更容易争取到中间选民的同情。显然,即便在巴特尔斯研究的十余年后,特朗普也证实了“简化议题”的重要性。加征关税保护就业、驱逐非法移民以减少工作竞争、减税、废除奥巴马医改等议题相比民主党复杂的经济政策要更加直观,也因此对中间选民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其三是选民的投票行为与经济表现的联系超过与经济政策的联系。巴特尔斯的研究发现,选民的投票行为与其经济政策主张之间的联系相对更弱。当然,这一机制可能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选民的议题偏好,亦即部分选民并没有将经济政策当作重点议题。不过,在将经济政策当作重点议题的人中,其投票行为也和两党的经济政策相似性关系不大,巴特尔斯认为两党对低收入者政策偏好缺乏回应性可能会成为一个原因—定量数据显示,民主党和共和党对高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回应性要远超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回应性。也就是说,无论低收入白人这一重要中间选民团体在经济政策上有何种偏好,被特殊利益集团和高收入群体“劫持”的两党都无法给出有效的回应。民主党侧重平等和再分配的经济政策反映的是持有左翼进步主义立场的高收入、高教育水平选民的主张,而非低收入白人群体的主张。
巴特尔斯描绘出这样一种场景: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下,大量中间选民基于经济表现而非经济再分配的政策摇摆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然而,茶党运动的爆发和奥巴马医改的波折又似乎显现出中间选民的复杂性。二〇一〇年奥巴马依靠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超级多数强行推动奥巴马医改立法后,反对强制征税的富裕白人选民成为茶党运动的基础。茶党运动在二〇一〇年中期选举冲击了民主党的两院多数,使民主党遭遇一九九四年来最大的失败。由于奥巴马医改向低收入选民提供了切实利益,将医保覆盖率从约84% 增长到约91%,茶党运动应该导致中低收入白人为代表的中间选民巩固在民主党阵营中,基于实际经济利益维持对民主党的支持,而温和的中高收入白人群体为代表的中间选民则继续向共和党转移,使得阶级分裂投票的图景更加明显,延续巴特尔斯所观察到的趋势。但是,二〇一六和二〇二〇年大选的图景却证明了,对中间选民动向的经济解释是不充分的。
二
赛德斯等人追踪了二〇一六和二〇二〇年两场大选, 在二〇一六年大选中观察到两个显著的现象:在一个略微倾向于希拉里·克林顿的大环境中,经济增长的表现并没有为民主党提供太多“加分”,而个人特质、初选和丑闻也并没有导致两党基本盘的崩溃。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得到了超过90% 的本党选民支持。另一方面,相比二〇一二年选举,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得票并没有遵循传统的选举定律:当一个候选人的得票率相比其同党前任增加或降低,其往往在所有选民组别中体现出同样的趋势。希拉里的得票相对二〇一二年的奥巴马降低了,但她并非在所有选民组别中同等减少了得票。相反,希拉里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男性中大幅失去选票,而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白人女性、少数族裔等群体中反而得到了选票。这是典型的选民重组:这些改变了支持对象的中间选民有着特定的结构和选举行为特征。二〇二〇年拜登与特朗普的竞选表现出了同样的结构:拜登虽然相比希拉里有更高的得票,但在低教育水平白人男性中继续大幅失血,而在高教育水平的白人,尤其是白人女性中扩大优势。
因此,分析特朗普时代后的美国选举,不能忽视中间选民的结构,将中间选民当作简单的“温和派”。如果中间选民只是在各个政策立场维度上都相对居于两党中心的选民,那么既不会出现巴特尔斯所捕捉到的,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白人选民立场变化的不同方向,也不会出现赛德斯等发现的,同一场选举中不同组别选民移动方向不一的现象。考虑到两党在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个议题上都持有各自的立场,我们可以认为存在两个乃至多个“议题维度”。一部分选民在特定议题维度上倾向于民主党人,在另一些特定议题维度上倾向于共和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共和两党在相应的议题维度上采取偏离中心立场的激进表述、提出激进政策,正是吸引而非疏远这些中间选民的手段。最简单的模型将议题分为经济、社会两个维度,但更多维度的模型同样符合上述分析。
赛德斯等发现,特朗普的胜利正是抓住了能够影响大量中间选民的种族焦虑这一议题。虽然特朗普以极端者的形象示人,赛德斯等通过对初选的研究发现,在税收、经济、堕胎权等传统的重要议题上,特朗普反而处于在共和党中更加温和的一派:无论是其政策立场,还是其在初选中得到的选民支持层,都属于这些议题上的温和派。特朗普明确且积极地表达出的“极端”立场,是族群关系的议题。特朗普敏锐地抓住了对白人优势地位的衰退和少数族群比例增加而感到焦虑的白人选民的情绪,在选举过程中放大了族群身份认同这一议题。
这一策略解释了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的胜利和二〇二〇年险败中的核心困惑:为何特朗普越是发表歧视性种族言论,其支持率越是稳固。赛德斯等回顾了二〇一二年曾经支持奥巴马的选民,发现该选民群体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选民联盟,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并非完全支持民主党的政策,而是为奥巴马的政策和选举吸引力所争取到的中间选民,其中包括了收入水平较低、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蓝领群体。当希拉里和特朗普同时将种族关系议题标定为选举的中心议程,对少数族裔受到“优待”的恐惧和族群身份焦虑情绪驱动这些低教育水平白人男性倒向特朗普。希拉里在这一中间选民流向的重组中有得有失:经济地位相对更好、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白人城郊选民转而流向了她。然而,低教育水平的蓝领白人在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中比例更高,希拉里吸引到的选民则多分布于不影响选举结果的深红和深蓝州。结果是选举人团从结构性有利于民主党转为结构性有利于共和党:在二〇一六年选举前,共和党被认为更有可能赢得普选票而输掉选举人团票。此后,民主党成为更加不利的一方。
对这种选民重组的发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竞争性解释认为,希拉里在经济议题上的温和立场,和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的民粹主义叙事,使得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选票流向发生变化。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在二〇一八年中期选举中,在经济上采取激进进步立场的民主党候选人仍然在城郊高教育水平的白人选民中取得进展。相比之下,赛德斯等的解释或许更加合理:中间选民的动向与在二〇一六和二〇二〇年选举中被“激发”的种族焦虑情绪息息相关。赛德斯等证明,高学历白人选民之所以倾向于民主党,是因为高学历白人更不可能具有种族焦虑情绪、持有种族主义观点。
在二〇二〇年大选中,类似的趋势仍然在延续,唯一的突发事件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损害了特朗普在一般中间选民中的支持率。然而,围绕种族焦虑产生的选票转移仍然显著。二〇一六年大选重塑了影响大量美国中间选民的议题,使得种族主义观念和种族焦虑成为决定性的力量。相比之下,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减弱,仅能解释部分锈带蓝领工人的立场变化,而且这一解释也是不完全的。作为低学历白人群体,锈带蓝领工人同样在二〇一六和二〇二〇年的选举中被激发了种族主义情绪,在投票行为中增加了种族观点的权重。
三
巴特尔斯和赛德斯等人的研究对中间选民的投票行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框架,这两种解释框架为我们勾勒出不同的中间选民群体形象。综合这些研究来看,中间选民在部分议题上倾向共和党,在另一些议题上又倾向民主党。可以通过在选举中“激发”不同的议题叙事而争取其支持的中间选民大概可以被分为三个群体:
其一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蓝领团体。这一群体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分布广泛,是民主党在所谓“锈带蓝墙三州”的选民联盟中的重要一环。该选民团体在社会议题上持有相对保守的立场,与民主党主流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存在分歧,但在经济议题上赞同政府规模的扩大,最低工资上涨,保护工会的立法和医疗、失业等方面福利的扩大。他们关注自身的工作受到外来竞争的潜在压力,对自由贸易持有怀疑立场,担忧非法移民损害其收入和岗位机会。随着种族议题和关税议题的激发,该群体日益倾向共和党。
其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郊富裕白人。这一群体长期以来是共和党的票仓。在美国的普遍城市规划中,市中心常常多种族混居,并主要囊括了中低收入群体,因此呈现出深蓝色。而城郊地区往往是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和富裕群体的居住地,偏向共和党。该团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普遍在社会议题上持有温和乃至偏向自由的立场,在经济议题上则反对增加税负、扩大政府开支和赤字财政。该团体因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对种族议题不敏感,并因社会议题上的自由倾向逐渐转向民主党。
其三是拉美裔身份认同程度较低的拉美裔选民。拉丁美洲裔并未像黑人一样受过长期、系统性的种族压迫,与美国主导的白人族群在文化上相近。由于来自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其结构也更为多元。该团体受到交叉压力的影响:一方面,其社会- 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在种族关系中处于结构性劣势一方,因此在经济和种族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另一方面,拉丁美洲裔选民的天主教信仰使他们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相对保守。在二〇一六年选举中,特朗普鲜明的种族主义倾向使得拉美裔选民大比例支持民主党。然而,随着特朗普的执政和保守主义议程的推动,拉美裔身份认同程度较低的拉美裔开始基于共同的社会政策立场转向共和党。
针对二〇二四年大选,似乎两种解释难言完美。现任总统拜登在整个任期内维持着良好的经济增长,而特朗普继续持有激进的种族立场,理应继续维系城郊白人向民主党的转向,并阻止低教育水平白人蓝领群体的流失。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几乎所有选民组别中失血:城郊富裕白人群体停止向民主党的转向,低教育水平白人蓝领继续倾向共和党。此外,拉美裔选民和年轻选民也大幅转向共和党。
答案可能存在于更普遍的选举政治规律中。或许一部分中间选民团体对特定的种族和经济议题更加敏感,但几乎所有的选民都会对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民生议题做出普遍反应。选举的基本规律仍然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二〇二四年大选中,现任总统的低支持率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显然仍然会对同党的竞选者不利。在政治极化的叙事中,人们容易忽视这种基本规律。(如果所有的中间选民团体都向同样的方向移动,就不仅要关注特定中间选民团体与特定政策的联系,还应从支持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宏观选举环境角度做出解释。两种解释并行不悖,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中间选民团体固然在决定选举成败中至关重要,但如果只关注中间选民团体,也有一叶障目之虞。)
当然,排除这些更普遍的宏观因素,中间选民对二〇二四年美国大选仍意义非凡。赛德斯等的研究证明了通过激发特定的议题争取中间摇摆选民是可行的策略。二〇二四年的特朗普在这一点上做得比其民主党对手更加高明。特朗普避免了堕胎权等不利于共和党的社会议题成为选举的主轴,借助地方的堕胎权公投将其地方化,而侧重于通货膨胀、关税和驱逐非法移民等议题。巴特尔斯的研究从另一角度提示了中间选民的流向为何与拜登政府的经济绩效相悖:人们更关注短期经济绩效,并更关注通货膨胀而非失业率。更多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选民倾向于将收入水平的增长视为个人能力的反馈,而将通货膨胀视为政府执政的疏失。因此,因收入较低而对通货膨胀更敏感的青年选民和拉美裔选民,也更可能因此转向反对执政党。
美国选举并非不可捉摸的游戏,政治极化并非能够解释一切的铁律。以中间选民为代表的美国选民团体的结构、偏好和行为特征,仍然可以很好地解释选举的成败,为我们揭示两党各自的策略如何与选民偏好和行为产生互动。在一九九二年,问题是经济。在二〇一六年,问题是种族。在二〇二四年,问题或许又还原为经济。把握住困扰中间选民的问题,或许就掌握了解读美国选举的“钥匙”。
(The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Democracy , John Sides,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