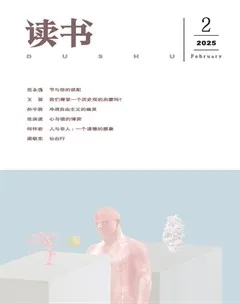冷战自由主义的幽灵
自二〇一六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着来自各种政治势力与思潮的围剿。左翼的进步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关于阶级、性别、种族的结构性不平等与系统性压迫,他们通过激进批判与身份政治对自由主义提出挑战。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右翼,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体观念,削弱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共同善的追求,瓦解了社会共同体的纽带;民粹主义则指责自由主义民主制被建制派精英所俘获,背叛了底层民众和国家利益,自称代表“人民”的民粹主义政党与领袖在不少西方国家上台执政。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恐怕没有谁能够否认,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
关于自由主义危机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本已司空见惯。但是,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的新著《与自己为敌的自由主义:冷战知识分子与我们时代的塑造》甫一出版,就激起轩然大波,毁誉参半。莫因是耶鲁大学的法学与历史学教授,他擅长通过谱系学方法揭示思想史上的断裂与转折,并以此介入现实的社会政治论辩。在此前的一系列思想史研究中,他发现普世人权的话语并非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而是“二战”前后由于大西洋两岸基督教政治势力的推广才得以兴起的晚近现象,这一话语在战后被基督教政治势力用于支持其保守主义政治议程,到七十年代又被用于美国的缓和对外政策,并影响了当今世界关于国际正义的观念与实践。这些研究为他赢得了声名,也奠定了他在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上的激进左翼立场。
《与自己为敌的自由主义》是一本关于冷战自由主义(Cold Warl iberal i sm)的思想史研究专著,也是一篇介入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意识形态争论的论战檄文。该书延续了莫因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旨趣,但在关于现实问题的立场上显得非常暧昧:这位激进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声称要为自由主义的病症提供诊断和药方。莫因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既是在批评信仰天主教的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学者帕特里克·德尼恩(Pat r ick Deneen),也构成对当下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应(2、173 页)。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德尼恩出版《自由主义为何失败》。德尼恩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作为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成功地削弱了家庭、社区与宗教机构,把人从特定的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赋予现代个体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自主;但是,自由主义民主制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结合也造成了今天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上的新贵族、经济上的不平等、教育上的优绩主义,以及新科技对人之为人的威胁,使现代个体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自主。德尼恩主张重建强调关怀、责任和牺牲的小型共同体,通过自下而上的地方性实践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
德尼恩的观点旋即遭到自由主义者们的激烈批评。同时,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关于自由主义危机的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根据莫因的判断,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如福山和马克·里拉)只是在自说自话,根本无法解决自由主义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是技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护教学:宣扬自由主义的美德并轻描淡写它的缺陷,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它;谴责(左翼或者右翼的)替代方案即便不会导致暴政,至少也是仓促和考虑不周的;以及,省去了解释自由主义最初是怎样变得如此不受欢迎的麻烦。特朗普当选总统是一场未被预料的突袭,而这些著述是从这一痛苦经历中写出来的,因此,关于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自由主义必须变成什么才能超越这场危机,他们更多是充满震惊和困惑,而无法指导行动或者提供阐释。”(175 页)在莫因看来,自由主义者们“寡人无疾”般的申辩,恰恰说明自由主义病得不轻;但是,他(至少从字面上看)认为自由主义仍然有救。德尼恩说,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忠于自己;莫因却说,自由主义的疾患是由于它与自己为敌,其病根在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冷战自由主义。
全书的第一句话表明了莫因的基本判断:“对自由主义来说,冷战自由主义是一场灭顶之灾。”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在二十世纪中叶决定性地改变了自由主义的面貌。在冷战初期,为“二战”做出重要贡献的苏联具有强大的道德正当性和意识形态力量。回顾法西斯主义的灾难、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西方阵营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感到恐惧,他们将自由确立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把在充满残酷与威胁的世界之中保存自由看作首要的政治目标。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但颇不寻常的是,莫因批评冷战自由主义是对苏联威胁的“过度反应”(6 页),并导致了一系列恶果:六十年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内部曾出现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批评(“冷战自由主义”这个短语正是这一时期的批评者所发明的),但并未伤其根本;七十年代后期,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与缓和政策的终结,冷战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并催生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冷战的结束与“历史的终结”似乎标志着这场自由保卫战的胜利,但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再次使西方世界感受到外部威胁的存在,也再度激活了冷战自由主义;对冷战自由主义者来说,二〇一六年特朗普的当选则意味着敌人出现在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内部,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于失去自由的恐惧。沿着莫因的逻辑,甚至可以说,一个冷战自由主义的幽灵在西方徘徊,这个幽灵使自由主义在赢得冷战的胜利之后仍然不断发现新的敌人(如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激进左翼、俄罗斯,乃至中国),它把恐惧而非希望塑造为自由主义的主导激情,剥夺了自由主义的理论自信。“冷战自由主义失败了……现在是重估冷战自由主义—而不是再次为它赋予活力—的时机。”
莫因把冷战自由主义称作对自由主义的“背叛”。他区分了三种自由主义: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冷战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前者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理想,追求个体完善和社会进步,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解放性的(emancipatory)政治理论,这种自由主义在应对种种挑战的过程中接受了或者促成了普选权、国家干预经济、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莫因认为冷战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次严重断裂,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抛弃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解放潮流,放弃了个人完善和社会进步的诉求,清除了在历史时间中实现解放、进步与自由的信念,他们怀疑人类的理性能力,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和对自由的威胁,把对民主、平等、解放或更高生活的追求看作极权主义与暴政的端始。尽管冷战初期的西方国家推行经济复苏计划、再分配政策与福利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却以冷战自由主义为突出标志,西方阵营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出现了“龃龉”。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一九七一年姗姗来迟,不过是开启了另一场龃龉;就在政治哲学与社会正义成为显学之际,世界迎来了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莫因认为,尽管冷战自由主义思想家大都支持—至少并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但是他们没有为福利国家提供充足的理论辩护,他们对国家权力的警惕反倒便利了自由至上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后来对福利国家的批评。
那么,冷战自由主义是如何“背叛”以前的自由主义的呢?莫因的论述中最为精彩之处,莫过于他对自由主义正典的塑造过程的分析。《与自己为敌的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来自二〇二二年初莫因在牛津大学讲授的六次卡莱尔讲座,这一系列讲座的主题正是“冷战与自由主义正典”。莫因选取了朱迪斯·施克莱、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汉娜·阿伦特、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六位冷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并选用施克莱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题记:“众所周知,每个时代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重写历史,政治观念史也不例外。不过,这些视角变化的具体性质有待考察。因为,对它们的研究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过去,还可以导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处境的更好的理解。”莫因发现,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大都也是思想史家,他们创制了一套“负典”(ant icanon)—也就是那些“为了定义和稳定传统而被谴责的过去的书籍、人物或运动”—并将其逐出自由主义的正典,同时寻找一些现代的思想资源来替代被放弃了的解放诉求。通过前三章对施克莱、伯林与波普尔的分析,莫因批评冷战自由主义把“从让- 雅克·卢梭开始,经由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达到高潮”的现代解放传统列入自由主义的负典。
莫因的思想史分析富有层次与褶皱,他没有把笔下的人物塑造为整齐划一的冷战自由主义信徒,而是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思想转变和对话关系。此处仅举他对施克莱与伯林的分析作为例证。施克莱著名的“恐惧的自由主义”无疑具有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气质,但她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乌托邦之后》却是“人们迄今为止写就的最伟大的对冷战自由主义的剖析与批评”。施克莱在《乌托邦之后》中惋惜地指出,启蒙运动中那种对人的自由行为能力的追求、对个人与社会的自我创造的向往,在“二战”之后已经消失殆尽。根据她的分析,这一转变缘起自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主义的保守化和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理性的批评,并完成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尽管施克莱后来转向了冷战自由主义,并转而捍卫一种以保障安全、避免残酷和减少伤害为要旨的启蒙,莫因却从她早期的工作中发现了批评与超越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以及他对积极自由的警惕,当然是冷战自由主义的重要命题,但是莫因强调,伯林在对浪漫主义的看法上是“他的冷战自由主义同侪的异议者”:施克莱批评浪漫主义的遁世倾向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否弃,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从浪漫主义中发现了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伯林却看到了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的结合。伯林认为浪漫主义运动挑战了真理与价值的客观性,这符合他对多元主义的倡导。伯林十分推崇的几位十九世纪思想家—贡斯当、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都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重视人的个性、创造力与自我完善。不过,莫因认为,伯林式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伯林对消极自由的捍卫最终无法安顿个体完善的理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在密尔那里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在伯林那里却最终退化为一种竞争关系。
不过,莫因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显然有些特殊的考虑,这在全书后半部分的三个章节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莫因选取的六人全都是犹太人(莫因自己也是犹太人),但他力图斩断他们的犹太血统与冷战自由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他以希梅尔法布对阿克顿勋爵的推崇为例,说明冷战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犹太现象”,反而“更具有典型的基督教性质”。在苏联声称代表科学与进步的方向、冷战自由主义者对世俗进步观念敬而远之的时刻,希梅尔法布从阿克顿勋爵对良心自由的强调中找到了一种足以与之相抗衡的、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自由主义。莫因试图通过阿伦特的例子表明,具有犹太血统的冷战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以外的自由诉求时采取了双重标准:他们偏安一隅地把西方看作保存了自由的孤岛,反对“二战”后风起云涌的、内嵌着民族主义与暴力革命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唯一的例外是,他们主张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犹太人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莫因写道:“冷战自由主义者们拥有一种地缘道德。基于一套关于世界上各民族的未曾明言却等级森严的假设,他们为大西洋两岸的‘西方’提供了冷战自由至上主义(Cold War libertarianism),在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上提供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暴力),在其他地方则展示出一种关于自由(无论是两种自由中的哪种)之命运的反讽的怀疑主义。”莫因对特里林的讨论,则关乎冷战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人性假定。特里林将弗洛伊德列入冷战自由主义的正典,重塑了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使冷战自由主义因承认人类攻击性之必然,而强调自我约束之必要,在思想气质上从乐观变得“现实”,由天真走向“成熟”。
莫因对后三位研究对象的选取颇有新意,但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伯林、波普尔、后期的施克莱,以及书中穿插提到的塔尔蒙,可以说是经典的冷战自由主义思想家;不过另外三位主角与冷战自由主义的关系就非常暧昧了。希梅尔法布和她的丈夫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莫因专章讨论希梅尔法布,不仅意在强调冷战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倾向,也是在提示冷战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性亲缘关系和时常的联盟”。问题在于,莫因既没有为他把希梅尔法布放入自由主义传统的做法提供辩护,也没有详细分析冷战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莫因对阿伦特的处理也很成问题。阿伦特是一位共和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但是,由于阿伦特的犹太血统、现实关切和她对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莫因仍然将阿伦特称作冷战自由主义的“同行者”,并认为阿伦特的政治理论“近乎一种‘奇怪的’冷战自由主义”。最后,莫因在这本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专章研讨特里林这位文学批评家,一些传统上重要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如雷蒙·阿隆和小阿瑟·施莱辛格,却被有意忽略,这种做法也颇可商榷。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莫因对冷战自由主义和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的理想类型建构,最终导向一种简化的“隧道历史”。尽管他在分析每个具体的冷战知识分子时颇尽精微,但是这些分析并不能很好地支撑全书的主论点。莫因从每个人物身上选取一个特点,然后用拼图的方式拼凑出一幅冷战自由主义的整体思想图景,这种做法有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对人物的取舍会极大地影响对思想图景的塑造;第二,每一个人物的特点(比如伯林对浪漫主义的赞扬和特里林对弗洛伊德的尊崇)可能只是这一人物的特殊情况,而无法构成冷战自由主义的一般特征。而且通读全书,冷战自由主义的详细定义付之阙如。莫因的思想史分析精细绵密,他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总体概括却失于粗疏,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莫因为当代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上。在他看来,当代自由主义虽然中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毒,但还可以从冷战以前的自由主义那里找到解药。不过,莫因低估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的内部多样性,也夸大了自由主义在冷战前后的断裂。诚如伯林与莫因所说,从十九世纪早期到中叶,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重视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何种制度条件这个问题上,贡斯当、托克维尔和密尔有相当不同的看法:贡斯当重视代议制政体和公民的政治参与,而不是民主普选和国家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干预;托克维尔虽然是一位民主思想家,但他总体上也反对国家干预;密尔支持通过经济与社会政策来保障个体享有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却主张通过比例代表制与复合投票权来对民主进行限制(参考 Arthur Ghins,“ Liberalism Reinvents Itself,”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 ,for thcoming)。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newl i b e r a l i sm)深受德国、英国观念论与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通过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实现个体完善和社会进步。莫因对此表示高度肯定,甚至还称“自由主义的最佳形式”就源自德国观念论。但是,莫因并没有在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与“新型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和比较。
关于莫因对冷战前后自由主义之间断裂的夸大,可以从他对民主的讨论中窥得一斑。莫因声称“更早一些的自由主义者们最终接受了民主化(虽然是谨慎地并且经常是不情愿地接受的),但是冷战自由主义者们恐惧大众政治—包括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莫因的修辞掩盖了民主化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区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确逐渐接受了民主化,或者说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实现了自我保存;但是,大众民主是二十世纪的新现象。考虑到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与托克维尔和密尔对多数暴政的担忧,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会接受二十世纪的大众民主;即便是在世纪之交提倡“新型自由主义”的霍布森与霍布豪斯,恐怕也很难对大众民主持赞成态度。对大众民主的忧虑和排斥,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特点,就这一点而言,冷战前后的自由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断裂。莫因关于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颇具误导性。
《与自己为敌的自由主义》成功地引发了争议与批评。从思想史上看,莫因暗示现代解放的“负典”应当重新列入自由主义的正典。就现实问题而言,莫因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解放,以及“普遍的自由与平等”。事实上,莫因所代表的激进左翼诉求和进步主义思潮正在美国社会和大学校园获得流行。中间派自由主义自然无法接受莫因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推广激进左翼立场的做法,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Holmes)在《伦敦书评》撰文强调莫因属于“左翼非自由主义”,保罗·凯利(Paul Kelly)则在英文《社会》杂志上坚称莫因的目的是“埋葬”自由主义。诚如莫因所言,当代自由主义难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未来设想,只是被动地面对各方力量的挑战。但是,自由主义至少保存了二十世纪的许多历史记忆,能够提醒今人避免重演过去的悲剧。相比之下,来自右翼的挑战或许更难应对。即便莫因是真诚地建议人们恢复一种更具解放性的、进步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也与温和版本的自由主义一样,仍然需要认真回应德尼恩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中提出的批评:良好的社会秩序能否稳定而持久地建立在个体自由与自主的基础之上?
(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Samuel Moy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