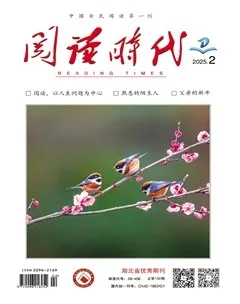“忆念”引来的忆念
一位诗界大家慨叹道:“只有能抵达良知本真的人,才能抵达诗的远方。”我以为,这是诗人该有的崇高追求与境界。往事重忆,旧诗新读,别有一番滋味。著名作家、诗人刘益善的首部诗集《我忆念的山村》名世已久,我羡仰亦久矣。今日重读这些似乎已经相离很远的文字,那心灵映照下的昂然诗意世界,依然让人感到揪心的悸动!“良知与悲悯是诗人的笔与墨”,这是怎样的一幅凄美而鲜亮的山村水墨画啊!作者是以诗的庄重仪式,完成着他对那个时代庄严的文学使命。
借来陈漱渝先生的话:“我的确不懂诗学,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诗歌发表个人见解;我的确不会写诗,但这并不妨碍我在青春岁月曾经痴迷于诗歌。”我与先生一见如故,相识于44年前——1981年5月为期一周的《长江文艺》诗歌创作学习班上。他长我三岁,却已在《长江文艺》做了多年的诗歌编辑。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诗刊》转载并获1981—1982年度《诗刊》优秀作品奖,后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先生亦是由此走上诗坛。我们是同时代人,同是农民的儿子,他笔下的那个山村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生活我十分熟稔,诗里的人物与故事我似乎都经历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着读着,我想到的或眼前浮现的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生养我的那个村子里熟识的父老乡亲们,以及那了然于心的山山水水,一切是那么生动、自然、亲和……挥之不去!

时代与诗人、与诗是不可分割的。一部诗集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罩上那个时代的尘影。细心的读者会感知到,诗人确也从某个角度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农村社会某些方面的状况及特点。我以为这正是《我忆念的山村》的价值所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读过这诗,认识并记住了一位值得尊重的“乡愁诗人”,亦重识并感怀着那段渐行渐远的岁月。这无疑是诗人为那个意气如虹的年代以及广大农村父老乡亲吟出的最强劲的律动。
朱自清说:“诗该怎么写我不知道,但我们这农村的光景是值得诗笔记录的。”农村天地广阔,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古今中外,但凡伟大的作家,没有不从农村大地汲取乳汁的。1977年,刘益善作为省委工作队成员,一头扎进鄂西北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下茅坪村工作生活了一整年。山野乡村滋养了他,村庄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涌向他的笔尖,唤起了他无限深情,只要被诗人的灵感捕捉到,便被赋予灵动、灵气、灵性、灵魂,被匠心独运、热忱赤诚地雕琢成字字珠玑、睿智夺目的诗行。那黄金般生活体验的珍贵印记与温热绵长的点滴忆念,无疑是他创作此诗的深厚基础。
语言作为诗的第一要素,明显与诗人的品格气质有关,与诗人的思想情操有关。语言是发自诗人内心的东西。《我忆念的山村》之所以历久弥新备受赞誉,至今仍有众多读者念念不忘、百读不厌,与它不尚浮华,不善矫饰,亦无居高临下,睥睨众生架势的诗风大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集子里,有诗人留下的生活日常的脚印、思想清澈的侧影和真诚的心灵剖白,亦能感受到他为人洵如、温文尔雅的性格折光。
刘益善先生的文字清新婉约、情致缠绵,却不脱一个“真”字。这些意象、意境,只有通过诗人自己认真地观察、思考后才能产生。这娓娓动听、直达心底的诗句,朴实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寄寓着在现实中无尽的胸臆。诗人的“寻求着真”,不仅反映生活的真,也表达其感情的真。在诗里面,反映生活的真实必须通过作者感情的真实来体现。有真情,才能说真话、现真境、写真象。寻着这样的真,通过这样的真,自然而然就会顿生美感。王安忆曾说过,与虚假对立的不只是真实,还有诗。诗和真并列,当我们离开真实的时候,也许便与诗背道而驰了。
先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度的时代热情,在诗作里融为一体,在创作上力求突破时代和环境的樊篱,这使作品具备了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就诗的风格而言,有的雍容,有的峻拔,有的明丽,亦不时带着感伤甚至有点凝重的情调,虽是时代使然,却也不能不说寄寓了诗人无尽的悲悯情怀。但他毕竟是严肃的,认真、理性、沉着地思考现实,追索时代,不仅写了偏僻山村的生活情趣,也写下了读来回味无穷、给人深沉之余痛的际遇与默然。现实与环境的错综,梦幻与现实的交织,这个特征必然地着色于他的诗行中。从诗中看得出,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生活飞跃的变化与美好会到来的愿景,先生关切、寄托、期冀着这一切。如《党课》写着:
我冷静了!/我清醒了!/我有了斗争的力量!/我看见夜色在仓皇退去/东方已出现希望的曙光!
先生一向似不尚情节而重炼意。那意境也者,不就是“清淡时恰似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骤雨”般动人的风采吗?在诗人的眼中,山村风物琐碎如《石磴》《老石桥》《房东》等等皆可信手拈来入诗,于寻常中见挚情,在平淡里显奇崛。他对乡间小人物无不寄予同情,以清丽隽颖的笔墨涂抹出普通人的悲欢来,平易晓畅,明白如话,偏又娓娓动听,撼动人心,让人只觉其真,不觉其俗,平淡、平静、平和的山村在他笔下得到诗意的描摹。
先生的《牛犊》非常地动人:
哞哞几声叫/嗅嗅花舔舔草/温喣的阳光下伸伸懒腰。/童年、乡里/我也这般小……
我读《就是这条田塍》时亦觉分外纯真天然、亲切诚恳:
早牧的牛/在田塍上拉一摊牛屎/你把牛屎捧到田里/再用脚搅匀/我望着你微驼的背/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老农的一生。
我还特别喜欢《派饭》:
倒出准备过节的米/到邻村孩子舅家/借两斤白面/坛子里掏几个鸡蛋/烙一只饼/熬小半锅稀饭;灶上另一口大锅/焖着红苕干/杂一点苞谷面/那就是一家人的早餐;我不忍心吃饱/我装着吃得很饱/一股咸涩吞进了胸间/放下半斤粮票一毛二分钱/主人执意不收/拉扯了半天/我赶快告别/因为我不走/他们不会端饭碗。
此诗情动恣肆,写得如泣如诉,慷慨淋漓,凝重且激越,这仅仅是写那顿平常普通的农家派饭吗?小诗概括的内容是这样深邃、宽广且细腻,不时闪烁的心灵火花引人入胜,启人遐思。这些叙写极其平凡的人与事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生活情景中,很自然地把读者带入了情景交融的诗的画面、诗的境界、诗的视觉美。诗句剥离了文字表象的浮华,链接着对那段物资极度匮乏岁月生存图景的哲思,其对社会形态的价值引领显得弥足珍贵。
世事变易,岁月匆匆。转瞬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先生所忆念的山村早是另副模样,作者的期盼不仅早已在他曾经描写过的土地上成为现实,而且连那隐隐的“沉默不语”也早已转化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盛大欢腾了。但在先生的忆念里,既有精神原乡的演绎,也有那个年代芜杂心灵的沉淀与洗涤。我们依旧可以读到他的全部热诚及他心向大山、心向农民的初心,亦能感受到生生不息的生活气息、浓郁深厚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印记。在他的诗情里,蕴含着鲜活的人性和睿智的审视。这构成了他诗作独具的魅力,也是他这个人的魅力。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永健新近在其专著《中国当代诗歌流派研究》中如是品鉴:研究当代中国乡土诗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乡土诗,如果缺少了湖北乃至全国乡土诗人之一的刘益善的乡土诗是不完整的。纵观刘益善的乡土诗,无疑表现了他与农民父兄血肉相依的情愫和刻骨铭心的“连系”,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农民20世纪50-80年代的生存环境与坎坷命运。
我始终感怀老诗人徐迟在所作《序》中的那段话:“到读者多年后还读到这些诗时,我们已经改变了并刷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和中国农村的面貌,中国农民也正在富裕起来了。即便如此,或是正是因此,还可以让我们读读《我忆念的山村》,看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想,这不仅仅是《我忆念的山村》带给一位有预见、有展望、有愿景的老诗人的忆念,也为今天的读者带来些许轻灵隽永、绵绵温热的忆念。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