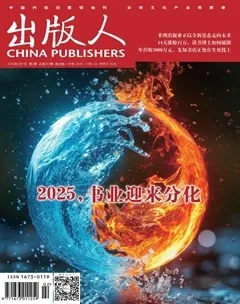儿童文学视域下生态美学带来的疗愈
《欢喜的森林》将儿童文学与生态美学意识相结合,通过作品中主人公“欢喜”的视角刻画出森林秘密笼罩下人与动物离奇的生活场景。作品将森林中的动植物与生活中的事物拟人化,并将乡下日常生活与儿童心理视域相结合。主人公欢喜与姥姥、山林中奇异动植物以及大自然的联结,与欢喜对都市生活的排斥形成了对比,展现了与生态美学联结的儿童文学对儿童心理的治愈,是文学建构大型虚拟想象场景的典型。
“森林”代表的生态美学与文学的联结。儿童文学中的生态美学赋予了自然界及其中的动植物生命力量与内在价值。作家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把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即生命体是具有其自身客观的“善”的存在物,主张尊重作为整体的生物共同体,承认每个动植物的内在价值。《欢喜的森林》以主人公的视角引出虚幻的森林与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的神秘融合,将日常生活与古代典籍《酉阳杂俎》中的动植物通过文学的笔法融入故事里,集中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将动植物的特点与传说用生动的语言刻画出来。通过欢喜与多个神秘角色的交流与心灵感应,将自然的奥妙与儿童的心灵成长联系在一起,是作者将文学与生态美学相融合所展现出来的生态价值的外化,同时也是生命体给予人类生存资源,与人类和平相处的“善”的体现。
作品背后文学的心灵治愈。文学具有精神分析治疗功能,通过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智慧与幻想的互动关系来虚构一个精神世界,从而达到对心灵的治愈。叶舒宪先生指出精神分析曾被简称为“谈话治疗”,哲学家保罗·利科又称之为“进入到对仅有的那一部分可以言说的经验之研究领域”。这些说法都揭示出精神分析作为某种语言技术的实质,这与作为语言艺术形式的文学本来就是完全相通的。《欢喜的森林》通过在主人公心里设置一片森林的场景,以及姥姥带着欢喜探索森林意义的情节,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心理疗愈功能。在姥姥的引导下,欢喜真正敞开心扉接纳世界,感受森林的美好,治愈了欢喜自闭的心灵。作者的视角进入儿童的内心深处,将其中的真善美与作为儿童的人的本质深入挖掘出来,并辅之以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智慧与幻想的外显成长要素,使读者意识到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作品相辅相成、互相联结的关系。
虚拟场景建构带来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提出:“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欢喜的森林》正是关于儿童愿望的幻想,这个愿望包括对乡下生活的向往以及与城市生活的和解。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儿童的内心需求总是容易被忽视。弗洛伊德指出,“孩子的游戏是由其愿望所决定的”。例如孩子总是做“已经长大”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模仿他所知道的年长者的生活方式,且会意识到把愿望隐藏起来至关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儿童所向往且需要的幻想与模仿是现实世界中所没有或缺少的必要生长条件与生存体验,这就需要有一个帮手去帮助其构建这个幻想场景。儿童文学的出现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对童真的再发现与再唤醒的作用,它真正将儿童置入了一个现实社会中所没有的童真世界,人的本质被唤醒,内心深处对童年童心的渴望被激发,从而带来愿望的满足,达到弗洛伊德所指的“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的美好结果。
《欢喜的森林》通过建构一个大型的生态区域与心灵疗愈功能的交互形态,达到儿童愿望的实现,使读者通过欢喜视角下的奇幻之旅深刻了解到作者的真正意图。作品正是作者想要让孩子们拾起童心,治愈内心深处有愿望缺失的童年,在社会的共同重视和帮助下真正地与自我和解,与快节奏社会和解,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愿望的文学展现。■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