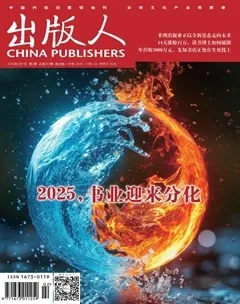一家开在村里的民营图书馆,能活下来吗
人与人之间互为内容,社群中的每个人既是贡献者,也是消费者,社群和图书馆共同繁荣。
在距离大理古城约3公里外的三塔脚下,绿桃村内,隐匿着一家名为“书理”的民营图书馆。书理不依赖社会捐赠,也不靠创始人自掏腰包来维持运营。在今天,这样一家开在村里的民营图书馆有可能生存下来吗?
事实证明,这家独树一帜的图书馆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在6年间从盈亏平衡发展至盈利,不仅拓展了空间,还吸引了770多位共建人,藏书量近2万册。
2018年,文林在大理古城创立了这家融合了民宿与阅读功能的图书馆。2020年,主理人小歌加入,书理开始尝试“以书换宿”模式——捐赠书籍可以享受住宿优惠。随后,书理转型为“共建图书馆”,并于2023年3月迁址绿桃村。这家图书馆“野蛮生长”,生机勃勃。
“擅走野路”的主理人
小歌的微信签名是“从来擅走野路”,这6个字几乎概括了她运营图书馆之前的人生轨迹。对于此次采访,小歌感到惊讶,因为她不明白“一个不卖书的图书馆怎么会吸引出版行业的关注”。她认为“书店主理人”这一身份并不足以定义她。在采访中,她甚至突然反问记者:“你是怎么看待生命和死亡的?”对自我探索和终极意义的追求,贯穿了小歌运营书理之前的10多年人生,也是她运营书理的重要驱动力。
大约20年前,小歌在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曾参与非政府组织实习。大四时,出于对就业之外“更真实的世界”的向往,她做出了第一个惊人决定:退学游历。她开过瑜伽馆,曾是某互联网品牌初创团队成员,在政府部门做过编外人员,在外企咨询公司担任过项目经理。小歌回忆,那是她人生前半段成长迅速的几年,为她积累了商业运营经验,拓宽了行业视野,“特别过瘾”。多年后,提及正在运营的图书馆和参与的公益项目,她仍认为兼顾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她所有项目的核心理念。几年后,小歌从外企“裸辞”,前往云南经营独立书店,她的生活因此增添了阅读和多元文化的新元素。“那时的大理是真正的乌托邦,独立书店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小歌回忆道,“读书对他们而言就是生活的日常。”她至今仍然乐于回忆那时在大理见到的充满冒险精神的背包客,其中许多外国人随身携带书籍,他们会将看过的书留给书店,书店以相近价格收购。在那里,知识的分享随时随地都能开启,无须邀请、策划或提前宣传,无论是室内还是街头,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写作、书籍、音乐和电影。
生活将小歌推向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她遇到做茶的朋友,便一同进山数月或半年,从茶山地貌、土壤、树种、气候全面了解茶叶;遇到精通日料的朋友,就跟着跑堂半年,深入了解食材、文化和食客需求;在新疆旅居时,她义务帮助本土企业家从零开始建立社区图书馆,亲自撰写书单、采购书籍、布置环境,并组织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她不仅关注事物的结果,还对其起源和过程充满好奇。这一切给小歌带来了多元文化体验。这些看似不同的经历、浓烈的理想色彩,都成为小歌注入书理的基因。2020年,当大理土著文林联系小歌,希望她帮忙运营图书馆时,小歌和书理的缘分就开始了。
“赶走”读者的图书馆
2018年,文林在大理古城的黄金地段开设了书理,旨在将阅读带回乡村和大山。然而,民营图书馆要想长期稳定经营,既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也需要不断更新书籍。仅靠个人资金或社会捐赠显然不可持续。
那时,“以书换宿”的方式也困难重重。住客不认同这一理念,对优惠力度不满,认为捐出优质图书“不值得”。还有人认为自己和书理只是交易关系,退房后便删除了主理人的微信。这样一来,书理既留不住人心,也聚拢不了好书。小歌认为,“以书换宿”只是手段,并非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书理如果要成为集合智识生活的公共空间,就离不开人的参与和相互影响。于是,她将书理定位为“共建图书馆”,并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赶走”读者。
小歌决定不再接受网上住宿订单,而是谨慎地选择豆瓣、微信和小红书等适合书理的平台进行宣传,因为许多住客是通过线下口碑了解到书理的。她不再接受某些赠书——成功学、心灵鸡汤、教辅材料等都被清理掉,只留下几本好书,从头开始。拒绝来之不易的顾客,难道没有顾虑吗?小歌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同频的人”,营造良好的空间生态和社群环境。与其他书店相比,书理的点心、饮品异常朴素:几块钱的曲奇、简单的咖啡和茶水。这是因为小歌不愿意看到书理成为人们拍照打卡的网红店。她会制止甚至“请走”那些破坏阅读氛围的顾客。2024年,因为太多游客直奔天台与三塔合影、大声喧哗,她撤走了图书馆天台的座位,让人“无卡可打”。
2023年上半年,小歌又做出了一个“逆势而行”的决定:将书理搬到距离大理古城约3公里的绿桃村。这等于放弃了一大批流量。搬家之后,来到书理的群体更加精准——闲逛的游客少了,除了附近居民和常住大理的读者外,专门为书理、为阅读而来的读者增加了,甚至有几位老读者特意为此搬到了村庄附近居住。
“人和人之间要互相推动”
在采访中,小歌多次用不同表述阐述了“共建图书馆”的核心理念:“人与人之间要相互推动。”她希望通过共建图书馆“让更多的普通人看到普通人”,通过知识交流“让生命得到成长,推动人的觉醒”。
在大理古城时,书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店内提供的体验项目和住宿;搬到绿桃村后则是体验项目和科普活动。小歌告诉我们,那些如今成为图书馆“顶流”的支柱项目,几乎都不是为盈利而设,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自然形成的。
例如小歌之所以想要推广非遗甲马(画有神像、云南民间用于祈福的木刻版画)制作体验项目,一是因为在书理连线海外华人的春节活动中,甲马是“最通俗易懂,最能连接人的情感”的物件;二是因为她希望推广甲马的非遗传承人老张。一开始,体验项目并未打算收费,但随着前来体验的人不断增加,供不应求,它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收费项目,并在2023年荣登大众点评榜单大理手工体验榜前三。
书理开设绘画项目的逻辑也是如此。小歌听到村里的孩子们说,学校里的美术课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于是多方打听到一位来自北京宋庄的画家,请他免费为孩子们开设绘画体验课。后来,由于太过热门,绘画体验还成了面向公众的固定收费服务。
书理与共建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建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书理真正成为人与人相遇的平台、创意和知识的孵化器。心理咨询师黄老师曾经在书理举办活动,为大家讲解梦境,如今准备自己开课;一位素人女孩在书理发起有关苏格拉底的系列讲座,收获了忠实听众,如今也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
书理的管理者通常是一名长期员工加上项目式志愿者,志愿者要在项目周期内完成自己提出的目标。除了短暂的旅游旺季以外,因为空间环境良好、读者自觉,维护接待的成本很低。同时,志愿者和员工都亲力亲为,动手实践,保洁、园林维护、小改造,都是团队一起进行的,其他支出也很少。
或许可以将书理的这一“商业模式”称为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人与人之间互为内容,社群中的每个人既是贡献者,也是消费者,社群和图书馆共同繁荣。但小歌的说法更朴素一些,她希望所有共建人,志愿者或读者“互相给对方一些真实的东西”。或许,这么一个生机勃勃、同频共振的群体,就是书理生命力的源泉。
书理的未来时刻都在变化着。小歌透露,应一些“希望收到陌生人的新书”的共建人的要求,她可能又要重操卖书的旧业。采访当天,书理已经获得了出版经营许可,可以出版一些记录村里孩子们的故事的画册。“这又是一个漫长又好玩儿的过程。”小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