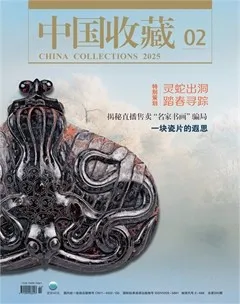看!这些“五彩斑斓的黑”

在长达2000年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黑釉瓷器始终保持着一种低调的存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黑陶,其黑色的色泽显然是早期文明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渗炭工艺的应用使得黑陶呈现出纯粹的黑色,为中国陶瓷文明的色彩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各色瓷器发展的历程各有不同,以古人之思维,黑色每每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陶瓷工匠们极力要摆脱这一釉色的束缚。直到有一天,匠师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黑色,并巧妙地将其融入瓷器之中,创造出层次分明的美感,使之成为其他釉色的参照基准。可以说,在整个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中,黑色既为始,亦为终。
黑釉瓷器的生产可以上溯到成熟瓷器创制的东汉晚期,而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不经意间在中国陶瓷的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两晋时期,真正的黑釉瓷开始出现。浙江德清窑在这一时期烧制的黑釉器,釉面滋润光泽,色黑如漆。南北朝时期,黑釉烧制技术传入北方,河北、河南等地的窑场也开始烧制黑釉器。进入隋唐以后,黑釉器在北方各窑场大行其道,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许多窑场均开始批量烧制黑釉器。而在南方,黑釉器烧制技术经由婺州窑、瓯窑南下,影响了福建东南一带的窑场。宋代是黑釉瓷的繁荣时期,其间黑釉瓷的生产地区迅速扩大,出现了大量专门烧造黑釉瓷的窑场。

磁州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民窑,以其独特的黑釉瓷器而闻名遐迩。窑址分布在河北省邯郸市的峰峰矿区彭城镇以及磁县观台镇一带,以观台窑为中心,因其地宋属磁州,故名磁州窑。又因磁州窑的影响力极为广泛,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均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烧造,例如河南的当阳峪窑、山东的淄博窑、陕西的介休窑等。即便是南方地区的江西吉州窑、福建晋江磁灶窑等也深受其影响,从而在宋元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系。
提及宋瓷,世人多论“ 汝官哥定钧”,实则所谓“五大名窑”不过是宋瓷有顷之一,仅代表了士大夫清雅艺术的审美取向,而磁州窑则是民间艺术的智慧结晶。
古雅朴拙
“ 鸡心罐”是宋金时期北方地区较为流行的器型,因形似鸡心而得名,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窑口皆有烧造。此罐(图1)圆口,腹下部渐丰,足墙较为低矮,造型敦实。罐外满施黑釉,口沿处施酱釉,外壁施釉近底,足露胎。其釉色黑中透亮,深邃古朴,犹如历史长河中沉淀出的一颗黑珍珠,让人不禁沉醉于这玄青的独特魅力。



在磁州窑的诸多名品中,以黑釉剔花最负盛名。剔花是制瓷传统装饰技法之一,最早出现在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黑釉剔花法是在瓷胎上先罩一层白化妆土,干后再罩黑化妆土,便成上黑下白两层,用刀具刻划出纹饰后,剔掉纹饰以外的黑化妆土,露出下层的白化妆土。这种工艺的关键,是要完全刮掉上层黑化妆土而不伤底层的白化妆土,对工匠的技术要求极高。
例如这件黑釉剔花鱼草纹罐(图2)器型硕大,唇口,圆唇平折,短颈,丰肩鼓腹,腹下收敛,底承圈足,足沿较宽,旋削渐层内凹,修胎有力。通体以白地剔黑花装饰,肩部及下腹部有双弦纹分隔,肩部剔一圈卷草纹,主纹饰间以鱼纹,构图繁而不乱。此罐整体剔划技法老练,线条流畅韧劲,黑白分明,尤见磁州窑古雅朴拙之风韵。
“铁锈”添彩
磁州窑所产的黑釉瓷器,仅次于其白瓷产品,颇具特色。陶瓷工艺师将他们在白釉器物上创新的装饰技术,同步应用于黑釉瓷器,从而赋予了后者前所未有的丰富装饰性。例如黑釉酱彩瓷器,它借鉴了白釉酱彩的装饰手法,采用高铁黑彩颜料,通过弹洒技术施于黑釉表面。经烧制后,器物表面呈现出黑色釉面上的棕色或棕红色斑点,同时也可以用这种高铁彩料绘画出纹饰,展现出显著的装饰美感。

此荷叶盖罐(图3)器型敦厚,盖作荷叶状,叶边沿造型宛若微风吹过,自然飘逸。胎体厚重,通体施黑釉,腹部数块条形铁锈花褐斑与黑釉相互交融,静中有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韵律。在黑色釉面上绘制酱褐色花纹的技艺,俗称“铁锈花”,因其花纹色泽酷似铁锈而得名,属于结晶釉的一种。铁锈花装饰技艺的图案多为不规则的斑点、条纹,或是简化了的花卉纹饰,展现出一种洒脱而不拘泥的风格。
另一件黑釉罐(图4)为唇口,短颈,鼓腹,浅圈足。器身外施黑釉,釉色乌黑如漆。黑釉之上绘褐彩鸟纹,下笔似无所想信手而来,寥寥数笔即出鸟振翅欲飞之貌,非熟工不可为。这种写意之美正是磁州窑的艺术特色所在。
这只矮梅瓶(图5)也带有类似的褐彩纹饰,此瓶因上部形制与梅瓶极其相似但腹部较短而得名,外国学者多称其为“半截梅瓶(Truncated Mei-ping)”,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 吐鲁瓶”。此类瓶有两个特点:一是基本特点与梅瓶一致,即造型优美,制作精良,均带有装饰且比较稀少;二是只在北方诸窑生产,南方各窑几乎不见。磁州观台窑是生产矮梅瓶最多的窑场之一,矮梅瓶的用途原本为酒瓶或醋瓶,但自北宋后期开始也被用作花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洛神赋图》中即绘有仪仗侍从捧持矮梅瓶插存珊瑚枝画面,由此可知此类瓶器亦作陈设花器。
这只矮梅瓶口呈矮梯形状,颈部短小,肩部圆润,腹部斜曲,整体器形饱满而圆润。其上施以黑釉,并点缀以铁锈花装饰,釉面光滑如镜,闪耀着玻璃般的光泽。铁锈斑点的笔触自由奔放,生动自然,营造出简约而光彩夺目的艺术效果,充分展现了古代窑工的智慧与匠心独运。
黑白互映
宋代茶文化兴盛,借由“ 茶色白,宜黑盏”的斗茶之风,以建窑、吉州窑产品为代表的黑釉茶盏风行一时。与此同时,其他窑场也积极竞争,形成了南北并重、各具特色的生产格局。工匠们各展所长,在黑釉茶盏的釉色上精雕细琢,创造出“色彩斑斓”的黑釉瓷器,如兔毫釉、玳瑁斑、剪纸贴花、木叶纹、黑釉印花、黑釉彩斑、黑釉剔花等多样化的装饰技艺。
此盏(图6)微敛,鼓腹,腹下缓收,圈足微撇。口沿作“白覆轮”,碗内饰有5条带状铁锈花斑,如花瓣绽放,又似夜空烟火,为单调的黑色釉面增添了几分生动与趣味。

“ 覆轮”这一名称源自日本,意指“ 镶边”,其灵感来源于当时的金银器工艺。工匠们运用精湛的技艺进行仿制,首先将黑釉均匀涂抹于器物之上,然后放入高温窑炉中烧制,接着使用竹刀仔细刮削器物的口沿部分,最后在边缘施以白釉。经过这一系列繁复的工序,黑与白的对比鲜明,清晰可辨,展现出瞬息万变的美感,被赋予“ 覆轮”之美誉,实乃恰如其分。
依据年代资料的比较分析,这些器物的流行时期,部分上限可推断至1 1世纪末期乃至更早,例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莲瓣式碗等。然而,其他不同样式的器物年代则明显较晚,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斗笠式碗、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束口式碗,以及藤田美术馆的油滴鸡心式碗等。日本学者也将这些器物的年代判定为1 2 世纪或1 3世纪,即北宋晚期或金代。
与其他茶盏相较,此类盏略显粗糙,然,正如《道德经》所言“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普通则不易引发贪婪之思,外观呈深黑色泽,则难以滋生爱慕之情,加之尺寸适中,边缘微收,形似钵盂,无一不蕴含满足之意。持此盏研茶沏水,顿感心境平和,宁静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