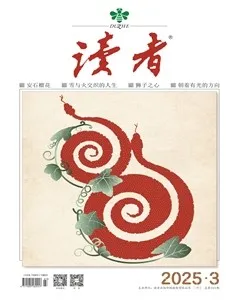朝着有光的方向

薄世宁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工作23年,他是一位很容易“入戏”的医生,要在感性与理性间寻找工作的平衡——这也是每位医生毕生的功课。
以下是薄世宁的讲述。
医学就像个“倔强老头儿”
前阵子,我收治了一位50多岁的女病人,她得了顽固性心衰。一开始,我们考虑她得的是应激性心脏病,一般一两周可以治好。但她在ICU里治了一个月,情况还是没好转,心衰反复发作。有一天,一位年轻医生提出,患者的腿因为坏死被切开,每天接受冲洗,会不会是这种冲洗导致了心脏负荷过重,才会久治不愈?但如果此时缝合伤口,又有加重她心衰的风险。我综合判断了一下,认为还是缝合对她最有利。于是,我们抓紧给她做了缝合,果然,第二天她的病情开始好转。
在ICU里,转机有时来得很迅速,甚至可以说就在医生的一念之间。但在它到来之前,更为漫长的时间里,医生需要精确管理病人的生命。
病人进入ICU后,心率、心电波形、血氧饱和度、血压、呼吸、中心静脉压等情况都会被24小时监控。在ICU工作久了,医生会习惯医疗仪器在耳边响个不停,但这种声音转化为急促又持续的蜂鸣声,就是病人生命数据极度异常的信号。一听到这种蜂鸣声,医生就会弹射起步去抢救。
有一回我值班,一位刚做完全麻手术的病人的呼吸机忽然打不进去气,还发出快速的、响亮的“啪啪”声。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血氧饱和度从90多降到80多,再到70多,还在持续往下降。照此下去下,病人在几分钟内就会窒息死亡。
必须立刻找出问题。我和同事们先关掉病人的呼吸机,重启检查,机器是好的;同时有护士捏皮球给病人输气,只捏了几下,就感觉跟捏石头似的,坚硬无比——皮球也输不进去气;而后,我推测病人的气道里有异物,但用气管镜一查探,病人的气道是通畅的。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还在下降,心脏快要停跳了,原因却还未知。我强迫自己冷静,最终判断是极其罕见的“寂静肺”,也就是麻醉药物导致的气道广泛痉挛,肺内空气只进不出,积气直至无法再进气。我们立刻用上了对应治疗药物,病人的状态逐渐平稳。
上述的所有判断、施救措施,都是在两三分钟内完成的,再资深的医生也难免心慌。毕竟代价是生命啊!
这种时候,能遇到一位可以信任、值得托付的医生,对家属来说太重要了。医学就像个“倔强老头儿”,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性格,坚持原则,用数据说话;阅历丰富、沉着冷静,但慈爱就藏在其冰冷的面具后面。患者想托付的医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病人不需要一个哭哭啼啼的医生
我第一次在ICU哭,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后。我跟着上级医生接诊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得了慢阻肺病,已是晚期,一来就是抢救状态,镇静、气切,上了呼吸机。气切容易引发感染,感染就要用抗生素。他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用药,身体已产生耐药性,但感染还在继续,陷入了恶性循环。
老人的子女们都特别友善,那时候我只有28岁,刚入行,想不遗余力地救他们的父亲。但在ICU里住了两个月后,老人还是去世了。那天我躲到楼道里大哭,情绪非常复杂。我明明那么努力地去救了,为什么还是治不好?
正式做医生的第一节课,就是要学会收起不良情绪。否则,你怎么用理性的态度去为病人看病?病人不需要一个哭哭啼啼的医生。客观中立地对待病人,更能让病人获益。但有时对病人和家属的亲切感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眼下我主管着一个男大学生患者,他在睡梦中动脉瘤破裂出血,脑功能重度损伤,昏迷不醒。父母放下外地的工作,在ICU陪了他半年。他的父亲对我说:“特别后悔,以前陪儿子太少,觉得他小,没什么可以跟他说的。等他躺在病床上了,我才知道来不及了。”我也是做父亲的,听完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10年前,有位43岁的肺癌晚期病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助她再活一年半左右——她的儿子正上高二,她想活到他高考完。她当时的情况其实很糟糕,不能做手术,也难说有保守治疗的方法。但在我和同事的建议下,她做了穿刺检测,竟找到了合适的靶向药。后来,她几乎痊愈。
生死攸关的决策
多数进入ICU的病人是神志不清的,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做决策的能力。那么,那些生死攸关的决策由谁来做?
近10年前,我参与抢救了一位羊水栓塞的孕妇。她有穿透性胎盘植入的情况,在剖宫产手术中突发羊水栓塞,心脏一度停跳,凝血功能也垮了。她接受了子宫切除手术,被送进ICU时,包括呼吸系统在内的多个器官都衰竭了。
我判断她并发了严重的脑水肿,需要立刻脱水抢救。但她的肾已衰竭,没有尿液,只能通过CRRT(连接性肾脏替代治疗)来脱水——穿刺她的股静脉,置入一根长短粗细像筷子一样的导管,把血液引出,过滤清除掉里面多余的水分、炎症因子和其他毒素,再把血液导回人体。但这会有再次室颤和大出血的风险。
当我把这一大堆概念告诉病人的丈夫时,他只是不停地说:“我整个人都是蒙的。”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医患之间要“共同决策”:医生告知诊断、治疗方案和可能的风险,患者或家属在评估后自主做出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医患合作关系。但是,当患者命悬一线时,患者或其家属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更现实的情况就像那位孕妇的丈夫,他的人生阅历、知识储备、决策思路在此刻都没有用处,他正在经历“理性休克”。
我告诉他:“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但我是个丈夫,也是个父亲,我希望你能同意我们做这项操作。”他同意了。采取措施后,病人的情况开始好转。
有些医生可能会担心,给患者或家属的建议多了,是否也要相应地承担风险?
对大部分病人家属来说,医生帮着做决定,是在替他们分担责任与压力。至少,不论日后的结果如何,他们已经让病人跟着医生做了最理性、最充足的治疗。
“不放手”的时刻
我刚工作那几年,参与救治了一位因冠心病、心肌梗死引发心搏骤停的老太太,她到医院时已瞳孔散大,我们判断预后不佳。之后半年里,她的丈夫一日不落地来ICU探视。
有一天,他穿戴正式地来到医院,请求我们允许他为老伴过一次生日。我和几个护士陪他一起来到床边,他开始回忆他们年轻时上山下乡的故事。而后他唱起一首老歌,边唱边拉老伴的手。我突然看到两滴眼泪从老太太的眼角滑落下来。当天,她去世了。
我原以为这位老太太是听不见的。深度昏迷、脑功能严重丧失,她难道还能有听觉吗?但是从那天起,我开始坚信,或许还有别的力量能够让她听见,让她感受到,亲人就在身边。谁敢说爱不是一种治疗方式?
我时不时会问自己:ICU的治疗目的到底是什么?放手或不放手,取决于什么?不放手不是不顾一切地抗拒死亡,也不是一定要用最贵的机器、最好的药物推迟死亡;不放手是不抛弃病人,使用科学的手段舒缓他们的痛苦。
一个24岁的患癌女孩,意识到病情已无法挽回,强烈要求离开ICU,入住普通病房。几天后她就去世了。
一位74岁的慢性肺病、呼吸衰竭患者,来ICU治疗,希望早日摆脱呼吸机。他住了一个多月,大概是治疗时间和花费都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他挣扎着用笔写下“回家”两个字。子女们多次劝说无果,最终把他接回了老家。
其实,尊重他们想离开、想回家的愿望,也是一种不放手。做医生,不仅要有知识,还要保持适度的温情。
一位脑功能受损的大学生,生日那天,他父母向我申请早点儿进ICU陪陪他,我同意了。
其实我多次向这对父母提过,孩子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他们不肯给孩子做脑死亡的评估,生怕结果出来,最后的希望也流走了。后来我也很少提治不好的事。
治病人,也要治病人家属。面对家属,医生不可有知识层面的傲慢。关怀和理解他们,就是给他们最好的治疗。
朝着有光的方向
现在回看做ICU医生的20多年,行业变化是明显的,重症医学的理念越来越完善。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我始终看不透死亡。一方面,就像一种新的疾病会让全人类恐惧,我不知道人死后是什么样的,这种未知让我恐惧;另一方面,我恐惧死亡可能预示的、永恒的别离。我觉得人生最悲剧、最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论你怎么努力,你终归是要和最亲的人说再见的。
我曾经听过ICU里的家属对着弥留之际的病人喊:“爸,你往前走!你朝着有光的方向走,你别害怕,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告别语,死亡甚至可能只是“暂别”——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不妨想象得美好一些。
死亡是什么?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无论答案是什么,医生的职责都是救命。这既包括延长生命让人活着,也包括让人在生或死时,拥有尊严和价值。因为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肖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