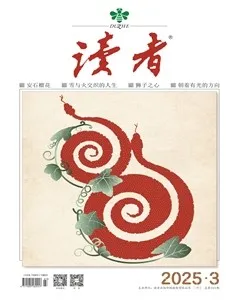只告白,不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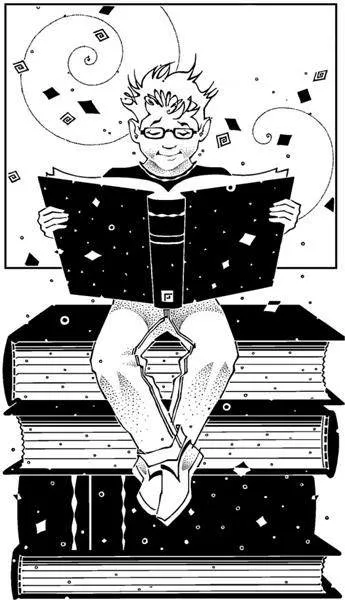
对我而言,《读者》不仅是一本杂志,更是一枚勋章。
出生于1990年前后的很多人,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场景:在我们的中学时代,几乎每个同学的课桌上都摆放过《读者》——那是唯一一本不会被老师没收的课外读物,也是唯一一本会在全班传阅的杂志。
哪怕是在学习极为紧张的高三,班主任也不曾阻拦我们在自习课上阅读《读者》,他说:“《读者》是一本好杂志。”
十几年后,当我拿着自己出版的书去拜访他时,他微微颔首,仅夸我努力。可当我提及自己在《读者》上发表文章时,他突然激动地说道:“好,好,能在《读者》上刊登文章,了不起。”
刹那间,我的心里似有火花飞溅,噼里啪啦,将少年时的自卑燃烧殆尽。
读书时,我并不是老师喜爱的学生,成绩中不溜儿,嘴巴不够甜,也没有出众的才艺,只喜欢埋头看书、写作。一个普通女孩待在属于她的青春里,敏感和压抑丝丝缕缕缠绕着她的心脏,缠成了习惯。
直到这一天,因为在《读者》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那颗被缠绕的心脏好像开始解绑。
当老师再三表示要多买几本刊登我的文章的那期《读者》,让学弟学妹们向我学习时,除了受宠若惊,我还有点儿虚荣地想到了“衣锦还乡”这个词。这是《读者》为我戴的一枚勋章,为我穿的一件灿烂的衣裳。当我开始认为自己耀眼,我便不再受困于逼仄的青春期,不再渴求别人的肯定,内心逐渐变得松弛,人生之路也更加宽广。
我将这段经历讲给好友听。
好友说:“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愿望是成为《读者》的编辑吗?”
当然记得,《读者》几乎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文化印记,塑造了我们对文字的敏感和热忱。因为这本杂志,我们尝试写作投稿,十几岁就定下职业目标。如果说《读者》是我们最初的文学土壤,那一封封手写信就是我们培育的绿苗,我们多么渴望这些绿苗能种植在《读者》这片土壤上啊。
盼望了那么多年,总算有了点儿收成。虽然我未能成为《读者》的编辑,但到底是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日日和文字打交道。
2021年,我终于在《读者》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拿到样刊后,我骄傲地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小时候,是《读者》的读者;长大后,成了《读者》的作者。”
这一刻,有个读者在替年少的自己向《读者》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