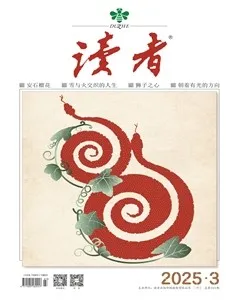真实的拥抱

吴媚儿长得不好看,小眼睛,白胖圆脸,下巴之下似乎还有第二层下巴,这让她的脸有点儿像一个光滑圆润的包子,令人有种想张嘴咬一口的冲动。她还戴着一副圆眼镜,金属镜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年,吴媚儿从城里转学到我们学校,成了学校的宠儿,因为她是从黄浦江西边来的,她是“上海人”。我们也是上海人,但我们不是她那种上海人。而我们住在东岸的人是怎么被他们称呼的?记得有一回亲戚家办喜事,从浦西来到浦东的小客人趴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指着田野间奔跑的乡下孩子呼喊着:“阿香,阿香……”
我是“阿香”吗?那个小“上海人”就是这么呼唤我们的。我喜欢这个名字,有一回电视里播放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面就有一个叫“阿香”的姑娘,乖巧漂亮。
吴媚儿来我们班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上高一的大女生。吴媚儿是“上海人”,这让我们无论怎么看,都觉得她是好看的。哪怕她的眼睛小而细,也不妨碍我们觉得像她那样就是一种时尚。还有,她居然用纸巾,而不是用手帕。在教学楼的阳台上,我们被老师安排看日食。晌午,课间操时间,我们每人拿了一片红玻璃,一颗颗朝天仰望的黑色头颅,右眼上一律盖着一片红玻璃,这让我们可以直视正被渐渐吞噬的太阳。吴媚儿在我旁边,她的红玻璃有些脏。我摸出叠成豆腐块儿的碎花手绢,说:“擦擦!”
我给我的手绢洒了花露水,它香香的,我自己都不太舍得用,但我舍得给吴媚儿擦红玻璃上的灰尘。可是吴媚儿拒绝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包,抽出一张雪白的纸递给我,然后又摸出一张,擦了擦自己的红玻璃。我捏着她给我的那张雪白的纸巾,抬头看向天空。暗红的玻璃过滤掉刺眼的强光,彼时我想,吴媚儿和我一样也要看日食,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正在被吞噬的太阳。
之后,我再也没有用过手绢,开始用零花钱买纸巾。那是吴媚儿带来的“城市之光”,16岁的我毫无悬念地接收到了。
吴媚儿进了校学生会,我们在学生会共事,我是文艺部部长,她是广播台副台长。她的普通话标准,来自城市的声音让她拥有了很多朋友。
那一日,校学生会组织与邻镇的中学联谊,我们坐上公交车,去往10公里外的另一座校园。吴媚儿穿着一身粉红色薄绒运动装,脚上居然是一双运动鞋,高高的鞋帮,圆圆的鞋面,鞋带又粗又长,系一个结,再系一个结,脚面就开出了一朵丰满的“鞋带花”,真够豪华的!我看了一眼自己脚上单薄而简陋的白跑鞋,心里隐隐生气。
联欢会开始了,所有人都被淹没在音乐声与欢笑声中,吴媚儿不再是最显眼的那一个。她和我们一样,做游戏,抢座位,鼓掌大笑。她总是很愿意冲上台去参与所有的游戏,可她总是输,输了要表演节目。她朗诵了一首诗,再输,再朗诵,最后,没有可朗诵的了,她站在舞台中央一脸着急。吴媚儿也不是万能的,我几乎有些幸灾乐祸地想。
我也输了一轮游戏,于是,我站到台上演唱了一首早已准备好的歌曲。我唱的是什么歌来着?对,《血染的风采》。我享受着被所有人瞩目的荣耀时刻,也享受着演唱一首歌曲时完全打开心扉的愉悦。突然,窗外闪过一个人影,穿着蓝色滑雪衫,戴着蓝色绒线帽,帽檐下露出两缕齐肩鬈发,是一个高个子的女生,背着双肩包……那种时髦,只有“上海人”才拥有。吴媚儿突然站起来,朝门外飞奔而去。
我的歌声并没有被打断,但是观众的目光被打断了。窗外,吴媚儿扑向蓝色滑雪衫,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拥抱啊!我们只在电视上看过。
我总觉得,我得到的掌声比吴媚儿获得的瞩目少了几许。那天回去的路上,吴媚儿依然挽着我的胳膊,我想我不能表现出点滴的失落感,更不能生气。我用近乎欢快的语气问她:“蓝色滑雪衫,是谁?”
“我初中的同桌,她转学到这所学校了。”
我告诉自己,吴媚儿长得不好看。可她与初中同学的那个拥抱,使她变得比白皙的、用纸巾的、戴金色眼镜的她,更浪漫、更时尚、更洋气了。她成了同学眼里城市的代表,我们以与她结交为荣。
很快,我们进入了高三,所有人都埋头进行高考复习,校学生会已经由高一或高二的学生接手,我们很久没有参加活动了。那个冬天的下午,化学课上,吴媚儿被班主任唤出了教室。下课后,我走出教室,看见她站在阳台上,面朝远处流动的寂静无声的运河。她一只手捏着金色的眼镜,另一只手正用纸巾擦拭眼角扑簌掉下的眼泪。
10米外的办公室门口,班主任正与一个中年男人说话。男人戴着黑框眼镜,也有着白皙的面庞、圆润的下巴……“早恋”这个词,在同学中疯传。葳蕤的青春,哪怕在荆棘丛生的高考前夕,也要挣扎出一段短暂的花期。
吴媚儿又转学了,在高考前的那个寒假。
5年后,我成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学校坐落在离上海市区70公里的远郊。我拥有一群比自己仅仅小5岁的学生,他们大多来自上海的郊区。再后来,我的学生越来越多,有时走在大街上,我会偶遇已经毕业的学生,那些女生会冲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时,我会想到吴媚儿,那个包子脸、小眼睛、胖墩墩的“上海人”。她让我第一次目睹了真实的拥抱。
如今我们早已学会了拥抱,也习惯了用纸巾,很多年轻人也许已经不认识手绢这种东西了,可是我的那些住在黄浦江东岸的亲朋,以及我的学生,他们和我一样,依然喜欢把黄浦江西岸或北岸的那片土地叫“上海”。对了,我写过一部小说,女主角叫“阿香”。我喜欢这个名字。“阿香”,香喷喷的“香”。
(静临风摘自《解放日报》2024年12月12日,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