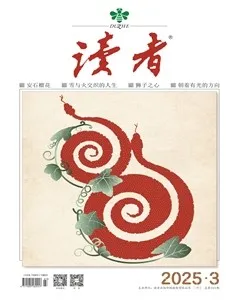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母亲节,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具体来说,是清洁卫浴和地板,如果清洗窗户的费用合理的话,那就一并清洗。对我来说,这份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一次家务责任。但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我的情绪劳动。
结果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丈夫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独自照顾三个孩子,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亲自动手。但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
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上的塑料储物箱绊倒——这个箱子是几天前他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他取出需要的东西,包好他要送给母亲和我的礼物后,就把箱子搁在了地板上,储物箱就变成了一个碍眼的路障,也是看了就令人生气的导火线。而要想把箱子归位,我必须从厨房拖一把椅子到衣帽间,才能踩着椅子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实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
“这正是症结所在。”我眼里泛着泪,说,“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一项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
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当你主动要求,并以正确的方式要求时,又会变成另一种额外的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我是唯一在乎细节的人,所以由我来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对我来说,情绪劳动使生活变成了一个竞技场。
我感到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微妙的分隔线上,一边要顾及他的感受,一边又要清楚传达我的想法。我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样主动积极地面对家务。不过我试图向丈夫解释这一点时,他很难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差别。“只要任务完成了就行,甭管是谁要求完成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听到他这样说时,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我并非第一个思考“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的人。社会学家当初创造这个词,是为了描述空乘人员、女佣和其他服务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展现快乐的模样,以及愉悦地应对陌生人的样子。
罗丝·哈克曼进一步扩展了情绪劳动定义的外延。她主张情绪劳动可能是女权主义的下一个战线。其后两三年间,“情绪劳动”这个议题获得愈来愈多的关注,有无数文章探讨情绪劳动及这种劳动的普遍性。
坦白说,我觉得那是因为女性已经受够了,忍无可忍。情绪劳动不仅仅是令人沮丧的、关于家事抱怨的来源,更是系统性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些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破坏性的方式将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凸现出来。社会深深地寄希望于女性担负起家中一切累人的精神劳动和情绪劳动,而那些受益最多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这些劳动。我们只好改变自己的语言、外表、言谈举止和内心的预期,以维持和睦。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为完成劳动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往往不被看见。
在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中,这种加乘式的情绪劳动会变成一种常态。日积月累,你的生活会变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驾驭它。你必须引导其他人在这套精心打造的系统中穿梭,以免他们被卡住或陷落。为了管理他人的情绪和预期,你需要越过重重障碍才能让人听到你的心声,耗尽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来的宝贵时间。
每个人都必须改变对情绪劳动的看法,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这项技能背后的真正价值。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劳动有其价值,并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关怀和管理情绪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是一种密集的解题训练,还可以获得同理心的额外效益。我们应该把情绪劳动变成一种人人都该拥有、人人都应理解的宝贵技能,因为它能使我们更充分地体验生活。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侣和后代的生活。当我们一起消除情绪劳动的不平等时,孩子们的未来就被改变了,我们的儿子可以学会恪尽本分,我们的女儿可以学会不必承担别人的分内工作。
(紫陌红尘摘自新星出版社《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一书,陆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