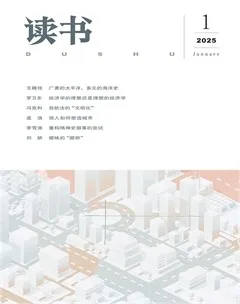延津三部曲中的百年心史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有两个主人公,分别是上卷的杨百顺和下卷的牛爱国。杨百顺离开老家延津,是为了去“别处”寻找安稳的生活;牛爱国在自己家里却仿若陌生人,以至彷徨于无地,愤而出走,竟回到了延津。所以,上卷名为《出延津记》,下卷叫作《回延津记》。这一本书实际上是两本书。它的续篇《一日三秋》也是围绕着延津而展开,主人公叫明亮,虽从小无家,却又能处处是家。对比杨百顺的决绝和牛爱国的困顿,明亮的泰然既像是他们的另一种前景,也像是作者有意给他们的困境以解答。三者加起来,即是我所认为的“延津三部曲”。由此,延津也不再是一个实际的地点,而是成了刘震云理解中国人现代漂泊历程的精神象征。如果分别用一句话来概括三者的整体意象,那就是“生活在别处”“无地彷徨”和“心有所居”。刘震云的小说那么多,为何独独拎出《一句顶一万句》和《一日三秋》,又为何将其称作三部曲?这是先做个交代。
粗略地说,刘震云在《手机》之前的创作,主要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关注权力、批判权力。读者熟悉的小林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不在本身,而在它对权力无形的反讽。也是因为权力,《故乡相处流传》里曹操的脚气成了所有人趋之若鹜的香蜜,《故乡面和花朵》里讲述者的话语才变得毫无节制、波涛滚滚。在名为《读鲁迅小说有感:学习和贴近鲁迅》的文章中,刘震云将这种批判立场变成了一种思想的自觉,自觉地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保持距离,站在平民日常的视角反思和批判权力。
但是,事情的吊诡往往是,越反对一个敌人,就越会变成那个敌人的样子。正因为其矛头所指是权力,其所立足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就无法直接呈现,甚至还不得不付出变形的代价。如果如刘震云所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那么,这种权力批判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采取了一种看似低低在下的姿态而已。
真正帮助作者突破这种二元悖论的,是他对日常生活自身之内在逻辑的敏感,也即是他从《手机》开始反复刻画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手机》里第三章“严朱氏”还只是相对浅显的感受,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撞开日常生活本身的秘密之门。最能直接体现这一点的是作者在该书出版后接受访谈时对写作立场的澄清:“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与这种俯视式写作不同,刘震云提倡的是倾听者的立场。在他看来,俯视是不好的,甚至仰视和平视也是不好的,而应该和那些书中的人成为知心的朋友,听他们讲,由他们讲。“写作也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事儿”,就是去听“那些说话不占地方的人”在说什么想什么。当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他的写作就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因此,他才经常提醒读者,我的小说读起来很绕,不是我故意要绕,而是生活中的理本来就这么绕,那些人说话很幽默,也不是我故意要幽默,而是生活的幽默原本就如此。也是因此,有学者将这种方式称为“叙事摹仿”。其实,哪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在摹仿呢,摹仿那个大象无形的“现实”,只不过各家所看到的现实及其关键不一样罢了。到此,刘震云就再也无意关心什么权力什么批判了。
在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刘震云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孤独:“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有特别巨大的区别。因为有宗教的社会是人—神社会,就是我们俩除了有交往之外,还有一个神,我们俩交往的时候都在跟神交往……但是不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信仰过宗教。你有心里话,必须找对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不止找到能说心里话的人是艰难的,而且,就算找到了知心朋友,朋友也很容易变成仇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知心和不知心也是会变化的,知心朋友有十个,但这十个知心朋友可能都变得不知心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神永远是人的知心朋友。神的嘴很严,人的嘴是不严的。祷告为什么要在密室呢?密室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进去。”这个中西社会模式的对比,在根本上切中了普通人日常交往的隐痛:正因为我们内心如此需要朋友,朋友才容易变成仇人。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孤独不是鲁滨孙式的孤独,也不是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而是和家的问题连在一起的带有伦理性的孤独。
西方的现代进程比中国早三四百年,对他们来说,家早已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宗教信仰。卢梭笔下的自然状态和自然宗教,司汤达刻画的爱情战争,其根源皆在于此,甚至到了世俗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K无可逃脱的审判生活,加缪大声疾呼的西西弗精神,都仍然是人与上帝之关系的回声。但中国的现代是从家的革命开始的,家既指向人伦,也指向中国人对历史对天地的感悟和理解。但此处的家的问题并不是指家的制度、家的模式,而是指我们每个人心中皆有体味的家的感觉,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身处世界之中能否找到的“在家之感”。
事实上,这个问题恰恰贯穿了延津三部曲延迭百年的线索。从时间上看,《出延津记》写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回延津记》是共和国成立到二000年左右,《一日三秋》则写到了可以微信视频通话的当下,前后延迭,正是一部现代中国的百年历史。然而,这部历史没有政治经济与文化,也看不到战争革命和灾荒,归本还原,唯剩下普通人庸碌琐碎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心灵在这些日常和无常中的漂泊。从杨百顺,到牛爱国,再到明亮,前后衔接,正是从追寻“别处”,到彷徨于“无地”,再到心有“所居”的历程。这既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演变史,也是这个民族的心灵在现代浪潮中沉浮跌宕的心史。
用小说来回望现代中国之变迁,几乎是藏在当代中国文学潜意识深处的持久焦虑,也是许多作家越成熟越想去主动承担的某种使命。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精神的核心在那个代表着儒家形象的朱先生身上;而在现实中,则体现在相互争斗的“白”“鹿”两个家族上,体现在白嘉轩那直直挺起的腰杆上。风俗伦理,浩然正气。贾平凹的《山本》里虽也写家,也用陆菊人代表儒,宽展师父代表释,陈先生代表道,但所有这些最后都隐没在一个更大的山川草木的世界里,历史的胜负,人世的输赢都显得轻飘飘的。而在刘震云笔下,无论是《出延津记》,还是《回延津记》,里面既没有约制人心的风俗伦理,世仇延迭的家族,也没有儒释道的搭配互补,和超越人世的自然世界。作者仿佛是用了笛卡儿式的哲学还原,原本靠得住的一切如今都靠不住了。这即是刘震云着意要我们看到的,现代中国在起始处的遗产,也是杨百顺们生命历程的底色。
不过,即使如此,这个延津世界仍和格非《江南三部曲》中花家舍百年大梦后的虚无迥然不同。如同海子在《答复》中,面对麦地,面对农耕文明衰败的命运所说:“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杨百顺手里所有的,不是别的,而是比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更决绝的去往别处的生命冲动,是即使没有目的也要去寻找的莫以名之的渴望。我们可以怀疑,刘震云的还原不免带有某种事后回望的解构,却不得不承认,对这种生命冲动的刻画还是抓住了传统中国在迈入现代世界时所凭靠的真正力量。杨百顺要逃出的延津,是所有靠得住的一切都不再靠得住的“这里”,然后去往“别处”,没有应许,没有指引。“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当年饱含悲情的希冀,在《出延津记》的主人公杨百顺身上有了最日常的展现。这正是我们的“出延津记”。
摩西的以色列人不必再“回埃及”,牛爱国却要“回延津”,问题是他要回的延津究竟是哪里?《回延津记》的牛爱国,是杨百顺的外孙,出场时三十五岁,有老婆有孩子有营生,辛劳中更多的是整密与平稳。他比当年的杨百顺所多的,似乎也正是困顿的中年比昂然的青年所多的。共和国成立初期诸多运动的轰轰烈烈,改革开放的汹涌热潮在书中都了无痕迹,只有波澜不惊的家庭生活如静水深流,渗透着每一个白天黑夜。但这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无法再继续,牛爱国被逼迫着走上了异路的漂泊,却意想不到地在曲折的旅途中找到了生活的盎然,而这也正是他当初比杨百顺所少的。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回延津记》结尾时,牛爱国正要接着去异地,生气淋漓,仿佛迈向一个别样的世界。所以,刘震云让牛爱国所回的并不是原来的故地,也不是四代人断断续续的命脉,而是当年杨百顺走异路逃异地的生命冲动。
历史是否会由此再次开始,我们并不确知;我们所确知的只是,这是牛爱国们的第二次生命,也是延津的第二次生命。然而,这第二次的生命还会像此前一样从昂然到困顿吗?异路和异地最终又会通向哪里?在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还有没有那“别样的人们”让我们去寻求?作者多半是看穿了这里的困局,才用《一日三秋》给出了别开生面的方向。
《江南三部曲》第三部《春尽江南》的结尾,是主人公端午借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现下这个时代发出的悲叹,言语之间,也像是作者借着端午而出场。“延津三部曲”的第三部是《一日三秋》,其色调既没有知识分子式的悲叹,也不像《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要借助于生命冲动的昂然,而是出人意表的温润明亮,正如同主人公的名字一样。而且,其明亮也不是只有明亮,底层还深藏着巨大的苦难,一如作者结尾所说:“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作者像是在写当下,又像是在写牛爱国和我们的另一种未来。
从内容上看,《一日三秋》复活了许多传统的要素,老董和黄道婆的巫术,明亮妈妈死而附体的阴阳相通,还有仙界下凡的精怪,花二娘的地方神话。但若抛开这些具体内容,作者的努力其实是想说,既然中原这片水土的人们几千年来经历过无数的灾祸和劫难,仍能够生生不息,那么帮他们渡过这些苦难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而这样的力量不正是现在的牛爱国们所需要的吗?或者说,这种力量是不是仍然潜藏在他们的身上?历史既是过往,也是当下。在小说和访谈里,作者都反复强调,这个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幽默,是花二娘要听的笑话,是面对生活的巨大苦难仍能够置身其中而又超越其外的泰然。
延津三部曲,是三种生活,也是三个阶段,个人的历史的都在其中。寻求别处的生活,是离家,是一步步走向陌生,也是想找到新的家;彷徨于无地,才必得从严整的安稳中挣脱,再次出发,这样,也就无需再彷徨;能将苦难化作轻轻的笑话,才是真正以柔克刚的力量,才能自己与万物与天地相通,才能心有所居,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生命不只是需要原初的冲动,也需要无能为力时泰然自若的洒脱。如果《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是还原式的某种“破”,那么《一日三秋》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立”,合在一起,正是刘震云为这个民族的现代历程书写的“心史”,一部每个普通人都在为离家、寻家而漂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