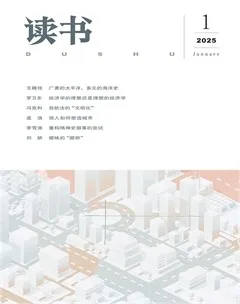五足牛的谶语
从宁夏银川到陕西榆林,北纬三十七度上下,以横亘东西的一条高速公路(青银+包茂)为分界,南北两侧就大约是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了。
不光是一条地理的分界线。始终与这条高速公路蜿蜒并行的就是明长城,以此和其东、西、北三面的黄河为界,中间的区域像是牧马人的套马索,正是《明史·地理志》所谓“大河三面环之”的“河套”,而往前追溯,属于秦始皇的“河南地”。这条分界线环毛乌素沙地南缘,处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区,是气候和地质地貌都很独特的地理单元,也是中国农牧交错面积最大、空间尺度最长的区域,具有十分相似的区域经济、文化特征。
分界线上如今分布着众多的城镇,由西而东县级及以上城市就有宁夏的银川市、盐池县和陕西的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区、榆林市、神木市、佳县。如果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其西部的起点城市我以为是宁夏的盐池县,而不是银川。银川位居黄河之西,历史上一直以“河西”著称,即便是在明人的眼中也是孤悬在“河外”的,这里得黄河灌溉之利,久负“塞北江南”盛名,与上述诸地的旱作农业差异明显。
盐池古为“昫衍”(或“眗衍”“朐衍”)地,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将“昫衍”与“义渠、大荔、乌氏”这些戎族相并列。除此之外,有关当地的讯息全然不见于史册,姗姗来迟的是《汉书·五行志》中一则怪异的“五足牛”报道:“秦孝文王五年(应为秦惠文王初更五年,前三二0),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同书引汉代谶纬学者对此莫衷一是的解读,比如刘向认为,这近于“牛祸”,并论证说:“足者,止也”,是戒示秦国统治者应停止的某些行为,如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奢侈过甚;或当时为战争需求,长途传输物资一直到遥远的北方,导致天下叛乱。而另一位易学大师京房在《易传》中说,这是因为秦国兴徭役、夺民时,所以才导致妖牛生五足。衍五足牛的异象,似乎传述了不短的时间,专以志怪的晋干宝《搜神记》也做了采集,并简略地概括了显然是来自刘向、京房的解读。
五足牛的报道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记述都表明,昫衍之地的原住民为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方式就是游牧。《史记》曾记述秦始皇三十二年(前二一五)蒙恬攻取“河南地”后数次徙民实边,但蒙恬死后的五六年间,中原群雄逐鹿,诸秦所谪戍边者皆复去,匈奴人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农耕经济即使曾经立足,也完全不具规模。自秦惠文王初更五年至明朝建立约一千八百年中,没有证据表明此地曾有过大规模的垦殖,当地这种以游牧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和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形态都没有重大的改观。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其历史变迁稍做梳理:汉承秦制,仍置昫衍县;东汉时废减该县,直至魏晋,此地一直为游牧人所占据。唐调露元年(六七九)设鲁、丽、含、塞、依、契“六胡州”以处突厥降户,其中部分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六胡州”的驻地多所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鲁州就在今盐池县境内,一九八五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发掘一处唐墓,《何府君墓志铭并序》显示其为何国人后裔的家族墓地,引人注目的是两扇石门上刻有胡旋舞图。宋时期,此地常为宋夏拉锯之地,而至迟在至道二年(九九六)即没于西夏;而元代悉为牧场。
中原王朝曾几度管辖此地,但支撑税收和戍边用度的支柱产业,是畜牧业和盐业。也许盐业的作用更为突出,宋人所谓“财用所出,仰给青盐”。昫衍之地盛产食盐,自汉代下讫民国时期,盐业发展历代延续不辍,“盐泽堆琼”甚至成为明代文人笔下的“四景”之一,明庆王府的长史周澄甚至赞叹当地的池盐:“若使移南国,黄金价可同。”早在西汉时期,其境内的惠安堡就有三处盐湖,西汉政府并设有盐官,对盐业实施专卖。唐代神龙元年(七0五)专置温池县(今盐池惠安堡附近),县名大概来源于温泉、盐池两个地名的缩写,据《唐会要·盐铁使》,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两员,巡官两员,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户百六十五户,并敕令专管支收用度;朔方节度使除管理防区军事,还兼管关内道政务,其中之一是兼任关内道盐池使,足见盐业专卖的重要意义。汉唐时期在该地安置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行政管理方面比较松散,特别是唐代实行羁縻制度,毋庸置疑,中原王朝通过对食盐资源的垄断性经营,相当大地增强了政权的控制能力。同时,私盐在民众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史·郑文宝传》和《太平寰宇记》都指出,此地居于沙卤,无果木,不植桑麻,树艺殊少,唯有池盐,百姓以采盐为业,以贩盐为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而换取粮食的地方之一就是邻近的灵州引黄灌区。
长时期以畜牧和盐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一直维持一种比较良好的水平。此地属鄂尔多斯西南部波状高原的一部分,是地下水的盆地,地下水从裂隙处涌出即为泉水。秦汉以来,无论中原还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城镇或定居点,均傍泉而建。如张家场古城,出土文物和规模都显示,似为汉代县城。该城所附近的北大池,从遗迹观察,当时面积至少为一百平方公里,水深至少达三十米。这符合《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晁错所谓“徙远方以实广虚”即移民实边时建城、营田的原则:“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可以遥想,盐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水泉盐泽,草木葱茏,正如中唐诗人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所咏“绿杨著水草如烟”,一派湖滩草甸和干旱半干旱草原风光。这也使人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统万城(今陕北靖边县北),大夏国主赫连勃勃相其地宜,决定建都于此时的由衷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
这种情形到了明代以后为之大变。明代的“套内”和贺兰山外即为蒙古势力范围。为处置边患,明朝政府立卫所,建城堡,分屯兵,所谓“缮城郭以守之”。但不久即发现这里地理宽漫,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分布几座守御的孤城,完全不能阻挡游牧人的侵扰。特别是正统以后敌患日多,边陲不绥,在边将的奏折中,从早期“刁斗相闻,旗帜相望”的从容一变为“城孤兵寡,有警猝难救援”的窘迫。职此之故,修筑边墙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成化八年(一四七二),由延绥巡抚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倡议,至成化十年(一四七四)六月,在宁夏巡抚徐廷章、总兵官范瑾的主持下,自黄河东岸至陕西定边县盐场堡,浚壕筑墙,修筑了一段绵延三百八十七里的边墙,被称为“河东墙”。
河东墙的修筑直抵黄沙。在余子俊看来,游牧人逐水草以为生,所以,凡属草木茂盛之地,一概划在边墙之内,使之绝牧;凡属沙碛之地,一概划在边墙之外,使之无法安居,如此可一劳永逸。这说明河东墙建在沙漠边缘,沿线生态已相当脆弱,此也为河东墙后来的命运所证明:仅仅六十年后,至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不得不将边墙南移十至二十里不等,另增筑“深沟高垒”一道,原因之一便是工程选址缺陷,沙土圮塌严重。明廷为实现戍军粮草自给,在边墙内侧大规模开荒营田,召军佃种。明人魏焕在《西园闻见录》中记载:“自筑外大边以后,零贼绝无,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孳牧遍野,粮价亦平。”本地降雨稀少,现代测量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三百毫米,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而农业开发最重要的方法是汲井灌溉,开发地下水资源,这尤其突出表现在对“水头”的控制和利用上。所谓“水头”,是明代西北边防中的专名,指分布在长城附近的湖泊、溪流、井泉等。为防止游牧人的侵扰,戍军将水头控制起来,一方面断绝游牧人的水源,另一方面用以浇灌土地。此地有泉名“铁柱泉”,据当时亲临实地考察的三边总督刘天和说,泉水面积“周广百余步”,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涸,“套虏”南下必在此饮水。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建铁柱泉城,将水泉围在城中,“占水泉,断胡马饮牧之区”,此为“御戎上策”。铁柱泉“四周空闲肥沃地土又广,合委官拨给,听其尽力开垦”,并给予“三年之后方从轻起科”的优惠政策。由于不断开垦和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地下水位下降,原生植被遭到毁坏,土地沙化加速,如遇暴雨冲刷,沟壑发育加速。
一九六0年六七月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率队考察盐池县,归后有《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一文(《科学通报》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呈现在侯先生眼中的铁柱泉城:“偌大一座城池,非但城内已经荒无人居,城外也是一片冷落景象。高大的城门洞,大半已被沙湮。瓮城之内,积沙亦多。”“至于围筑城中的铁柱泉,已经渺无踪影。四周墙下,惟有积沙,多少不等。”而他考察的建于明正德六年(一五二一)的红山堡,堡城之外,沟蚀纵横,以致入城的道路都横遭阻绝,显然是由于建城以后天然植被经过大规模开采,土壤的抗蚀力大为减小,沟蚀发生加速,最终形成深沟大堑。此情此景,不知当年那些赞咏“农夫秋成击壤歌”“农儿持券买耕牛”“樵牧满川耕遍野”的文臣武将们会做何感想?
在学术界,关于毛乌素沙地的主要成因,一直有究系气候波动还是人类活动所致的讨论。但是,自明代中叶五百年以来该区域并没有发生大的气候变更或地壳变动,那么,此后的土地荒漠化加剧,并非气候发展的顶级产物,而是人类活动的累积作用,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当时大规模屯垦以及清代愈发过度的滥垦、滥牧、滥樵、滥采。今日盐池,虽经几十年来大力防治,荒漠化土地依然占县域面积约百分之八十,依类型和面积大小分别为风蚀、水蚀和盐渍荒漠化。盐池东至榆林明代边墙沿线地区,大都面临着极为相似的严重生态问题,都普遍实施了禁牧以及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等措施。人们找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吗?答案将不会在短时间里揭晓。如果说,谶纬是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的神的启示,那么,五足牛的变异,何尝不是对草原垦殖后果的首次预警。往事越千年,假如刘向、京房之流再世,他们也许会这样说:足者止也,戒大举农耜也。但是,人们并不能参透玄机,觉悟这一谶语的奥义,直至天荒秽、地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