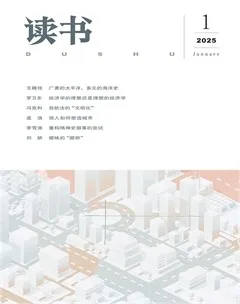义例:有无与违从
一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说:“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
例义又称义例。较早对义例的关注,是经学领域对《春秋》书法的探讨。书法即义例之法,亦即书不书、如何书的记事方法、原则和程式。晋人杜预《春秋释例》提出《左传》“称凡者五十”,认为它就是对《春秋》书法的归纳,所谓例是也;唐人孔颖达《左氏春秋正义序》提出“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例中寓含着嘉善黜恶、褒是贬非,所谓义是也。就是说,义乃所纪之事,即内容及体现的主旨;例乃纪事法度,即规则和条例。
义例又称凡例,今人著述亦有凡例,但多为条列式的直接表述,古人义例却多有不自相标,只在写作实践中随文体现者,非深入著述肌理不易发现,难于把握,这就是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所说的:“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所以古人历来重视推究义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一所谓“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是也。
有清至民国,学者特别重视古书义例的研究,名著有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余嘉锡《古书通例》等。又有不少学者仿其例而扩大到文本之外的层面,如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和《史讳举例》,丰富了义例之学的内涵。
推究义例是为了就例推义,推究义例才能更好地理解文义。文学批评史上有一桩著名的公案,钟嵘《诗品》将陶渊明列于中品,并称源出同列于中品的应璩。应璩文学地位远较陶氏为低,所以钟说颇为人所诟病,以致有人怀疑渊明本来列于上品,今在中品,是后人窜乱的结果。钱锺书则决然否定这种可能性,认为《诗品》论“某源出于某”虽多附会牵合,本身却自具义法,即诗人或源出同品,或源出上一品,绝无身居高品而源出下品者,故陶渊明不可能原列上品,并由此提出“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书之全”(《谈艺录》二四)就不足以论定古人的阐释学方法。不知其人之世,即不了解南朝文风与陶诗之不相契合;不究其书之全,就是指不掌握全书的义例。
汉晋以降,学术从“著述之文”渐向“文人之文”(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六《文集》)变化,文章义例之学随之兴盛。康乾时期的桐城文派代表人物方苞尤倡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又书货殖传后》),义法具而后文成。他评点《左传》《史记》而成《左传义法举要》与《史记评语》,虽取史书为对象,却多从属辞比事、叙事手法、章法安排等多角度揭示其义法,无异于文章学的探讨。
旧时金石类著述属于史部,金石例类却划归集部(《四库全书总目》即列在集部诗文评),由此可见古人对于碑志义例的重视,与重视文章作法密切相关。
碑志义例类最早的著述是元人潘昂霄所著《金石例》,随后就数到明人王行《墓铭举例》和清人黄宗羲的《金石要例》。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卢见曾(一六九0至一七六八)将三书汇为一编,以《金石三例》为名刊行于世。
二
碑铭鼎盛于东汉,墓志成熟于南北朝。后来碑志合为一语,有时浑称二物,有时单指其一。碑志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其本为实用性文体,从文章学角度看,内容结构模式化倾向严重,尤其墓志,语言的骈俪和僵化更为突出。至中唐韩愈,才以史传性叙事法作墓志,易骈为散,讲究文章作法,格遂大变。也正因如此,从上述最早的三书开始,对碑志义例的探讨,韩柳便成为重心。兹简述三书之大略如下。
(一)《金石例》十卷
元人潘昂霄著。昂霄生卒不详,字景梁,号苍崖,济南(今属山东)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金石例》以金石为名,却有石无金,此古人语汇浑言之一例。全书内容,同时人傅贵全序所述甚明:“一卷至五卷则述铭志之始,而于贵贱、品级、茔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之制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则述唐文括例,而于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葬、月日之笔削特详焉。九卷则先正格言,十卷则史院凡例制度。”共括碑志义例近二百条,其中韩愈碑志的括例过半。
清人郭麐《金石例补序》说:“金石之有例自潘景梁始。”《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明以来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无矩度,得是书以为依据,亦可谓尚有典型,愈于率意妄撰者多矣”,对此书开括例先河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作为第一部碑志义例专著,此书自有不足处。《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其“所载括例但举韩愈之文,未免举一而废百”,“以《金石例》为名,所述宜止于碑志,而泛及杂文之格与起居注之式,似乎不伦”。
(二)《墓铭举例》四卷
明人王行(一三三一至一三九三)著。王行字止仲,号半轩,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诗文书画皆擅,史称一代奇才。《明史·文苑传》有传。
《墓铭举例》同样重视韩愈碑志,又从韩愈一家扩至李翱、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朱熹等唐宋十五家碑志,抉发出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妻、子、葬日、葬地等十三类共二百三十余例。
与《金石例》相较,《墓铭举例》新创之处有二,一是既列正例,又重变例,即卷一题识所谓“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二是重由例论义,如卷一“柳子厚墓志铭”:“题不书官,其字重于官也。”卷二“泷冈阡表”:“右表其先君之墓道也,而题以地书,变例以致其尊也。”凡此之处皆可补《金石例》之不足。
卷二前著者有题识,谓“文自东汉之衰,更八代而愈下。至唐韩文公始振而起之,以复于古焉。韩文公既为之倡,同时和之者唯李文公(翱)、柳河东(宗元)而已。后二百年至宋之盛始,复得穆参军(修)、苏沧浪(舜卿)、欧阳公(修)、尹河南(洙)相与溯而继之,而欧公其杰然者,当时文风实为之变,从而和之者日以浸盛,而南丰曾氏(巩)、临川王氏(安石)、眉山苏氏(轼)出矣,南流以还,斯文之任则在考亭焉”云云,知其所取之十五家,虽是从墓铭一体出发,其意义实不限于墓铭一体,而是着眼于集部文之总体变迁,朱彝尊称“《墓铭举例》一书,足为学文者津筏”(《明诗综》卷十引《诗话》),洵非虚语。
此书取材虽广,亦只限于中唐以下,而未上溯南北朝。亦有人认为其未能区分定例、常例、特例。
(三)《金石要例》不分卷
清人黄宗羲(一六一0至一六九五)著。宗羲字太冲,号黎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学无不精,著述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思想家。《清史稿·儒林传》有传。
黄宗羲自述撰著此书的原因,是碑版之体至宋末元初而坏,“《金石例》大段以韩愈为例,却未能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领,稍为辩证,所以补苍崖之缺也”(《金石要例》题识)。
为例之义即义例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和事实,坏例之始即既有义例突破的始作俑者,这确实是《金石要例》所关注的两个重点。所以此书立例虽仅三十六条,却较前二书更为深刻,且所涉朝代更多,括例更重要,表述更清晰,更有助于研读前人所撰碑志。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九云:“自黃梨洲氏《金石要例》出后,文之义法,已括其凡,为碑版者,谨守不渝,即为定则。”又鲍振方《金石订例》卷一题识:“盖非苍崖无以识例之备,非梨洲无以知例之严。二者相救,不可偏废。”

此书考据偶有可议处,如《书合葬例》称未有书“暨配某氏”者,例坏于明人王慎中,不尽准确。
这三种最早的碑志义例著述作用很大,影响也很大,将其汇为一编的卢见曾论其意义云:“合三书而金石之例始赅。曩病时贤碑碣叙次失宜,烦简靡当,盖未尝于前人体制一为省录耳。兹故汇刻以行世,俾后之君子晓然于金石之文。”(《金石三例序》)
清中期以降,随着对金石碑志多重价值的进一步认识,金石学大盛,探讨义例的著述亦蓬勃而生。梁玉绳《志铭广例》、刘宝楠《汉石例》、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等,无不承袭其体例而成书。
三
到了乾隆年间,《金石三例》得到了一位重要文人的批注,这位文人就是王芑孙。
王芑孙(一七五五至一八一七),字念丰,号惕甫、沤波,长洲(今苏州)人,《清史列传》卷七二称其幼有异禀,年十二三即能操觚为文,多参与朝廷典礼文章之事,肆力于诗古文,为南北时望所推。
王芑孙素喜金石义例之学,撰有专著《碑版文广例》,又专力批注《金石三例》,清末冯焌光刊刻而印行之。其批注于原书或补或纠,或评或议,内容丰富,条目俱在,毋庸详述。
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是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一部《金石三例》,其中的《金石例》一书有王芑孙的朱蓝二色亲笔满批,卷十后跋云:“此书置案头二十余年,翻阅百过,偶有会心,随手点注。”可知其对《金石例》的关注之久和推重之深。
王芑孙批注《金石例》卷首有原收藏者武进人陶度自他本移录的两段王氏识语,其中“余阅是书二十余年”一段的署款时间为嘉庆十三年(一八0八),由此可知王芑孙置《金石例》于案头的起始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前。至于王芑孙对另二书即《墓铭举例》《金石要例》的批注(今唯见冯焌光刻本),想亦不出此二十年间。
在批注《金石三例》的过程中,王芑孙开始《碑版文广例》的撰著。上引陶度移其识语云:“异日门人中有为余稍加删替,并余今作《碑版广例》合刊行之,虽谓之《金石四例》可也。”似嘉庆十三年已经或接近完成。然据其《穀日自述二首》(《渊雅堂编年诗稿》卷十九“庚午”)之二“文总千家例”句下自注:“余方作《碑版广例》一书未了。”庚午即嘉庆十五年(一八一0),知其写作过程亦持续较久,无怪乎他对自己的著述以及批注如此自珍。
王芑孙的《金石三例》批注及其《碑版文广例》,除具体的评点和大量的补例,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中体现的碑志演变观、义例观等文章学思想,仅举两端。
一是论例虽重汉魏,更重唐宋。
清人朱彝尊《书王氏墓铭举例后》(《曝书亭集》卷五二)谓碑志盛于东汉,对《金石例》过重韩、欧等唐宋志例表示不满。王芑孙承其说,认为“汉魏六朝中自有简质可法者,即为韩柳所从来。《唐文粹》所载诸家亦尚有峣然自立于韩柳之外者,安得以八代之衰一语概从吐弃”(《墓铭举例》跋),故其上追秦汉,下迄元明,著《碑版文广例》以补其缺。其书括汉代碑碣之例七十八条,前所未有,对后世如《汉石例》等不无影响。
但是,他又认为汉碑版“或奥而赜,或枝以蔓,虽或得焉,其所得常不敌其所失”,“不皆出于文士,乖离析乱,人率其臆,固未尝有例也”(《碑版文广例》卷一题识),所以仍然将碑版的鼎盛期归于唐、宋,将文章正统归于韩、欧,认为即使从义例的角度看,也需要以韩、欧为立足点和出发点:
碑版莫盛于韩、欧,韩以前非无作者,凡其可法,韩、欧则既取而法之矣;其不可法,韩、欧亦既削而去之矣。韩以后非无作者,能以韩、欧之例例秦汉、例元明,无往不得矣;不以韩、欧之例例秦汉、例元明,无往不失矣。得失之数明,而后承学治古文者有所入。(《碑版文广例自叙》)
因此,其《碑版文广例》虽颇详于汉,而实更详于有唐一代,达九十条之多。
二是论文不重循例,而重极才尽致。
尤为难得的是,王芑孙非常重视义例,长期从事研究,对义例功能的认识却相当客观辩证。他在《金石要例》卷端眉批云:
文章者,称性而谈,扶义以立,乘气以行,极才而至,无例可言。专以例言,则成印板。
又于《金石例》卷六“韩文公铭志括例”天头批曰:
凡此等皆临文之变,随时而改,随人而异,无例可言。若一一以例言之,则转成担版。作者之心思才力,皆坐困其中,而无由自骋,即使一皆如例,亦所谓缚律僧也。绁虎囚龙,岂有与乎斯文也哉。
他甚至极端地说:
传家以例说《春秋》而《春秋》晦,文家以例求文章而文章隘。(《碑版文广例自叙》)
那么义例类著述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在《金石例》目录后的题识中这样表达:
学古文者始入当极才尽致为之,不必求例,子厚、老苏早年文字可按。言例则先有一物制之于笔先,而无以极其才矣。然才境既极而无驭之者,必将为七百里之连营,必将为八骏之游宴瑶池,而不知返,故授之文律焉。讲于例者熟,然后得诸心而应诸手者,不缪于施。
无例则文之能事必不至,有例则文之趣必不得,文之用必不鸿。始由无例以之有例,继由有例以之无例,此学之者之功夫节次也。
他还有一种说法更耐人寻味:
先儒宿学莫不龂龂于此,亦聊为无知妄作者正告之尔。
凡著书皆为知者道,唯此乃为不知者道也。(《金石要例》卷端眉批)
王芑孙殁二十余年后的道光辛丑年(一八四一),校写《碑版文广例》的江元文在跋中引其先大父之语曰:
自来作碑版文字,如高山出云,氤氲升中,随风变幻,无一而非云也,何例之有。然而昧者指烟痕水气以实之,则颠矣。惕甫先生之为《碑版文广例》也,亦犹为不知云者示之准也。
显然,“为不知云者示之准”,就出自王芑孙所说的“为不知者道”。由此亦可知,在后人眼中,王芑孙的著述就略等于佛陀所说的月之于指了:“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楞严经》卷二)
的确,碑版义例是随时而变的,何况还有正例、变例、坏例和非例造成的复杂性。仅举黄宗羲《金石要例》所括之例为例。对墓主的称呼,黄书《称呼例》谓耆旧则称府君,其实这是唐例,汉人碑版并不然(参王芑孙批注);黄书《书合葬例》谓妇人从夫,故合葬者志题只书某官某公墓志铭,未有书暨配某氏者,杭世骏却举出多个反例(梁玉绳:《志铭广例》卷一“题书妻合葬”引);黄书《书生卒年月日例》谓凡书生卒止书某年某月某日,不书某时,《志铭广例》卷二“生卒书时”却列举六朝至唐多例,以证黄氏之非。
总之,王芑孙提出“为古文者不可不知例,却又不得拘于例”(《墓铭举例》卷三“魏嘉州墓铭”批),稍后的郭麐也说:“泥于例,则官府吏胥之文移也;不知例,则乡农村学究之论说也。”(《金石例补序》)近一个世纪以来,南北朝以下墓志大量出土,更证明前贤所言非虚,足可为今日读、用义例书者之圭臬。
又岂止于碑版一体,文章写作中如何处理义与例的关系,如何看待为文之用心与文章之作法,高明者多持与王芑孙相同的看法。如同时期的大学者章学诚云:“古人文无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盖有所以为文者也。文而有格,学者不知所以为文,而竞趋于格,于是以格为当然之具,而真文丧矣。”正确的做法是:“文心无穷,文格有尽,以有尽之格,而运以无穷之心,亦曰得其所以为文者,而不以格为当然之具,强人相从。”(《章氏遗书》卷二九《文格举隅序》)
可知古代大家之文,正可于讲义例与不讲义例、有义例与无义例之间去寻其一端之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似论,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似策,韩愈“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李涂:《文章精义》),其《蓝田县丞厅壁记》更全然打破厅壁记的公文体式,彪炳厅壁记的史册。借用前引江元文祖父的话来说,讲义例是为不知云者示之准也,突破义例往往成为“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的至文。
四
王芑孙极为自珍的积年所批《金石三例》,生前却未得刊行。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四月,南海冯焌光从书贾处得之,“分朱蓝两笔,书法亦分数体,或行或楷,无不精妙可玩。其评识各条,尤阐发入微,持论严正”,遂谋刊行,公诸学林和艺林。次年六月竣工,而焌光已先二月病卒(参《金石例》冯焌光及其弟瑞光跋)。此本后为吴县朱记荣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收入《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00八年有影印本,颇便取览。
遗憾的是,今藏上海图书馆的《金石三例》王芑孙批注本,仅存王氏对《金石例》一书的批注,亦为朱蓝笔行书。据收藏者陶度癸丑(一九一三)九月《金石要例》后跋语,陶氏所得原仅此王批《金石例》一种,后寻得同板(卢见曾乾隆二十年初刻本)《墓铭举例》《金石要例》以足成《金石三例》一书。
将此王芑孙亲手批注《金石例》与上述冯焌光刊本相校,字句略有出入,全书又无冯氏笔迹或藏印,可知不是冯氏所得之本。书前陶度题记谓,除此本外又于厂肆见一朱笔过录本,又可知王芑孙多次移其所批于他本。又据卷首王思明叙后及书后王氏两段跋语,此本是王氏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居沈恕(号绮云)啸园时应沈嘱而过录之本。“异日门人中有借度者,此本在后,以此本为正”,则其不仅在王氏所批所录诸批注本中有特殊价值,王氏批注之亲笔手迹,天壤间恐怕也只有这一种存在了。
据扉页题记、书后跋文及所钤印章,上海图书馆所藏王芑孙批注《金石三例》本曾经徐渭仁(号紫珊)、沈树镛(郑斋)、耆龄(号思巽,斋名温雪)、周越然、袁克文(字抱存,又作豹丞、豹龛,号寒云)之手,后由袁克文让与陶度(字钵民)。
王芑孙不仅是清中期的名学者、大诗人,还是出色的书法家。其书“遍求诸家帖,一一与追程”(《臂痛自述四十韵》,《渊雅堂编年诗稿》卷十七“甲子”),尤于《灵飞经》、赵孟、《瘗鹤铭》、《醴泉铭》等用力为深。
并世书家中,王芑孙与年长三十余岁的刘墉(石庵)特相交好,刘墉曾盛称其书法,馈赠其书作。而其书则于诸家遍所取法外,多学刘墉。其诗有“我出公门得所从,世人谬谓书如公”(《山左吴季游太学》)语,笔者曾得观其行书真迹多种,喜用浓墨,运笔沉着,笔画丰腴,结体朴拙,确与刘墉大相仿佛。
但石庵体似亦仅为王芑孙书之一体,笔者另曾见其楷书,整饬端穆,如六朝写经一路。前述上海图书馆藏《金石三例》批注中的小行书,遒劲浑茫之外更兼流宕旖旎之美,观之如行山阴之道,颇使人生难以为怀之感。
王芑孙同乡后辈叶廷琯《鸥陂渔话·王惕甫夫妇合璧书卷》云:“我吴明季以来,书家用笔皆以清秀俊逸见长,至惕甫始以遒厚浑古矫之,遂为三百年所未有。”由此语可略窥王芑孙书得时人赏识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