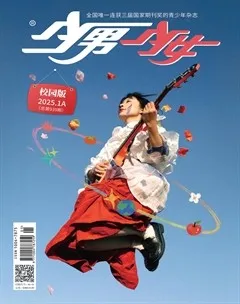斗草之趣
最近,我和妹妹重拾了儿时十分喜欢的一个小游戏—“斗酢浆草”。
酢浆草是一种十分常见却不起眼的小草。它由三片心形的小叶和一根粗壮的茎组成,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三叶草。它给了我和妹妹许多快乐。
“斗酢浆草”这个小游戏是从我外婆那一辈人流传下来的。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其稀缺,食物就更少了,所以当时人们经常会把酢浆草当作野菜吃掉。因为这种草有一种奇特的酸味,所以在客家话中被称作“铺菇酸”。客家话中的“麻的即酸呵哩”,就是用来形容它的酸的。
除了能吃,这种草还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玩具之一。因为这种草很有韧性,只要把它的肉质茎捏掉一小段,找到草中间的一根白线,把这条线拉出来,和茎完全分离,只留一点与叶子相连。再把多余的茎掐掉,放在空气中晃荡几下(作用大致相当于放飞纸飞机前的吹气),就可以拿去斗草了。
怎么斗法呢?两人分别将两根草的茎提住,轻轻一荡,让两根草的茎绕在一起,再分别朝自己这边拉。先把对方的草勒断的一方就是赢家,他的草就被称作“王将”。输的那个就只能屈尊当“乌龟”了。
斗草虽然看似简单,其实也很讲究方法。这不,我和妹妹各提一根草,绕在一起就开始斗了。一开始,我就迫不及待地出招了,先在对方的草上套一个活套,然后一拧,一拉。嘿,妹妹成功做“乌龟”了。
当我大呼胜利之时,妹妹不服气,找来一根更大更粗的草,向我发起挑战,我欣然应战。这次,妹妹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率先勒向我的草。我赶忙一绕,逃过一劫。紧接着,我又使出了一个“乌龙摆尾”,试图将妹妹手中的草勒断。可真还就应了“身大力不亏”这句话,妹妹的草茎比我的要粗,刚一接触,我的草茎就断成了两截。
不知什么原因,斗草用的草总是越斗越有韧性,越斗越有战绩。我几次换草,几次都被杀得连连败退,毫无还手之力。但我依旧兴致勃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找更大的草,期盼着再与妹妹一较高下,一决雌雄。
斗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游戏,却给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指导老师:牛筱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