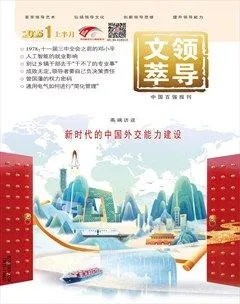被故乡开除的人
对于身败名裂的负面人物的默契排斥,体现了中国人朴素的爱憎观念。中国人重乡土,从故乡及其乡缘关系中获得社会支撑,希望故土能给自己增光添彩。谁都不愿意一个臭名昭著的人,败坏了故乡的名声。
古代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谁都不愿意和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相伴长眠在故土的地下。再想到子子孙孙都要蒙受这个宵小丑类的负面影响,人们难免同仇敌忾,干脆开除他的“乡籍”了。
“不主动、不谈论、不回应”
传统中国的乡土是和宗族密不可分的,故乡在古人的情感中几乎等同于家族。宗族和故乡融合一体,组成了古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背景。而宗法制度和族规中便有“除籍”(出族)的严惩,即将一个家族成员逐出家门。当某个成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数典忘祖、卖国求荣、作奸犯科等,通常会遭除籍。相关记载在传世的族谱中俯拾皆是,这种惩罚通常同时伴随杖责、鞭笞等体罚。
在古代,被除籍后,不仅意味着宗族不再承认他的血缘身份(有的家族还会收回姓氏),他再也得不到宗族和家人的任何支持,更严重的是,他在族谱上的记录一笔勾销,死后不能葬入家族墓地、不能标识世系传承,将成为一个孤魂野鬼。这在古代是一项釜底抽薪的终极惩罚,除籍之人成为无根无源之人。开除乡籍可以看作宗族除籍的外化与延伸。没有故乡的人无法获得地缘支持,同样意味着无法落叶归根。事实上,开除乡籍通常是宗族除籍的并行惩罚,二者是贯通的。逐出家门的败类,乡亲们也看不上,反之亦然。
我们以大奸臣秦桧的籍贯为例。《宋史》记载秦桧是“江宁人”,但南京从来没有认过秦桧这个乡人,江宁秦氏更是以之为耻。出身江宁秦氏的乾隆朝状元秦大士,在西湖岳庙看到秦桧夫妇跪像,羞愧难当,写下了“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同时,秦桧的籍贯像皮球一样被后世踢来踢去。
通行的说法是:秦桧出生在湖北黄州的舟上,年少时居住江苏常州,后迁居江宁。又有一说,认为秦桧是其父任职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知县时所生。同样,黄州、常州、永福三地都对此讳莫如深。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后世眼中的“坏人”,严嵩却得到了故乡的维护。乡邻不仅为他修建祠堂,还自发地不让类似京剧《打严嵩》这样的戏曲在县境内上演。原因大概就是严嵩在故乡颇有善名,至今仍留有遗迹的分宜县万年桥,就是严嵩顾念乡邻安危而出资修建的。这也反映出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不能以好坏一概而论。
被“踢皮球”的阮大铖
对于绝大部分负面历史人物,各地普遍奉行不主动、不谈论、不回应的“三不原则”。不过,历史上也发生过两个地方将“坏蛋”踢皮球踢出公案的案例,最著名的便是“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阮大铖。
阮大铖是明清鼎革时期的人物,他以文学传世,是明朝首屈一指的诗人、剧作家,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但在不少人眼里,他的品德似乎匹配不上如此才气。
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形势下,阮大铖起初列籍东林,以清名立世;仕途受阻后,依附魏忠贤,出任光禄卿。魏忠贤败,阮大铖隐居南京,力求复出,遭到东林党、复社诸人的狙击。明亡后,阮大铖拥戴福王在南京继位,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掌权后,他这个兵部尚书党同伐异,对东林党和复社罗织罪名,打击报复。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灭福王政权。阮大铖率先剃发降清,成了“四姓家奴”。
降清后,阮大铖积极充当向导,追随清军攻占南方各地。他随清兵入闽,途中头面肿胀,清军贝勒劝他留下养病,阮大铖的反应却颇值得玩味。钱澄之《藏山阁文存》记载,面对他人的劝说,阮大铖反驳称:“我何病!我虽年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他执意表现,还在翻山越岭时“独下马徒步而前”,显示自己筋力“百倍于汝后生”。最后,当清军找到阮大铖时,他已经死了。
鉴于时值盛夏,清军担心尸体溃烂,便草草收殓。“铁铮铮汉子”阮大铖最终不知埋在何处。乾隆朝筛别国初归降的明代士人,将洪承畴等为清朝定鼎天下的降臣归入《明史·贰臣传》,以彰恶扬善。可在乾隆君臣眼里,阮大铖连当“贰臣”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归入《奸臣传》,令人唏嘘。
修史立传,写明籍贯是惯例。明代桐城县的科名录里,万历乙卯科举人、万历丙辰科进士中,都有阮大铖,阮大铖是安徽桐城县人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明史》把阮大铖写为安徽怀宁人。
时任《明史》总裁是出身桐城张氏的张廷玉。他把持了明朝正史的修撰大权,估计是不屑于与阮大铖同乡,把后者的籍贯记成了怀宁。考虑到张廷玉位高权重,怀宁人有万般不愿,也暂且忍气吞声了。不过,怀宁县人文荟萃,士大夫势力强盛,对于阮大铖这个从天而降的“同乡”怨气深重,始终谋划将他“请走”。
民国初期,怀宁县借编修县志的机会,特意考证阮大铖并非怀宁籍,指出《明史》记载有误。《怀宁县志·山川》在介绍境内名胜百子山时,借物言史:“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遗憾的是,礼部的题名碑和府学前的进士坊都已经没有实物可以佐证了,桐城县秉承“三不原则”,不做任何回应。怀宁百姓抗议声高涨,但桐城县风平浪静,历次编修《桐城县志》压根就不提阮大铖半个字。
“平楚”之叹
如今,我们审视中国历史上对败类、恶人的除籍现象,依然可以汲取精神养分。这项惩罚对坏人的实质作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小了,但是它始终犹如一把高悬的利剑,警醒所有人在面对诱惑、遭遇艰难的时候要谨慎抉择。
北宋宰相张邦昌在靖康之耻前后,对女真人卑躬屈膝,并出任侵略者扶持的“大楚”政权傀儡皇帝。他是河北沧州东光县大龙湾村考出去的进士宰相,原本是一个励志故事兼宣传典型,可是东光县对这个“大楚皇帝”只字不提。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大龙湾村划入了衡水阜城县。后者更是对此不屑一顾。张邦昌变成了典型的没有故乡的人。
南宋建立后,张邦昌罢官,贬谪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建炎元年(1127)九月,朝廷“赐死”张邦昌。他的最后时光,据《大金国志》记载是这样的:当张邦昌抵达贬所,寓居在潭州天宁寺。寺内有一座平楚楼,取自唐代书法家沈传师“目伤平楚虞帝魂”之句。当得到朝廷的赐死诏,张邦昌一开始徘徊退避,直到“忽睹‘平楚’二字,长叹就缢”。
平楚楼上秋高气爽,张邦昌满怀生的眷恋,急寻逃生之路,楼下是催他速速自尽的差官,随时要拉他进入黑暗的永夜。不知道彼时的张邦昌有没有悔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不知道彼时的张邦昌有没有意识到,除了现实的“赐死”,在之后的一千年光阴中,生他养他的故乡会抹去他的一切痕迹,仿佛他这个人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