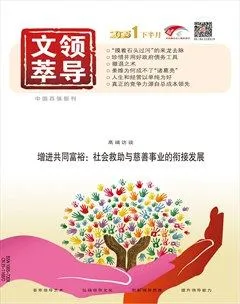船上的费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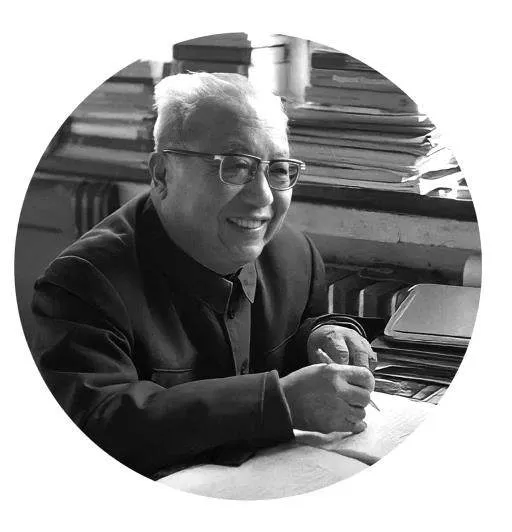
费孝通说过,他一生学术工作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可以说,他的田野调查是从船上开始的。在《桂行通讯·过柳州》一文末尾,他留下“十月十二日于赴象县之新广船中”的记录。
从此开始,在费孝通的学术经历中,船既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工具,也有了超越于器物层面的象征意义。他编写瑶山调查报告时,曾把整个国家运转比作大船航行,表达改良主张。费孝通说:“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所以,“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暮年里,他确认自己“一直是在中国现代化这条大船上做事情”。
一
瑶山调查中,一次意外事故使费孝通身负重伤。他接受姐姐的建议和安排,回家乡养伤,一九三六年夏住进开弦弓村。
村里的小型缫丝厂引发他的调查兴趣。当年费孝通有抽烟的习惯。他去村里商店买烟,店主只一支一支零售,不卖整包的。想买整包烟,需找村里的航船去镇上。
费孝通的眼光转向航船。他跟着航船到镇上,主要不是为买烟,是要观察村镇之间的商业流通渠道,看出船家在水乡经济网络中的作用。他实地见证,“镇旁的河面上停泊着二三百条船,镇周围的农副产品都集中在那儿”。
在当年交通条件下,费孝通从航船往返观察村庄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汇聚航船的镇上留意“乡脚”在乡村社会组织里的功能。
为了更切近、细微地观察,费孝通曾参与航船上的劳作。他帮助船家扎结准备出售的生丝,现场观看一艘航船、一套制度怎样连接交易双方,沟通生产消费,在一方水土中发挥着神奇的组织功能。其神奇,让费孝通禁不住“连叫三声”。
他说,这套“航船制度影响于太湖流域的区位组织极大,在震泽这一带地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航船直接到震泽来做买卖。开弦弓虽是一乡的主村,但是在经济上不能作一乡中各村的中心,连本村都不能造成一个市场”,便是这套制度的效用所致。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费孝通告别家乡,到上海搭乘外轮,去英国留学。他说:“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
费孝通把开弦弓的航船制度写了进去。两年后,《江村经济》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引起国际学界轰动。他完成论文答辩后回国,还是走水路。他买了价格最低的统舱票,这样可在途中和社会底层的人们接触、交谈、交朋友,顺便做调查,还节省费用。
统舱里的温州青田人告诉费孝通,他们漂泊海外,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挣下血汗钱,要带回家乡,盖一所房子,修一座坟。这两件事办妥,就算落叶归根功德圆满了。同胞背井离乡,历遍艰辛,终得告老还乡。统舱里穷苦同胞的语言、神情、心事,费孝通一直记忆到老,在晚年里的数次温州实地调查过程中,不时提起。
二
费孝通当年学成回国,乘坐的是法国轮船。停泊西贡港口时,接连听到国内广州、汉口沦陷的消息。情势危急,路阻且险,他不得不舍舟登陆,取道越南,进入抗战后方,到了云南昆明。他执教于云南大学,并在西南联大兼课。
一九四三年初,费孝通和他的恩师潘光旦先生等知名教授同往大理讲学,顺道游苍山洱海。师徒二人同坐船舱,费孝通写下“洱海船底的黄昏”,文笔动人。
“惹人”者,有岸上美景,更有恩师情趣。费孝通记录船上另一时刻说:“饭饱茶足,朋友们还没有下船,满天星斗,没有月。虽未喝酒,却多少已有了一些醉意。潘公抽烟言志,说他平生没有其他抱负,只想买一艘船,带着他所爱的书(无非是蔼理斯之辈的著作)放游太湖,随到随宿,逢景玩景。船里可以容得下两三便榻,有友人来便在湖心月下,作终宵谈。”
费孝通听着老师的梦想,觉得自己太俗,似乎没有想过归隐之道。不过,他心里也念叨着龚自珍的一句词:“笛声叫破五湖秋,整我图书三万轴,同上兰舟。”
三
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费孝通实现了重访江村的愿望。他和姐姐费达生一起坐着船进村。那一刻的情景十分动人,费孝通说: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情感如此让费孝通感动,也使他警觉,担心浓厚的乡情会影响他观察、调查的客观眼光。后来写出的《重访江村》一文,从容说理,言之有据,证明他的科学精神经得起严格检验。在那个年份,文中对当时的农业政策提出温和的商榷,须见识,也须担当。
一九八一年十月初,初得“改正”的费孝通三访江村。
这次访问,距费孝通初访江村相隔四十多年,整个中国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到处生机勃发,江村也一样。他说,这次调查数据,使自己掌握了“近五十年的比较资料”。这段时间里,这个村庄的经历,和中国其他农村的经历大致相同,它可以“作为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旬,费孝通在马鞍山看过李白墓后回家乡,从南京到苏州,走沪宁高速公路。两侧景物飞逝,他想起李白名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次日,费孝通对助手说:“山是什么?重重阻力和障碍嘛。除了万重山,还有两岸猿声,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所以我说‘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毁誉就是两岸猿声。……看着路两边的景色,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就出来了这样的感受,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过,我的山还有最后一重。”
说这话时,费孝通将满八十七周岁。回首过往,一生很不容易,瞻念前程,余年可数。“猿声嘛,让它‘啼不住’好了,不管它了”,眼前正做的事,还是要用心。一位学界朋友曾问他:“费孝通”这篇文章,您打算怎么结束?
接下来,一番宏论脱口而出。费孝通说:“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经济地理上看,是跨国经济时代。要联络五大洲,有三十万吨以上的大船,就可以解决问题。政治上的交道,就不是三十万吨船的问题了。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可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刚刚开头,整个中国经济刚刚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历程。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是个沉重的大船。从开弦弓的航船,到国际网络经济,几千年在里边呢。现在把中国估计得太了不起,是危险的。自我估计过头,要出毛病的。这个局面下,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做,怎么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我想,‘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把这里边的道理说明白,启发更多的人,“把这一代人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这是费孝通在中国现代化这条大船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他说:“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