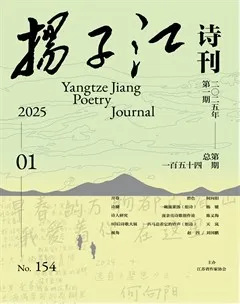父亲和酒(组诗)
2025-01-14 00:00:00夭夭
扬子江 2025年1期
凌晨四点的雪
早安。我走在雪地里,
雪还在昏茫茫地落。
挂在路边的中国结透出隐约的红,
又老又绿的植物啊,
街灯啊,
我记得他们没有头绪的样子。
每一朵都是执念,
落在虔诚之上,
也落在白首不相离的一瞬间。
长路冷清。
我站着,在雪的身旁,
唯有扑簌簌地落泪,
我站着,朝曾经跪着的自己
投下深深的一瞥。
雪啊,
就要盖住我小心翼翼的足迹。
暴雨中的少年
仿佛自己也成了一阵暴雨,
落在海棠的头上,
也落在无名的墓碑上。
丢下还未成形的枷锁,
他奔跑,他攥着闪电,
他的辩词里还没长出茂盛的枝丫,
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去哪儿?他也是一个未知的深渊啊,
用密集的雨水冲刷这个年代,
看啊,街灯就要亮起,
他成了最先的那束光,
雨落在光的头上,
落在羞于表达和野蛮生长的那一刻。
四野无人
直到有人漏出深藏的慌张,
空无的另一头,
替身们在寻找那一阵恍惚。
置身其中,把万物困住,
为他们洗净身子,
迎接冥冥之中那些模糊的片段。
曲终人散时,会有人来推开这虚无之门,
用逃荒者的故乡,
用一座寺院的肃穆,
来填补这四野无人的荒凉。
父亲和酒
父亲老了。无可避免的,
每一盅酒也跟着老了。
他无法控制,就像无法控制
我们一天天长大,并慢慢远离。
无数次,我在他破旧的解放鞋
沾着的新泥里寻找自己,
槐花开时,我们会把重男轻女的
日子放一放,
去弯下腰身的事物里缝补伤口。
干杯啊,我瘦弱的老父亲,
干杯,交不起五元学费的老父亲,
父亲,我恨你的酒,
它从未告诉我,要怎样才能走到
春天身旁,陪他默默流泪。
路过一座寺院
大门紧闭,有花枝伸出院外,
肃穆间,深径发出久别重逢的呜呜声。
来去匆匆,
万物滚烫,悬在不为人知的对视里。
皆是错过,皆是词不达意的存在,
皆是漏洞百出的身躯横在隐喻里。
安静,是一种残忍的抽丝剥茧,
千万双看不见的手在虚无中摸索。
猜你喜欢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2年4期)2022-04-08 21:24:29
新少年(2021年3期)2021-03-28 02:30:27
青年歌声(2021年1期)2021-01-30 09:53:30
文学少年(绘本版)(2019年1期)2019-03-20 12:32:38
东坡赤壁诗词(2018年1期)2018-03-31 09:10:10
领导文萃(2017年22期)2017-11-27 08:21:43
福建文学(2015年2期)2015-03-02 01:18:38
大灰狼(2014年3期)2014-04-16 13:44:44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2009年7期)2009-09-04 08:37:56
新校园·阅读(2009年4期)2009-05-07 09: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