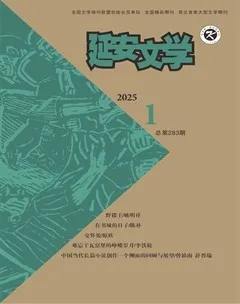川江民间本草
陶灵,重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天津文学》《延安文学》等。出版散文集《川江广记》《川江博物》等。
百 草
百草不是一种植物,是多种草本植物的合称。
唐代中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说(译成白话):“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采一百种草,阴干后烧成灰,和石灰做成球团,先烧红,晾冷之后碾压或捣磨成粉末,涂抹刀箭等金属器械所致的伤口止血,被狗咬的伤口也可涂抹。”
川江民间也有“端午百草皆入药”的说法,一定要清晨去采,过了中午,药性减半。但老百姓心中“百草”的概念,并不一定严格以一百种草为限,或许没有这么多,也有可能超过,甚至不只认定五月初五这一天。
重庆城里的吴融大姐在巫山县城江对岸当知青,1969年冬的一天,下雪了,不用上坡做活路,她和两个知青去队长家烤火。她走在最后,突然被不声不响的大黄狗猛咬一口,小腿上的伤口立刻流出血来。队长的佑客(妻子)吓坏了,马上搬出一块大菜板,用刀在上面一阵乱刨,刨起一层黑黢黢的老污垢,看上去黏糊糊的,然后用食指刮起来,直接敷在吴大姐的伤口上。她边敷边解释说,百草都是药,菜板切的菜菜草草多,自带药性,我们身上整起了口口,都是这样医的。那时候农村人的菜板除了切人吃的蔬菜外,又宰剁坡上扯回来的鲜猪草,一年到头不知要经历多少种菜、草。
吴大姐很幽默,说,大黄狗吃了屎的嘴巴又来咬她,想起都恶心。好在过了几天伤口就不痛了,“狂犬病”也没有来,到现在还活着。
古代中医药书上又有一种叫“百草霜”的中药,和“百草”类似。过去老百姓做饭烧稻草、麦秸和各种杂草以及木柴、树枝,往往于灶门边、锅底和烟囱内结成一层黑霜,川江人喊“锅烟墨”。《本草纲目》将百草霜归入“土部”,不算草类药。平时可收集一些百草霜,用箩筛筛一遍,除去杂质,拿玻璃瓶装好备用。如果从铁锅底刮下百草霜,都烧结成了块状,先要捣碎,再用箩筛筛出细粉。捣碎时最好用石舂钵,免得到处弄得黑黝黝的,不好擦洗干净。
百草霜用途多,主治多种出血:不小心,手被刀或利器划破,撒点在伤口上止血;流鼻血不止,从玻璃瓶里舀一小勺,摊在纸上,吹入鼻孔,血立止;牙齿缝出血,涂搽少许百草霜,有效;因肠胃湿热,大便中的血带片块状,米汤调匀五钱百草霜,放在室外露一夜,第二天早晨空腹服下。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最好去看医生,因普通人弄不懂是不是因肠胃湿热而出血。百草霜也可外用:调猪油涂搽头上的白秃疮。
最早的中医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玉石部》中还介绍了一种“冬灰”,差不多与百草霜相似,我们喊“草木灰”,即冬天炉灶中所烧各种柴草的灰。
川江有童谣唱道:“重阳不推粑,老虎要咬妈。”重阳节到来前两三天,外婆用灶孔里的草木灰泡了水,澄清后,滗出来,泡上几斤大米和苞谷籽。草木灰水每天更换一次。重阳节早晨捞起大米和苞谷籽,清水淘洗干净后,用石磨推成面浆,然后蒸出各种花样儿的重阳糕:菊花糕、红糖甜糕、节节花糕等。外婆不全用大米,专门混了苞谷籽,每只糕黄灿灿的,看着就想吃。但想到灶孔里黑乎乎的草木灰,我又忍不住问,干净吗?外婆说:“草木灰水泡了,蒸的粑粑又泡又软,才好吃。”
我长大了才明白,草木灰含碱性,有发酵的作用。后来,我在渝东南看见苗家人做好豆腐肉丸,先放进火铺的草木灰里,过一会再取出来,洗干净,在肉汤里越煮越嫩,鲜美可口。我很好奇,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主人也不知,说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方法。
小时候,有一次回乡下老家过年,见二婶从灶孔里撮出草木灰泡水,洗一家大小的衣服。它的碱性有去污的功效,过去物资紧缺又少钱,难买到肥皂和洗衣粉,这不失为一个好用途。
香 油
川江人吃火锅都要配味碟,也就是蘸料。火锅本身极具麻辣鲜香咸的大味,岂不是多余了?其实这蘸料只有香油和大蒜泥。香油又名芝麻油、麻油,用芝麻榨取而来,香味浓郁,川江人就取了个这么形象的名字。大蒜捣碎而茸,即泥,曰大蒜泥。
香油性凉,在大麻大辣的火锅汤料中烫煮的菜品,入口之前,先放蘸料里冷却一下,可降火去燥,也让干滋滋的辣味变得柔润一些。而蒜泥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能减轻麻辣食材对肠胃的刺激。现在新派火锅的吃法,倒是要在蘸料里加入芫荽、葱花、小米辣、芝麻酱、香辣酱、蚝油等多种调料和佐料,我是不认同的。火锅底料用各种香料与调料专门熬制而成,蘸料里只放香油和蒜泥足矣,最多再加点醋,可开胃,并中和辣味。
也有人吃火锅的蘸料里不放香油,用大众化的菜籽油,效果一样,口感也差不多。这是遵循老习惯,因为过去香油比较珍贵,大家舍不得用。榨取香油的芝麻产量低,栽种的人说“毛多肉少”,特别是吃不饱饭的日子,都不愿种植。俗话也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虽然并没有否定芝麻本身,却是拿芝麻小说事。
北宋中药学家唐慎微告诉我们:民间传说,夫妇两人一同栽种芝麻,生长才茂盛。早在唐代,女诗人葛鸦儿就有诗句是这样写的:“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不见归。”李时珍老先生解释:“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葛鸦儿诗句意思是,已到了春耕时节,该播种芝麻了,然而丈夫在外,谁来和我一起播种呢?按说现在已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丈夫为什么还不见回来?此诗叙述的是一对离散夫妇的辛酸故事,但从中可知民间确有芝麻需夫妇一同栽种的说法。
香油还是凉拌菜的灵魂。以前逢年过节,或家里有远到的客人,姑妈才偶尔做一次凉拌菜吃,也舍不得放香油。她用筷子在瓶里蘸一下,滴几滴在菜碗里,那香味至今都没散去……
我们县城有家出名的小食摊名“鬼包面”,说是民国时候就有了,傍晚出摊,下半夜收摊。川江人喊“馄饨”为包面。传说有一次,摊主照例在白天清点夜间收取的包面钱,突然发现里面有一撮纸灰,连续几天如此。一道士说,是夜间有鬼来吃了包面,给的是烧成灰的冥币,白天才现形。那时候老百姓用铜小钱,摊主便暗中舀了一碗水,每次收了包面钱都投入水碗中。如果遇到有钱浮在水面上,就把道士画的“符纸灰”悄悄撒进包面碗里,鬼吃后会被降住,不再去害人。鬼也算是一种神,大概早已料到摊主的用意,从此再没来吃过包面了。这事传开后,包面摊不但没人忌讳,反而越开越红火,久而久之,大家赠送了“鬼包面”这个摊名。我小时候看到的“鬼包面”摊不知是第几代了,开在两幢房子间的巷道里,上学放学路过时爱“望嘴”。见摊主给包面碗里滴香油,连筷子都嫌粗了,瓶里插着一根竹签,差不多现在烧烤串用的签子一样粗细,用时提起来,往碗里滴一两滴即可。名小吃摊不担心影响其声誉,如此节省,看来以前香油确实珍贵。
1976年,重庆知青王月强回城,安排在川江治滩队的拖轮上当水手,当年冬天在巫山下马滩施工。遇到休息天,大家一起到城里玩耍,王月强趁机去赶场。他发现芝麻卖得很便宜,两角钱一斤,想磨点香油带回家里。于是,约上几个船员,合起来买了十多斤,找到工地附近一户农家,借地方加工。
先把芝麻倒进锅里翻炒,炒干水分,飘出香味后,芝麻酥脆了。十多斤芝麻一锅炒不开,分两三次炒。灶屋这边锅里继续炒着,那边屋檐下的石磨慢悠悠转动,开始磨芝麻面。磨好的芝麻面装在一只木盆里,烧好滚烫的开水,拿瓢舀进去,淹过芝麻面大约二十公分。木盆底下垫放一根圆木棒,双手抓住盆沿使劲摇晃,一直不停。不一会儿,水面慢慢漂浮起一层油,用小勺轻轻舀起来,另外拿盆装着。舀完浮油后,再不停地摇晃木盆,又舀起浮油。木盆里的水凉了,滗出去,另加开水摇晃……反复这样,直到木盆里再也没油漂浮起来。舀在盆里的油含水,水在下,油在上,滗出油,倒掉水,也反复几次。直到凌晨两点钟,王月强和船员们终于得到一盆香喷喷、原汁原味的香油。这种取油技巧叫“水代法”,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香油制作方法。
取香油剩下的芝麻渣和滗出的水,留给借地方的这户农家,可分几次混合猪草煮了喂猪。那年月,人肚子里都没几滴油水,猪能吃到这么好的饲料,肯定长膘快。主人非常高兴,爽快地煮了块腊肉,招呼王月强他们打了一顿“牙祭”。
王月强分到两瓶香油,带回家时,父亲像得了件宝贝,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舍不得吃,两年都没吃完,打开瓶盖,仍是当初那么香,一点没变质。
老鹰茶
川江流域夏季较长,空气湿度又大,闷热难受。小时候,我见许多人家一大早烧好“老鹰茶”,用缸钵或瓦盆装起,旁边放一只小土碗。口渴了,舀起一碗,咕噜噜灌一肚子,再听到一阵“咯儿——咯儿——”的嗝声,爽极了。
老鹰茶也称“老荫茶”,适合牛饮,过去是老百姓夏天的必备饮料。民国《万县乡土志》中记载老鹰茶:“叶粗大,色红而性寒,盛夏饮之,祛暑……”虽名为茶,但本不是茶,属樟科,用其中的豹皮樟树的嫩枝、嫩叶制成,为一种代用茶。为何不称豹皮樟茶或豹皮茶,而叫老鹰茶呢?说是豹皮樟树只生长在崇山峻岭,像老鹰那样凶猛厉害的飞禽才能上去;它的芽叶清凉解毒,老鹰等飞禽啄食可解毒。
我不评判这得名之说的对与错,但认为也许叫“老荫茶”更适合些。川江流域南川、城口、巫溪、开县、云阳等老鹰茶出产地,山间有许多的老豹皮樟树,枝繁叶茂,一棵就能成荫。黔江濯水镇甚至有一棵五百年的豹皮樟树,高约二十米,树冠近一百平方米,叫“老荫茶树”再恰当不过了。
重庆歌乐山三百梯上面出产一种“酒罐萝卜”,形状上大下小像土陶酒罐而得名。这萝卜好,皮薄不生布,入口化渣。农村生产队集体生产时期,有胆子大的社员用粪桶挑到山脚下悄悄卖。回去时,不“打空手”,到队上包的单位公厕带一挑粪,可计工分。三百梯是一条梯路相连的陡坡,挑一担百多斤重的粪,大冬天都累得汗流浃背,头上直冒热气。夏天更是受不了,喉咙干得要冒烟。上了坡顶,有一棵大黄葛树,挑粪社员都要歇一脚。夏天,树下有个老鹰茶摊,一分钱一碗,痛快灌下。喝第一口时,有股樟香味,冲鼻,脑壳顿觉清醒。几口下肚,嘴里回甜,全身轻松、舒坦,力气又回来了。
我们巷子的余酒罐在河坝盐仓库㧯盐包,下车、上船,活路狠,累了回家,都要喝一杯酒解乏。有天中午,他肚子有点气胀,喝了杯酒不想吃饭,倒头午睡。醒来时,三点钟了,感觉肚子饿。揭开桌子上的甑盖一看,只剩一碗冷干饭和半碗夹生红萝卜丁。又见桌上瓦盆里的老鹰茶是热的,估计佑客重烧水泡过。他舀了一碗,倒在冷饭里,就着萝卜丁吃起来。冷饭因热老鹰茶而回温,口感正好,萝卜丁在菜坛子里泡过一夜,加蒜苗用油炒过,油而不腻,香脆爽口,呼呼几下刨完。余酒罐心想:“老话说‘好看不如素打扮,好吃不过茶泡饭’,看来真是这样子的。”然后,十分满足地抓过木椅靠背上的汗帕,往肩上一搭,又出门做活路了。
过去,国营厂矿时兴给工人发放“劳保三件套”:肥皂、棉线手套和老鹰茶。前两样一年半载才发一次,夏天入伏后,老鹰茶天天供应,由后勤人员直接送到车间。云安盐厂的工人称这为“清凉茶”,里面还放有十滴水,袪暑、健胃。熬盐工下午五点交接班,三点多钟后,很多细娃儿拿着碗、钵去车间端回来喝,是他们老汉儿省下的老鹰茶。国营厂矿在采购劳保老鹰茶时,往往量很大,存放久了,会生一种黑色的专门吃老鹰茶的虫子,叫茶虫,死后与老鹰茶混为一体。茶虫的粪便干燥后色泽棕黑,形似蚕沙,但比蚕沙小,称茶沙。老一辈的人说,茶虫、茶沙都是好东西,仍可与老鹰茶一起熬煮后当饮料,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消肿。用混合了茶虫、茶沙的老鹰茶给细娃儿做枕头睡觉,头颈不长火疖子;夏天时,拿茶虫、茶沙熬水,给细娃儿洗澡后身上又不生痱子。以前缺少药品,有草药医生专门收购老鹰茶茶沙,熬水,放冷了后冲洗患者眼睛,可治因发炎引起的眼睛红肿、流泪、疼痛等症状,几次就好。大多数人不认识,也不知道茶沙,草药医生说成是灵丹妙药,趁机卖高价。《本草纲目》中称茶虫为“茶蛀虫”,李时珍说“取其屎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县城少有啤酒卖,开初大家也不习惯喝。二贤祠巷有家“六毛火锅”,每天用非常大的锑锅熬一锅老鹰茶,供食客尽情饮用。那茶汁色泽深红透亮,我戏称“红糖水”,每次吃火锅要喝几碗,边吃菜边喝。如果不喝,第二天肚子肯定不舒服,一上午会跑几趟厕所。究其原因,老鹰茶可释躁平矜,祛火除湿。清道光《城口厅志》说(译成白话):“老鹰茶并不清香,比茶逊色很多。但晒酱时,掺入熬煮后的老鹰茶,酱不变味。”这就是品质。
在川江一带城镇的餐馆吃饭,顾客等菜上桌时,服务员一般都给每人倒一杯老鹰茶,边喝边等。老鹰茶口味大众化,人人可喝;餐馆老板也划算,抓一把老鹰茶可烧一大锅,只值一两角钱。十多年前,一种“苦荞茶”出现后,大多数餐馆改用苦荞茶招待顾客了。这种茶也不错,清热、通便、降压降脂。但很多人喝惯了老鹰茶,不愿改口。文友小芳说:“有一次,几个闺蜜约起吃饭,有两家餐厅可选,菜品味道都差不多,我就选了有老鹰茶喝的那家。”她特别告诉我,喝着老鹰茶吃菜,一点不觉得油腻。
老鹰茶在初夏长出新枝叶后,过去都是由农民随意采摘回来,除了嫩叶,和着嫩枝也采下,需剪断成小节。小时候,我看到母亲买回来的老鹰茶,都是整片叶子和许多短截细枝混在一起的。农民把嫩枝叶背回家,要用开水稍煮杀青,不然枝叶中含的樟香味太冲鼻,接受不了。快速从开水中捞起枝叶,摊在篾巴折上,半阴半阳中晾干。赶场时,背到市场去卖。晾干的老鹰茶是泡货,不压秤,一大口袋才卖几块钱。老鹰茶粗枝大叶,喝的时候,最好抓一把在锅里熬煮十来分钟,才出味。如果不愿花那工夫,也必须用滚开的水泡。
近几年来,人们对老鹰茶研究发现,其有保肝、降糖脂、抗炎的作用。于是,川江一带出产老鹰茶的地方,建起多家专业生产厂,硬是用生产茶叶的工序、手艺,精制老鹰茶,甚至还像做红茶一样进行发酵。这样制作出的老鹰茶模样与口感跟茶叶一样了,却再也喝不出特有的樟香冲鼻味儿,失去了本真的东西,已经不是我曾经喜欢的那个老鹰茶了。
何首乌
没读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前,我就知道何首乌了。
父亲当指导员的百杂业总店有两家中药铺,其中一家在老城大东门旁。里面总是散发出难闻的怪味,但又总诱惑我,迈着一双小腿跨进去。每次,正抓药的赵伯伯看到我,赶忙放下手中的戥秤,在药抽屉里摸出两颗干瘪的大枣,递给我,重复着一句话:“只剩两颗了,再要没得了哟!”小时候少零食吃,嘴又总是好吃。
民国时,赵伯伯就在这家药铺抓药。他说那时帮资本家,现在为人民服务。他没结过婚,过继了弟弟的女儿将来给他养老送终,当时已长大成人,在农村小学教书。赵伯伯平时一个人懒得做饭,吃单位伙食团,但经常端着小锑锅,在伙食团大灶旁的耳灶上炖东西吃,然后掏出止咳糖浆小玻璃瓶,里面装的老白干,喝上几口。有一次,他又端着小锑锅从我家门口过路,母亲逗趣问:“赵昌文,炖的么子好吃的?”
“何首乌。”赵伯伯神气地回答。
“这个是药,不好吃。”母亲摇摇头说。
他放下小锑锅,低头伸过来,把头发往后摸摸:“你看,我有根白头发没得?”五十多岁的赵伯伯,头上确实看不见一根白发,“何首乌是黑头发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中药何首乌。
学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课堂上,同桌陈志坚找我说“小话”:“我就挖过何首乌的。”这时老师瞪了我们一眼,不敢继续说。下课后,陈志坚又告诉我,挖的何首乌切成片晒干,卖给供销社收购门市,钱存起交学杂费,他妈和老汉儿才让他读的初中。不然回家给生产队放牛、割草。
陈志坚陆续摆他挖何首乌的经历:“不好挖,何首乌都长得深,在老土里面,土硬。但是供销社收购价贵。我听大人说,长在乱石坎子里的最多。挖到何首乌后,还要把坎子垒好,耽搁时间。我每天必须要打一背篓猪草回去,顺便把何首乌叶子也背回家,猪牛都肯吃,生得细嫩。挖的何首乌都小,还没得红苕一半大。听大人说,它长得很慢,石头坎子里的大些。”
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好耍,甚至羨慕陈志坚的经历。我是城里的娃儿,父母又是双职工,“少年不识愁滋味”,体会不到其中的艰辛。
何首乌本是人名,唐代时一个叫“何首乌”的人对此发现、采服有功,便以其命名。民间传说,五十年的何首乌有拳头大,服上一年时间,头发乌黑;一百五十年的何首乌大如盆,服一年后,老掉的牙齿能重新长出来;三百年之何首乌大小像箩筐,服上一年可增寿延龄,久服,成为生活在地上的神仙。民间对何首乌一直附会了神秘的色彩。
前几年,我在一乡场地摊上,看到有人卖何首乌,其中两只有拳头大,长得极像人形。何首乌与人参不同,像人形说的不是人身子,指人头。卖的人喊价五百元一只,他没跟着鲁迅先生说“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不然自己早在天上了,不会在这儿卖何首乌。他的说辞是,在“龙洞”旁边石缝里挖的,药性最好,吃了最“补人”。龙洞即喀斯特地质的溶洞,补人是滋补身体的意思。我听别人说过,水井边生长的何首乌质量也好。水井和龙洞旁边的环境都阴冷潮湿,看来何首乌喜阴湿,才易长、蔸大。
旁边一老者见我一直在询问何首乌,又蹲下去拿在手上看,以为要买。趁我站起身时,用手掩嘴,悄悄在我耳边劝道:“莫买,他雕成人头的,敷了泥巴看不出来,做的假。”我对他笑笑:“我是觉得好玩,不买。”
老者听我这么说,放心了。然后给我摆,人身上不论哪里肉痛,把生何首乌弄碎,和生姜汁调成泥,敷在痛的地方,用布包好;再烤烫干净的布鞋底板,热敷布包着的肉痛地方,很快见效,就不痛了。老者说的“肉痛”是指皮下疼痛。
看来老者有故事,我请他去茶馆坐坐,摆一会儿龙门阵。
“何首乌生吃的话,很伤胃,更伤肝。”在茶馆坐定,一杯热茶上桌,老者没喝,双手捧着杯子说:“内服,必须要制好才能用,九蒸九晒。”于是,给我摆起过程来——
何首乌不能直接沾铁器,用竹片削尖做刀,洗干净后切成大块。最后一次洗的水不要倒,把何首乌块浸泡一晚上。洗、泡用陶瓦盆、木盆都行。第二天开始和黑豆一起蒸,泡何首乌块的水做甑脚水。黑豆的量和何首乌的差不多。上了大气后几分钟就可以了,趁热洒上牛奶,仍然盖上甑盖,捂起。凉了后,用簸箕摊开,端到太阳底下曝晒干。甑脚水莫倒,下次蒸前淋在何首乌块和黑豆上。
我打断老者的话:“为什么要洒牛奶?”
“本来是要洒人奶的,现在没得呀!”老者喝了口茶,又说,“往年子,有专门卖人奶的妇女。”
“哦——”我明白,中药治病有很多怪异的地方,规矩也多。又问:“下雨天,何首乌块和黑豆晒不干怎么办?”
老者又答:“用火烤干,烧杠炭火,没得烟子。”
老者继续摆,这样连续蒸晒九次后,碾打成面面,每天舀一调羹,兑开水喝。他听爷爷说:“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老者祖上在乡场上开中药铺,他父亲接手没几年,不允许私人开了,就回家务农。从小,老者在爷爷和父亲那里学到一些中药知识。
有点遗憾,老者没能继承祖业,要不然民间会多一家卖真药的铺子。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告诉我真话:“莫买,他……做的假。”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