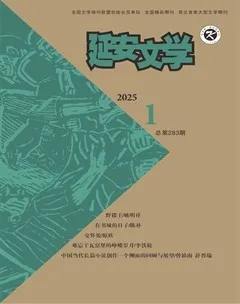方言是故乡和你的私聊
一
这是一部用文学的笔法对方言进行解读的书。
方言作为一种口语表达,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不言而喻;而文学作为以审美为主旨的非实用表达,具有其虚拟性。本书的作者采用实其言而虚其声的方法,通过广泛采集、旁征博引,给这些遗落在僻野荒山、辗转于乡民口中的方言俚语验明正身;将对声波的听觉识别提升到对文字的视觉识别;在钩沉稽古中发微抉隐,为方言本字找到了确凿的实证依据。
作为一个陕北土著,我每天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都是同乡人说话的声调语气和辅之以这种语气的表情神态,濡染既久,自以为对陕北的人文地理、民俗方言还算了解。直到将这本书读完,让人心生惶愧。抛开民俗风物、乡邦礼仪暂且不说,单就对方言的了解,还只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上。好在本书的作者为我们从浩瀚的词林字典中找回了方言本字。洋洋近30万言的一部厚重之作,从方言的撷取到慎密的解读,采摭广博,包罗宏富。从实用性上来讲,这本书可作为工具书。25个类目,400多条词汇,一查便知;从审美上来说,这又是一部文学书。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场景,有对乡邦文献和民俗风物的呈现。而更让我看重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念我煌煌大陕北虽然地接边荒,闭塞贫穷,但歌谣文理,千年永续;方言俗话,本自具足。本书的作者正是在浩瀚的方言语汇中,通过钩深索隐,在为方言的使用纠谬指正的同时,还紧紧抓住方言本字的本源含义和所蕴含的丰富信息,通过考证、辨析、解读,让我们在“知其所以然”中,对这些有着青铜质地,大璞未琢,含英蕴华,历经人世沧桑而不改独特声气,随手拈来便能状绘出人间百态和世道人心的方言俚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二
2013年,延安府城的几位同乡被非遗保护部门邀请到西安。好吃好喝好招待,只是为了办妥一件事——将府城人说话的原声录存下来。
中国何其大,方言南腔北调又是何其的繁杂。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即便将全国各地的方言都按照录存的方法荟萃到同一个博物馆,每个人也都会根据自己的听觉辨识毫无偏差地找到来自家乡的原声。
听觉是一种记忆,一种唤醒,一种精神惦记。
张如意写出了她的惦记。
老早以前,在好几个公众号上读到过她写的有关陕北方言的随笔,每次转发之后,都能在朋友圈引起热烈的讨论。对于这种非专业讨论中出现的对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仅从参与这种讨论的人数之多和热情之高中就能让人感受到:每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都在强调自家方言所具有的专属性、唯一性和不可亵渎的神圣性。
当然,文化的自信首先是来自对方言的自恋。
木心少小离家,五十多年未闻乡音。当他回到故乡乌镇,听到乡亲们口中吐念出的“乖异悦耳,有一种麻痒痒亲切感”的家乡话时,老人感慨时过境迁几十年,家乡人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方言。
曹乃谦噙着一口雁北方言写小说,读者时不时地被小说里偶尔出现的方言土语所磕绊。有人建议他在小说的章节后作些注释。曹说:看不懂就嫑看了。
万物并育不相害,语言也是如此。
推广普通话和对方言进行保护就是一种双轨“并育”。
前者传输方便,交流顺畅,好使;后者在同字不同音的表达中尽显方言摇曳生姿、灼灼其华的语言魅力。这种魅力当然是来自祖先、历史、水土,来自通过血脉植入到体内的那枚不可更换的文化芯片。
这本书的奥妙和趣味在于,作者的训诂考辨不拘于一家之言。因声求义,反复推敲、比较、辨析;将由感官而来的听觉经验诉诸于笔端,从陕北人口中至今还在使用的“活”字中展开叙述。干这事费手。钩沉辑佚,归类整理倒在其次,最考验作者的是对陕北人文地理的熟悉程度和个人认知水平的高低。我们知道,陕北地接边荒,山大沟深,人尤劲悍。产生于这个地方的许多原生艺术为世人所赞叹。试想:在追求标准化、一体化的时代风潮中,一个端一碗洋柿子汤汤和杂面,口里唱着“青线线(那个)蓝线线”,一口还能算出三十三颗荞麦有九十九道棱的人,你若让他改口说普通话,他会感到为难、憋屈、别扭。有学者认为:许多原生艺术,包括与之互为滋养的方言俚语,都可以说是“疯癫”心灵的昭然若现。还是那句话,我看重这本书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每一个生活在陕北或曾在陕北长期生活过的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语言具有一种一开口便能窥见人心的神通力,压根就没有什么“土”“洋”之分。常言说,物无定味,适口者珍。任何语言,能经世致用才是第一要义。历史上的陕北地广人稀,兵连祸结,灾难频仍,曾被人讥为是一块未经文明浸润过的化外之地。能够在“兴废系乎时序”的人世沧桑中,将从祖先口中辗转下来的方言俚语作为一种现成语言为我们所使用,实属不易。这本书,饮水思源,赓续文脉,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将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日渐显现。
三
见过韩少功穿着一双胶鞋坐在田埂上吸烟的照片。愜意自足,一副田舍翁乐见仓廪实的悠然神态。
湘人性格霸蛮,做事有恒;因对“霸蛮”一词不甚了解,我还是在韩少功写的《马桥词典》里找到了解释。其实,这本书不是词典,是作者以马桥人说的方言俚语为由头写的一部展现历史文化和人生世相的小说。小说写得好,是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不论是哪个地域的方言,好像都带有一种悖离雅训、狂野无拘的美学气质。是在冯毅的办公室见到王克明写的《听见古代》,翻开一看,正好碰上一句“夜黑地架后垴畔山上大刮了”的话,让人感到馕口亲切。这本书后来很火、在对方言的溯本寻根中有发现,有见地,是一部挖掘和保护陕北方言的开先河之作。后来又读了王建领、狄马、鲁翰等文化学者和作家写的有关陕北方言的著述和文章,量大面宽,五音繁会。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来,每个人对方言的撷取和解读不尽相同。或心有所念,或情有所寄;或在此一语中发见文言古词,或在彼一言中如遇失意之人。一言以蔽之,能拨动心弦者,当为采撷之首选。如意君以女性的视角,在对方言的撷取上似乎更家常一些。饮食男女,柴米油盐,这些与陕北人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的方言俚语,在作者笔下更有烟火气。想想看,我们所读过的名著佳作,大都以穷理尽性为要。这本书,归类分明,在注释和解读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则逾千言,可单独成篇;短则百余字,也只是为一个方言语汇在使用中恐昧者不察,故标明,仅此而已。正所谓:尺布寸缕,都应珍而宝之,这正是这本书值得称道的看点之一。陕北人说的许多话因为找不到相对应的文字,只能靠声波来识别。本书的作者近年来一门心思钩沉稽古,找回了许多过去只能靠拼音来替代的方言本字;并在对部分方言词汇的注释和解读中,以陕北民歌的歌词或谚语作为楔子,为解读起到了破题解义和画龙点睛的作用。此为看点之二。方言本字本来就难找,而要用文字来状绘出这种语言特有的“味道”,就让人感到有些不好拿捏。陕北人说话声音抑扬多变,用重叠词较多;许多词语听起来很笨拙,实则非常机巧,而且话里头还有许多只能让人意会的留白,如人们常说的“鼻子哼人没深浅”所传递出的意思,就很难用文字来表达。本书的作者源于对陕北人文地理的熟悉和对方言词汇的深刻理解,抓住方言独有的“声气”特点,细心描摹,以文绘声,且笔到意到,此为看点之三。深厚的文学功底,洒脱无拘而又不失风趣幽默的叙事风格,彰显出作者在审美取向上受张爱玲和李娟等人的影响。全书近30万言,文气饱满,行止得当,所描绘出的风土人情及生活场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解读文字的诗意化又和古拙的方言俚语互为映衬,相得益彰。此为看点之四。而让我感到惶愧的是,在这本凭着语言的分量便足以压起铁称砣的厚重之作中,有许多方言俚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种蕴含天机,有如神授,能在核桃壳里掏出果冻的方言妙趣和可圈可点的精采解读实在是太多了。我不作引述,是因为脱离文本语境的引述会让作者的文字失去原有的成色;再说,过多引述原文和频繁使用省略号一样,有偷懒的嫌疑。但在这里我还想要说的是,方言是体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便是你的家当再厚实,也要有人好好来看管。保护方言,敬惜字纸,这是祖训,也是天道。每一个从事方言保护和文字研究的人,实际上都是“说文解字”的参与者。当你懂得汉字构成的神奇枢机后,也就对仓颉造字为什么会引起“天雨粟,鬼夜哭”有了真正的理解。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所使用过的每一个字,包括靠声波传递出的方言俚语,都应该被供奉在故乡的祠堂里。
四
方言是故乡和你的私聊。
所聊的话题虽然没有私密性,但又不足为外人道,因为外人听不懂。
吾乡某地,爷孙俩因孙女要参加礼仪学习培训,为节省几百元,老人在电话中给孙女说:其他培训项目的钱咱交上,普通话就不学了,咱的话管够用。孙女说不学不行,出了门,咱说的话怕人家听不懂。老人接住话茬回怼:他们说的话俺也听不懂嘛。
这是个真事,抄录备忘。
人在年轻的时候,与故乡有一种本能的生分和疏离,老觉得诗和美都在远方。在艰难险恶的世路上跋涉之后,鸟倦飞而知还,这才感觉到还是故乡这棵大树可依傍。美国怀乡写实主义大师安德鲁·怀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故乡。他画田园山水,画故乡人物。他说将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语言精确地展现在画作上是他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语言又必须是带有故乡特色的方言,而不是公共用语。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不懂得经过漫长岁月才积累起来的方言俚语里所蕴含的价值。
读完如意女士的这部书稿,想起多年前我和同事第一次跨省采访的情景。那时候旅游业还没有兴起,人口限制流动。两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还都有些文学情结的年轻人,在火车“哐当”复“哐当”的行驶声中讨论着一个话题:为什么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常能读到“旅途中的无聊和寂寞”的话语?谈论了半天,最后给出一个辞条式的解释是:人在旅途中,因心里的某种期待在未被确定之前产生的一种低迷情绪。到达山东济南,刚一出站,老远就听见前来接站的同乡“飚”来一句打诨中带着问候的家乡话,温暖,亲切,让人一听,立马就有了一种与山河故人同在的踏实感。之后去了寿光,见到来这里学习大棚菜种植的许多同乡。一见面,先客套,接下来便是抢着说话。越是在异地他乡,家乡话就说得越攒劲,越地道。若能把当时说的那些话录下来,绝对是教科书一级的方言比拼。活泼、轻松、粗俗的相互戏谑中还透着机智。第二天,当地的一位领导来看望大家。这位领导很和霭,说一口胶东话。他说话的语速虽然慢,但许多话我还是没听懂。想起贾平凹的那句“普通话就是普通人说的话”的著名调侃,时不时地被一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拿来给自己打圆场。后来,经过琢磨、观察,我发现许多大人物不凡的气质和带有神秘的威严,确实与他们不说普通话有关。
绥德自古以来就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邑,有“天下名州”和“商贸旱码头”之称。这里人文荟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陕北民间艺术和方言俚语的富集区。本书的作者在童年时就与外婆生活在绥德张家砭一个叫十里铺的村庄。几十年之后,回忆起外婆当年在硷畔上的那声呼唤,竟将贮存在她幽深耳洞里的有关方言的记忆给拽扯了出来。在这个快手抖音满天飞、脱口秀热蒸现卖竟成了时尚消费的今天,作者能在乱云飞渡的天宇下另辟苍穹,从嘈杂的人世喧嚣中转身去了田野,去了只有留守老人在墙根负暄的荒村,对遗落在这里的方言俚语悉心采撷,笔录心记,每有意会辄录入箧中;在饮其流而怀其源中,将乡音化为纸上声,让这些因与口音对不上号而被冷落的方言本字又端铮铮地站在字林辞海中。余华说,一个中文作家只要掌握上两千个汉字就足够用于写作。我理解他说的意思是:汉语的运用之妙全在于来回倒腾。我对陕北方言的保护关注有年,经阅读诸贤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再加上如意君采撷的这400多个方言词汇,自觉从今往后,即便走过九州八十三县,在语言交流上不会有碍。民间广阔的山野和田间地头是从事方言采撷的广阔天地。干这事,很寂寞。有点像一个人回到他曾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庄,走进祖屋,看见门背后立着一柄被时光抚摸得有点褪色的手杖。他嗅着祖屋里散发出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他感到自己现在唯一要做并能够做到的是:拂拭掉飞落在这柄手杖上的尘埃,替不在场的祖父说出这柄手杖的来历。想想也是,人若没有这根策杖相依,那前进的步履又将会是多么的艰难。
是为序。
责任编辑: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