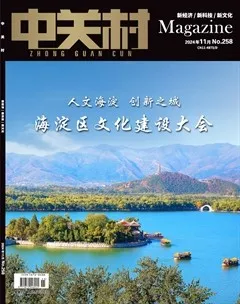曹雪芹《红楼梦》与海淀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文学家堪与曹公比肩,《红楼梦》以对人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人类情感的关照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级文豪相媲美。
谈起海淀历史文化标识,素有“红、皇、兰”一说。“红”,是指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兰”,是指纳兰容若和他的《纳兰词》;“皇”,是指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海淀的文化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但是这三个标识不管从深度和广度上,更广为人知,因而成为海淀的自豪,增强了海淀的文化自信。
我们就来谈谈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以一部小说将中国传统文化统统囊括其中,人们一提起《红楼梦》就自然想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写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鲜活的人物、凄美的爱情,是一部读不完、说不尽的千古奇书。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文学家堪与曹公比肩,《红楼梦》以对人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人类情感的关照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级文豪相媲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曾于2022年农历四月十日,在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门前有过一次“行为艺术”。他与好友王振在馆前小广场砖地上,用地书软笔写了几首《红楼梦》里的诗,他把这次行为叫作“曹门学书”,以此来表达对曹公的敬意。
作家的心是相通的,曹雪芹很高傲,他早就知道自己作品会面临不同的理解,因而他在《红楼梦》的开篇就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诗也正是莫言在曹馆前地书的内容。莫言在交流中接着说:“中国有部《红楼梦》,中国人一直在解释,越解释越糊涂。所以高明的小说家会把思想藏在故事里,把精力放在人物上,让人物自己表达,所以有的小说充满悖论。以后我还要创作这样的小说。”
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对于作者曹雪芹的研究,可以说从这部作品诞生开始,就存有争议。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是乾隆十九年(1754)完成的,至今270年了,从最初的脂砚斋、敦诚、敦敏、墨香等人到民国时的胡适、蔡元培,到现在的研究者和上亿的“红迷”,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因为人们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根据自己的阅历和自己对生命的认知来理解这部文学作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理解深度又有不同,而这也正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
《红楼梦》不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惬意,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它写出了人生的苦痛,也写出了人生的诗意。作为四大名著之首,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版本为例,这是一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书中几百个人物,其中有几十个人物个性鲜明。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呢?白先勇先生把人群分为两类:读过《红楼梦》的和没有读过的。他想表达的是,读过的就知道什么是命运,对事物有一定的认知,活得从容;没读过的不知命,因而活得比较被动和仓皇。生活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但是人性、人的情感、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并没有变,因而不存在哲学、道德上的背离,而《红楼梦》的文学艺术价值,在当下依然处于巅峰地位。
我把《红楼梦》比喻成一个大舞台,作者把各种生命的形态在这个舞台上演给我们看:高贵的、低贱的;儒雅的、粗俗的;富贵的、贫穷的;美丽的、丑陋的;年长的、年幼的;当官的、平民百姓、流氓地痞、贩夫走卒等,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就像舞台下的观众,在看这些人物的演出。这时候《红楼梦》的代入感就出来了,我们在看演出,也就是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幻化成里边的一个人物,你是舞台上的哪一个呢?你是书中的哪一位呢?这就是成功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力量。成功的作品,他的人物是永生的,《红楼梦》里的人物,至今仍然鲜活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文化形象的代表,英国有莎士比亚,印度有泰戈尔,俄罗斯有托尔斯泰,法国有巴尔扎克、雨果,如果中国拿出一位作家与他们比肩,那只有曹雪芹。
对于作品的研究,我们要遵从文学的规律,而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研究,我们要遵从历史研究的规律,要重证据,要严谨。如果两者混淆了,则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作者曹雪芹的研究,最初只在熟悉他的很小的范围里,那个时候其实还说不上是研究,直到胡适先生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即便这样,对作品的赏析解读,更甚于对作者的关注。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是对作家研究划时代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香山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的发现,成为曹雪芹研究最大的爆点。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创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以《红楼梦》曹雪芹主题的纪念馆,因而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围绕正白旗39号院,是不是曹雪芹的西山故居的争议,至今没有定论。红学界对曹雪芹西山著述的范围,支持到卧佛寺樱桃沟一带。我在曹雪芹纪念馆做了十年馆长,这段工作的阅历,让我对这个问题观点很明确:是不是故居并不重要,正白旗39号院,是曹雪芹的家,是人们缅怀、祭奠、拜谒曹公的一个地方。2004年,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先生曾向全国政协会议有过一个提案:给曹雪芹在北京西山安个家。这个提案得到了当时整个文艺组30几位知名艺术家的签名支持,在京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李希凡、周汝昌、胡文彬、张庆善等都发声、发文表示支持。《中国政协报》《光明日报》作了报道,题目就是“给曹雪芹在西山安个家”,对曹雪芹纪念馆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
目前学界对曹雪芹的了解,无非这样几个方面:从作品中去找他的影子——“读其书,欲知其为人”;从清代的档案中找线索——但是从他叔父曹頫之后,曹家在官方档案中就几乎见不到了;从清代人的笔记中窥其侧面——袁枚、裕瑞、周春、富察明义《绿烟锁窗集》(题红绝句二十首)、永忠德《延芬室稿》等;从友人诗中看性情——友人诗总共20首左右,主要是敦诚、敦敏、张宜泉的;从民间传说中看风骨——内容涉及家世、著述、才华、性格为人等;从他生活的时代和家世——了解他的思想意识和“家族的记忆”。
研究者都是根据自己的学识素养,来融合这几个方面,将其还原到曹雪芹生活的历史时代,还原到那个时代的制度下,才可能更近于事实真相。因为学识素养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而新材料鲜有发现,即便是发现了,也缺乏权威性的论证和认可,所以越来越多的个人臆想便被作为学术成果。
2013年,在海淀区的支持下,北京曹雪芹学会与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大师与经典”国际论坛。英国莎士比亚、俄国托尔斯泰、法国巴尔扎克故居、基金会主席等均到北京参加了论坛。除了交流文学巨匠带给人类的精神抚慰外,我还就故居问题与莎士比亚故居基金会主席戴安娜女士进行了交流。我问戴安娜主席,在你们英国,连莎士比亚这个人是否存在还有争议,你们如何面对质疑、把这个主题做好呢?戴安娜的回答至今令我钦佩。她说,莎士比亚是我们的国家形象,这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共识。我们的国家向世界推介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三分之一国家的教材里,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她的话令我们深思,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宣传,我们站位高度不够,因而总是陷在学术问题上纠结。
越纠结越荒诞,越研究越荒唐,目前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竟有120多人了。其实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共识,《红楼梦》于中国: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识;是一种曹雪芹所在的清中期社会生活鲜活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典雅、高贵、精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质。同时它又成为两个途径:现代中国人了解古代文化的途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
再谈到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与海淀的关系,无疑这是我们手里的一个珍宝。国内南京、辽阳、河北都有这个主题的纪念馆、纪念园,但直接与曹雪芹本人相关联的,只有位于我们海淀的黄叶村的曹雪芹纪念馆。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宝贝,因而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把它做大做强。
“红”“皇”“兰”有着内在的联系,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正是乾隆皇帝大肆修建、扩建“三山五园”的时候,发生在身边的重大事件,被这位天才作家随手拈来,与他儿时稔熟的江南园林融合在一起,成就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纸上”园林大观园。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年轻时的伙伴、至交,宝玉的多愁善感多少带有他的影子。这三个主题分开各有内容,互联互动则会产生大于三的文化动力与魅力。
感恩曹公,他为上风上水的海淀、为人类留下了弥足宝贵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