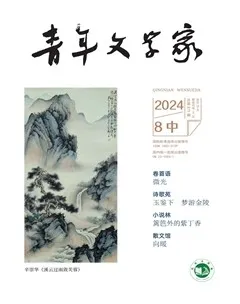从锁入自我的“城堡”到“春台”之中的“共在”



小说作为一种叙述文体,其本质是对时间的凝固、保存和创造,对于事件的叙述无论如何也要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律。但是,“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空间的价值不能被低估。1945年,美国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用“空间形式”(Spacial Form)一词来概括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的时间的空间化倾向,对普鲁斯特、乔伊斯等现代作家进行了研究。而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也具备典型的空间特性,历来有数多学者从空间角度对其分析。
格非作为中国的先锋作家之一,对于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其对于《卡夫卡谈话录》的导读《卡夫卡的钟摆》一文与经典作家进行了对话。在他看来,卡夫卡是钟摆起步的那一端,而他则是钟摆开始回旋的这一端。他在书中提到,在读卡夫卡小说时有一种最常见、最根本的经验,那就是他的小说都是一个个黑暗的、没有边际的开阔空间,不经意间进入便会感到眩晕。这个黑屋子里的部件具有某种反常化的效果,但空间本身大得没有深度,其所设置场景总是非常单调,仿佛都被浓雾包围。这种从一个空间再到另一个空间—空间的连续性与无穷性在格非的小说中也得到了体现。将格非的新作《登春台》与卡夫卡的《城堡》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两本书的空间结构及其深刻的内蕴。
一、村庄与“春台”的空间象征
(一)空间的季节象征:村庄之“冬”与“春台”之“春”
在黑格尔看来,空间即时间,时间是空间的真理。而季节作为时间的外在表现形式,恰恰也是空间的表象。村庄以冬季作为空间表象,而“春台”则是以“春”作为其空间表象。
《城堡》以“城堡”作为标题,但城堡并不是主人公K所处的空间,只是K一直在追求的一个东西。K一直处在村庄之中,村庄才是《城堡》的主要空间。
《城堡》的开篇即写到K抵达了村庄,但对于K是如何来到村庄以及为何来村庄,小说均没有交代。可以说,K是“被抛”入了村庄。在海德格尔看来,“被抛”并非意味着“被决定性”,而是指“此在”根本的生存方式。只要“此在”作为其所是的东西存在,就始终处在被抛的状态中。之所以被称为“此在”,是因为“此”只能在“此”存在,而这个“此”可以是任何一个“此”,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因此,在“此”也即不在“此”,因为“此在”随时可能被拽入新的可能性,也即被抛入“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K被抛入了村庄,这看似荒诞,但只是一种常态。常人的生活看似充满秩序,但这种现成的秩序随时会被风暴破坏,这种破坏而非现成的秩序才是真正的常态。卡夫卡的其他小说中也有这种类似的现象。例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觉醒来时惊奇地发现自己有了甲虫的躯干;《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忽然被抓,被要求进行审判。这些看似荒诞的开头实际上只是“被抛”的一种可能性,荒诞恰恰是常态。与这两部小说不同的是,《城堡》中的K被抛入了一个实在的空间—村庄。
《城堡》开篇即写到“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强调了全书以冬为背景,而且春天和夏天都很短暂。在深邃的冬季画卷中,雪的意象贯穿全文。雪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冷漠氛围,更将生命的温度降至冰点,使得希望也随之冻结。在这冰封雪飘的严酷环境中,K的无助感越发凸显。为了生存,K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求他人的援助。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使得这位异乡人K的失败成了无法逃脱的命运。在村庄里,厚厚的积雪使得K行动极为不便。他意外步入了“长得没有尽头的村子”,最后停下了脚步,感到体力不支,再也无法前行,陷入了茫茫的雪原。被城堡抛弃的巴纳巴斯一家与K建立了联系,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欺骗的悖论关系”(格非《小说叙事研究》),K以为的希望不过是他的主观幻想。
与《城堡》中明显的季节指向相比,《登春台》的“春”的季节指向较为抽象。尽管小说的时间线庞杂,前后跨度达四十年,但“春”的内涵在全书中都有较为集中的体现。
首先,是“春台”本身的象征。“登春台”这一标题出自老子《道德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陈鼓应将其翻译为“众人都兴高采烈,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书中的“春台”实际上就是指小说中四位主人公的交会处—神州联合公司。沈辛夷面对家庭的期望,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后攻读研究生,历经曲折后成功进入神州联合公司这一知名企业;陈克明出生于北京郊区,在亲朋好友的协助下尝试各种小本经营,然而都未能抓住商机,生意连连失败,不得不以“开黑车”为生,然而命运却在他最绝望时带来了转机—神州联合公司的创始人周振遐注意到了他,将他招入公司;窦宝庆来自甘肃偏远山区,误打误撞地来到北京,因表现出色被周振遐选拔为司机,甚至一度有意将他培养成接班人;周振遐本是一位恬淡的学者,在大学好友蒋承泽的邀请下加入了他的创业公司,在蒋承泽因癌症不幸去世后,周振遐接过了公司的重任,成为新的管理者,公司做得越来越好。
四位主人公齐聚神州联合公司同样是一种“被抛”,是一种存在可能性的体现。但这种“被抛”不像《城堡》那样极具荒诞性,而是在表面上看来充满生机,正如老子所说“如登春台”,似乎都被命运眷顾。四位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讲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且展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其次,是“花”的意象。在小说《周振遐》一章中,周振遐先是在7月盛夏频频造访阿苏卫的花圃,第二年的11月则精心挑选了一批月季大苗,将之移栽到花园中。但在栽培养花的过程中,周振瑕频频受挫,受到花枝的无意伤害,在非理性中作出残忍之举。后来,周振瑕意外地被海格瑞这种母本月季吸引,在苦心栽培后,海格瑞在第二年春天开启了枝繁叶茂的爆花时间。而这美丽的花给他带来了种花几年来的唯一赞美,他亦在这解语之花中得到了宽慰。这看似无意义的片段恰恰在关键处指引了文章的核心,种花的过程其实就是四位主人公的命运的概括—花盛开时是绚烂的,但种花、养花的过程是艰辛的,过程中充满了意外与非理性,正如四位主人公登上“春台”的过程一般。
(二)空间的无限延展与同一的指向
村庄与“春台”的空间在不同人物视角的转换中得到了延展,但最终都指向了同一的空间。
村庄作为一个封闭但又大得无边的空间,其内部的结构极为单调。一排排几乎毫无差异的小房子,一条条走不完的街道,构成了村庄的全貌。而这些房子的内部格局在办公室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最具典型性的就是村长对于索迪尼办公室的描述。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一捆捆公文,由于不断地从文件堆中取出、放入文件,而且过程匆忙,这一捆捆文件就不断地掉到地上,而这持续不断掉落的哗啦声就成为他办公室的典型特征。文件是空间的压缩,而文件的掉落又象征着空间的膨胀。空间就在这种永无停息地压缩与膨胀中慢慢延伸。在巴纳巴斯的描述中,办公室里放着一本本大书,官员们并排在那里翻阅,但他们并不是交换书,而是交换位置。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人却始终在不停息地流动,这同样构成了空间的延展。
村庄的内层空间也在主人公K与周围人的关系中慢慢延展开来。K来到城堡时首先进入的是客栈,对于村庄和城堡并无任何了解。第二天,K走出客栈,想要走去城堡,但只能远远观望,并且其中的布局似乎与村庄并无差异,只是普通的建筑群。为了接近城堡,K来到了桥头客栈,认识了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进而认识了客栈的老板娘。从认识老板娘开始,小说的视角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起初,小说是从K的视角来叙事,K主动地寻求接近城堡的方式。但认识老板娘之后,K成为一个被动的倾听者,老板娘的长篇叙述使她短暂地成了小说的主角,也延展了村庄的空间。随后,K又认识了村长、奥尔加、培枇等人,在与他们的对话中,K几乎只是倾听。这些叙述者的视角各自短暂地成为小说的主要视角,使得小说的空间不断延展。而在比尔格的长篇大论中,这种空间的无限延展更是形成一种压迫,使得K昏昏欲睡。村庄的空间在不同人物的叙述中得到了延展,但是所有叙述的共同指向—城堡的空间却仍是虚无的。城堡始终不可知。
《登春台》中的空间也同样在不同的人物视角中得到了延展。小说的序章从周振遐坐在长椅上的叙述开始,先后经历了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不同视角下故事的叙述,最后又回到了周振遐。但周振遐就是书中所有人的真正指向吗?或者说,周振遐就是空间延展的根本指向吗?恐怕并不是。周振遐的存在就类似于《城堡》中K的存在,他将书中的人物串联起来,但真正指引着书中人物的,实质上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在小说的一个片段中,陈克明问静熹,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幸运或不幸。静熹的回答是,“大概是老天爷的脸色吧”,“如果老天爷的心情不好,不让你获得幸福,那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这个片段实际上道出了小说的核心思想—命运具有偶然性,每个人都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理性的方式作出选择,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被这种非理性的“老天爷的脸色”决定,包括之后陈克明生意的频频失败,又意外得到周振瑕的赏识,包括窦元庆被周振瑕提拔,而后又与郑元春相识,都处于意料之外。并且,个人的冲动也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陈克明的出轨导致与静熹的关系日渐糟糕,最后二人分手;以及窦元庆向郑元春全盘道出自己的过往经历,导致被告入狱。这种种的意外交织,最后才有了四位主人公在“春台”的会合。因此,空间的延展的根本指向并不是周振遐,而是非理性的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城堡》中的城堡,统治着一方空间,自身却又不具备空间的形式,更准确地说,二者都是“力”。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力的运动过程进行了阐释:“力的一个环节,即力之分散为各自具有独立存在的质料,就是力的表现;但是当力的这些各自独立存在的质料消失其存在时,便是力本身,或没有表现的和被迫返回自身的力。”村庄与“春台”都在“力”的作用下无限延展,各自分散为独立的发展过程,但这些复归于一个同一的空间—在《城堡》中表现为“城堡”,在《登春台》中则表现为“春台”。
二、《城堡》:K将自己锁入城堡
K只知道自己唯一的目标是进入城堡,但是始终处于村庄之中。小说对于城堡的描述晦暗不明,其存在与否不可判断。“城堡”这个词极具空间特征,但在小说中却基本没有体现其空间性,可以说是一个虚无的空间。但这个虚无的空间又恰恰是村庄这个实在空间的存在基础,村庄中的每一个人都信奉城堡,但一致认同城堡不可进入—这个虚无的空间最后成为一个虚无的概念。只有K不愿相信城堡的这种虚无性,渴望接近城堡。
但是,城堡是无法进入的。在K刚来到城堡给城堡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能进入时,得到的回答是“任何时候都不行”。而通过K寻找土地测量员相关文件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K担任土地测量员这一决定本身便存在谬误,因此他无法合法地获取进入城堡的身份认可。这一系列的行动和尝试,均未能帮助他离城堡更近。
此外,即便K获得进入城堡的许可,城堡本身也并非利益的象征和稳定的保障。城堡为K指派了两位助手,实则是对其进行持续的监视,使他陷入无法挣脱的束缚之中。这两位助手不断扰乱K的日常生活,打破他的宁静,甚至骚扰他的未婚妻。尽管他们来自城堡,却未能对K的生活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进而凸显了城堡对K生活的消极作用。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所谓的利益与安定,在现实中很可能是虚幻的。城堡中的高级官员克拉姆,其存在曾被视为确凿无疑,K甚至在酒馆的门缝中目睹了他的形象。然而,卡夫卡通过奥尔加的叙述,使读者对克拉姆存在的真实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么为什么巴纳巴斯还要怀疑在那儿被称为克拉姆的那个官员是否真是克拉姆呢?”在村庄中,关于克拉姆的描述呈现出了多样性,每位目击者对其形象的描述均有所不同,这种不一致性使得克拉姆的存在与否成了一个难以验证的谜团,由此,城堡的存在与否也不可知且无从考证。
《城堡》中的K一直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寻求进入城堡的办法,作出的选择与城堡强权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他反对酒店老板娘与村长的教导,骗走了弗丽达,目的是使克拉姆愤怒,由此引起克拉姆的注意,以此来接近克拉姆,以进入城堡,但反而离城堡越来越远。芝诺关于运动不可分的哲学悖论“同《城堡》里的问题一模一样,因此,运动物体、‘飞矢不动’悖论中的飞矢和‘阿喀琉斯追乌龟’中的阿喀琉斯就是文学中最初的卡夫卡的人物”(博尔赫斯《探讨别集》)。K深陷逻各斯的困境。“这个K营造了城堡作为自己的命运,只是为了反抗它、背叛它,反抗与背叛的目的又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由。”(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K朝思暮想的自由实际上正是他想要摆脱的东西,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对于城堡的反叛之中,无法抓住,一旦抓住,便不是自由了。
“城堡”一词的德语为das Schloß,而schließn(中文意为锁上、关上)的过去分词为geschlossen。因此,das Schloß具有城堡与锁上、关上的双层含义,可以理解为城堡之门始终是关闭的。由此,K从一个空间“被抛”入村庄,渴望进入城堡,但始终被锁在城堡之外。而困住他的空间便是村庄,他在这个单调但又大得无边的空间里越陷越深。
那么,K一直在苦苦寻求的城堡究竟是什么?城堡是一个虚无的空间,甚至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历来有不同的学者对城堡进行过意义的阐释,如曾艳兵、李爽曾在《百年〈城堡〉漫漫长路—卡夫卡〈城堡〉主题新论》中将其概括为三个核心的方面:从神学角度来讲,“城堡”是天国或者上帝的“恩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城堡”是官僚专制机构的隐喻;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城堡”是精神分析的寓言。在小说本身的朦胧叙述与众多学者对城堡的意义阐述中,城堡的意义反而显得更加不可知,即便是所有的观点综合起来也难以概括城堡的所有含义。城堡最后走向神秘、虚无,始终浮在半空中,不知是何物,也不知有无。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村庄本身可能就是城堡,每个人都是克拉姆,甚至,K自己便是克拉姆本人。城堡的虚无空间与村庄的实在空间相重合。但是,K始终信奉城堡的存在,在这种永恒追求中恰恰把自己锁入了自己的城堡,“力”本身被迫进行无穷次的循环而没有结束之时,最终导致K在自己的城堡中越陷越深,被困在“无限性”之中。“无限性”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被视作一个环节,标志着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转变,体现了持续不断的循环过程。通过自我反思,这一循环的终点与起点相互颠倒。由于K始终没能达到实现的终点—城堡,因此一直在外部的驱使下,被迫进行一圈又一圈的循环,终点与起点并没有本质差异,因此这种无限并不是“真无限”。K从来不曾意识到,他自己可能一直处于城堡之中。
三、《登春台》:“春台”之中的“共在”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专门探讨过“共在”。海德格尔首先强调了“在之中”,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意味着“居而寓于……”,也即“此在”本质上具有空间性。“此在”本身有一种切身的“在空间之中的存在”,不过这种空间唯基于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才是可能的。因此,“此在”“在之中”存在,即“在世界中存在”。但“此在”并不是单独在此,他人“也在此”,“此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同世界。因此,这种“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而他人的在世界之中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可见,“此在”本质上是“共在”。这种“共在”并不涉及物理距离上的远近,而是实际生活的共在。在《登春台》中,四位主人公有各自的生命轨迹,但又通过种种意外与偶然彼此相连,显示出一种实际生活中的共在。
“共在”的一种倾向是庸庸碌碌,是人处在平均状态的一种表现。而公众意见则在当下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其为正确的。在《登春台》中,格非特别强调了公众意见对于个体的影响。在信息化的时代,全球性的巨大的社会网络系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跟随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信息,忙忙碌碌,不知道在追逐什么。格非借用海德格尔的思想,将这无形的网络称之为“他人”,而这他人恰恰又“查无此人”。
《登春台》中的人物在看似登上“春台”,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又在“他人”的支配下面临各种新的困境。当母亲身患重病时,沈辛夷惊讶地发现母亲仍在盘算资金,企图东山再起,自己却始终对“母性”的存在抱有希望,难以放下孝顺的观念;陈克明在一次意外的亲密接触之后与静熹分手,但内心始终无法接受,总是想着再与前妻会面;窦宝庆在公司里结识了风情万种的郑元春,向她敞开心扉,却不料被她送进了监狱,即使如此,心里还念着她的想法与感受;周振遐却害怕与人群的接触,试图躲开所有的人,在长期的尝试中,他渐渐学会了对社会关系的要求漠然置之,却又无法摆脱道德上的自我谴责。
因此,登上“春台”只是暂时的,且登上“春台”也并不意味着利益的满足与安定。正如叔本华所言,“意志自身在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穷的追求”(《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欲望没有满足之时。众人的烦恼是无穷无尽的,在登上“春台”后他们仍然受到“他人”的羁绊,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乃至支配着他们的生活。
公众意见对个体的存在影响如此之大,甚至起到了支配作用,那么公众意见一定就是消极的吗?海德格尔强调,本真的自我就处在他人之中。本真的自我存在并不是要从他人之中解脱出来,自己本身就是他人的生存变式。人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才能够获得这种本真的自我存在。
周振遐这个人物是本真存在的很好体现。他真正的自我实现表现在向死存在的实践中。在小说开头,作者对于生与死进行了大段的论述,将死的话题引到周振遐身上—“那些通常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死亡,如今也在要求他即刻兑现”。在这种将死的感觉之前,周振遐神思恍惚,在再次抬起头之时,大街上已是一片沉寂。他在意识到自己即将昏迷之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对生的渴求,竟能够饮下被两枚烟蒂污染的脏水,还能够清醒地给董事长陈克明发微信。而那遥远的声音正是来自周振瑕的内心深处,从他对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已然没有太多的执念。在他出院之后,他主动接受了女邻居送的丝瓜和紫苏叶,第一次没有犹豫就接受了女邻居的邀请。他不再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感到恐惧,而是欣然、自在地接受了这一切。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强调,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而先行表明的就是对最本己的最极端的能在进行领会的可能性,也即意味着本真的生存的可能性。周振遐在死中意识到了自己能在的可能性,不再去逃避,而是让自己主动融入社会之中,在与他人的“共在”之中主动把自己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
与格非的以往小说相比,《登春台》展现了一种面向现实的社会性写作,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时期,具有了更强、更直接的社会性。并且,小说对于现实的涉猎的广度,在格非个人的创作中也是空前的。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命运,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将永远无法摆脱这种非本真状态,永远处于沉沦和被抛状态之中呢?并非如此。海德格尔认识到,“真正可怕的东西并非世界成为完全技术的世界。更可怕得多的是人对这世界变化没有准备,我们还不能够沉思地达到适当地探讨在这个时代真正上升起来的东西”(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只有这种沉思才能让个体在面对现代技术世界发展时获得一种主体的力量。由此他提出“诗意地栖居”,与大地亲近,也即与本真存在的亲近。格非的《登春台》便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文中的人物并非通过现代网络产生了命运的交织,而是通过偶然性的力量,具有一种如同《城堡》一般的梦的结构。《登春台》中的人物登上“春台”之路,也是一条探寻自我存在之路。如同《城堡》中的K一般,他们受到根深蒂固的“他人”的观念的影响,一次次地陷入困境,一次次地处于“被抛”境地。《城堡》里人物的淡漠联系与《登春台》中人物的紧密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也赋予了空间不同的内涵。他们不像《城堡》中的人物那样是彼此孤立的存在,他们彼此之间命运的联结指引了他们的前进方向,并提供了一条真正的本真存在之路—这条路不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之中,而恰恰就在与他人“共在”的世界之中,也即在“春台”之中。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异—《登春台》更强调此岸的自我实现,书中人物在“春台”之中的“共在”便是一种体现;而《城堡》将这种解脱交付于彼岸的“城堡”,可望而不可即。不论是何种思考方式,都丰富了空间本身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