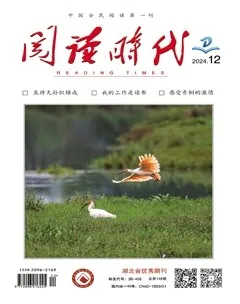“玲珑宝塔”化“仙楼”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这是李太白登扬州西灵塔时吟咏的诗句。“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这是高适登广陵栖灵寺塔时吟咏的诗句。唐人喜登临高耸的佛塔远眺,诗人更因此而发兴吟诗。而在都城长安,当慈恩寺中的雁塔重修成砖构的七层高塔之后,更是人们登临俯瞰京师的绝佳场所。
在今人心目中,雁塔正是唐代文化的象征。而将宝塔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中国城市的标志,也是近代西方人的普遍看法。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于1929年所写书籍的插图,画出了他心目中中国圣人孔子的形貌:这位中国“伟大的精神领袖”坐在山丘的树下,望着山下的一座中国城市,其间耸立着几座“玲珑宝塔”。他认为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00年的事。当然,在这里房龙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在孔夫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宝塔”这种高层建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俗称的“玲珑宝塔”,实际是佛教建筑中的佛塔,它本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东传,佛塔建筑也随之东传中土。
“宝塔”化“仙楼”
在西天梵境古印度,佛教初兴时并非“像教”,那时没有塑造供信徒礼拜的偶像,而是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为向已涅槃的佛陀礼拜的对象,塔即为其中之一。塔,按梵语音译称“窣堵波”,又译为“塔婆”。在古印度,佛塔的基本造型是一个大圆馒头一般的塔体,塔顶中心树立上带相轮的刹,又因塔体像一个覆扣的圜底钵,故习称覆钵形塔。
这种在古印度流行的大圆馒头形貌的覆钵形塔,在东汉末佛教初传东土时是否也流传到了中国?在文献中缺乏记述,更不见有实物遗存。传说佛教初传汉土,在东汉都城洛阳最早建造的白马寺中,“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因记述简略,故此壁画中的“塔”是什么模样谁也不清楚。但据文献记载,汉时人们对佛的认知,只是将其视为外来的神仙,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或将佛(浮图)与黄老并祠,或杂厕于西王母等神人仙兽之间,汇集于中国传统的神仙信奉之中。因此,佛教的形象也与神仙一样被称为“仙人”。
传世文献经常提及,东汉、三国时期有一类建筑为“浮图祠”(或称“浮屠祠”“佛图祠”),僧人似居其中。最著名的文献记载,与东汉后期的笮融有关。
大约在汉献帝初平四年,陶谦任徐州牧时,使笮融督广陵、丹阳运漕。笮融信奉佛教,就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这则记载表明笮融所修“浮图祠”即佛寺,是将原古印度佛寺中心的覆钵形塔改为中国建筑的重楼,周围建阁道。在楼顶树“铜槃九重”,也就是将印度佛塔顶中心树立的带有多重相轮的塔刹改建在楼顶上。为什么选择重楼来取代馒头状的覆钵形塔?或许与汉人崇信“仙人好楼居”有关,佛是“仙人”,所以将供奉他的塔修成重楼形貌。
最早的中国式佛塔
在20世纪前半叶,对《三国志·吴书》中关于笮融“浮图祠”的记载,中国佛教史研究者只能从文字记述知道它下有重楼、阁道,顶“垂铜槃九重”,但其具体形貌则无从想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空前发展,不断在东汉末年乃至魏晋时的墓葬出土文物中,获得数量众多的陶制楼阁建筑模型,有的在高楼的周围还筑有阁道,从而可以对笮融“浮图祠”的具体形态进行推测。进入21世纪,一项新的考古发现对解析笮融“浮图祠”的具体形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2008年10月,在湖北襄樊菜越发现的一座墓内,出土了一件施黄褐釉的陶楼。那是一座二层楼,周绕围墙,前设楼院大门。陶楼平面方形,在一层和二层间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屋脊起翘作叶形饰,在脊的居中处,设一馒头状覆钵形座。座体镂空雕饰母子熊斗虎图案,座的中央树立刹杆,上饰相轮七重,最顶端饰有一兽,形体呈弯月状。楼院大门设门楼,两扇门上各嵌饰铺首衔环,铺首上又贴塑一裸身童子像,肩生双翼。大门右侧墙上另开一扇小门,门扉上亦贴塑一双翼童子像。这座陶明器明显模拟的是一座浮图祠,墓葬的时代被推定为三国孙吴初期,应与笮融建浮图祠的时代相差不远。只是陶浮图祠只有两层楼,又无阁道,规模较小,无法与笮融所建相比,但是提供了在重楼顶上树立塔刹的具体形象。
以此,再参照已出土的大型汉代陶楼模型,例如河北阜城出土的大型五重陶楼,以及甘肃武威雷台魏晋墓出土的周建阁道的高层陶楼,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想象复原出笮融所建的可容三千人的浮图祠的宏伟形貌。那就是将中国传统重楼与西来的佛塔塔刹相结合,所建成的最早的中国式佛塔。
“仙人好楼居”
随着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发展,古人的宗教观念和信仰体系也在发生着改变。从对“天”与“神”的崇拜发展到对“人”的推崇,民间信仰逐渐走向成熟的体系,人事的重要性也日渐彰显,正所谓“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丧葬中的建筑和随葬品源于对现实世间生活的模仿和再现,为逝者重构一个神秘的虚拟世界,观念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礼仪性远大于实用性。陶楼的本质是随葬建筑明器,但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人们对心中理想的实践再现。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一言———“仙人好楼居”。古人多认为仙人都是居于高楼之上,建造高大的楼观便是与神仙结交相会的方法之一,“登高”的信念深深地镌刻在百姓的心里,阙观楼阁也就承载着世人对神仙世界的憧憬和向往。因此,借助明器对仙界的图像模拟,通过媒质材料的转换与符号元素的重构,营造出地下世界的叙事场景,表达出古人对上天的崇拜、对仙境的向往,借逝去之人实现他们成仙的愿望。
(综合自《探掘梵迹:中国佛美术考古概说》及“文化艺术出版社”)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