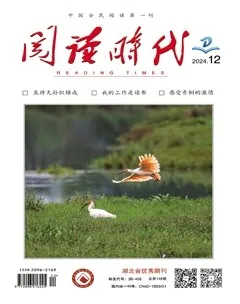用书种下一颗种子
对我们来说,阅读,从来不是课外阅读,它本身就是语文学科的课程核心,并不局限于语文学科,而是所有学科全面推进;也不仅是作为学科内容被落实下来,而是这个场域内所有人真切的生活方式。
“读”是课下自由阅读,是一段随着年级升高,从“海量”到“深度”、从“悦读”到“啃读”的旅程。“思”是课堂主题讨论,是用问题思辨的方式,帮助学生真正读懂故事,这是他们能够持续沉浸阅读的关键。“写”是用文字表达课堂思辨的成果,在阅读的同时,引导学生用写作的方式关联自身,表达观点。“讲”是口语表达,包括讲述、演讲、对话等,这是创设共同生活的场域,是对之前独立写作的补充和深化。当然,还有一个隐形的、贯穿始终的维度是“活”,就是让故事的精神在教室中活着,成为真正能够帮助学生穿越困难的观念系统。
在童书中打开生命的可能
小学低段,儿童的认知特点决定,他们是用整个生命在感知世界,精确的学习任务必须置于意义背景之中才能有效发生。因此,故事的输入(自由阅读和课堂共读)与同步地写、讲、演等输出,便是母语学习的重中之重。
我们学校的每间教室都有图书,确保学生们课下随时可以进入阅读状态,这是让他们爱上阅读的第一步。在此之上,需要进入旨在促进思维提升的课堂对话,比如二年级讲《丑小鸭》,我们会在课堂上讨论丑小鸭朝向天鹅的成长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断用写绘自居丑小鸭,表达自己在那种处境中的选择和理由。并且,我们会在共同生活中不断活出这样的领会:瞧,你有成为天鹅(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愿望吗?你有为了愿望而去游泳(离开舒适区)的勇气吗?当梦想实现了,你是否会因为有一颗谦卑的心而不骄傲?
这样与生命打通的追问,就让丑小鸭的蜕变之路,变成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在此基础上,再由全班学生共同出演《丑小鸭》改编的童话剧。期末庆典时,我们再以丑小鸭的故事为线索,回顾我们寻找自己的旅程,把那些因为愿望而“游泳”的故事一一讲述。于是,每个“小鸭”都看到了更好的自己。
另外,在学生生日的时候,故事也会被作为特别的礼物送出。有奇思妙想的孩子,我就在课堂上讲《鳄鱼哥尼流》并特别送给他;生命需要方向的孩子,我就送他《海伦的大世界》……如此,不知不觉中,学生们爱上阅读,并种下了爱、勇气、梦想等关乎生命成长的种子。
在诗词中寻找生命的镜像
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中段学生的认知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此阶段,阅读由绘本故事转向了篇幅更长的经典童书和小说,在主题讨论深入理解故事内核的基础上,写作也由以“绘”为主转向以“写”为主。学生要在千万字阅读量的加持下,突破读写初步自动化双重大关。
于是,中国古典小说、国内外名著等被引入教室,很多学生如痴如醉,疯狂啃读。一个“十一”长假,阅读量最多的学生可以达到100万字。
同时,四年级学生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开启为期一年的“栖息在农历的天空下———古典诗词、节气节日、文化传统之旅”。这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综合课程———语文晨诵课讲解跟节气相关的诗词,吉他课学习弹唱,舞蹈课用肢体表达此种触动,美术课则用画笔进行相关创作,科学课观察物候现象和写物候笔记,还可以创作诗歌,撰写诗评。整整一年,我们在二十四节气中串起了150首古典诗词,学生们的创作从最初的几行到最后的上千字。
到了小学高段的晨诵课,李杜苏陶几位重要诗人被引入。我们以诗人精神发展历史为线索,带入诗歌。比如李白诗歌课程,我会带入40首诗歌,每日配合诗评写作一篇。最后一首《临路歌》,是在期末考试的早晨结束的,之后的考试作文,便以“李白,我心中的……”为题,学生们的写作带着温度,洋洋洒洒。学期末,我又用全班演出音乐诗剧作为课程小结,将朗诵、吟诵、舞蹈、歌曲综合融入。学生们演绎的李白,不是模仿别人的表演,而是对自己理解的李白精神的表达。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学科素养得到发展,而且,它们还共同指向———整体浪漫感知以儒释道为底色的中华民族之精神血脉。是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就藏在以孔孟老庄为底色的诗词歌赋、文化源流中。
就这样,学生们的生命在故事、诗词和经典的浸润中,初步触及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之思考,从而读写水平都有了新的跨越。
在经典中接续精神的血脉
进入中学,学生们在之前读写自动化达成的基础上,不再追求阅读的数量,而是在小学高段向纵深突破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课下,各种广谱书籍被引入,作为文理综课程的浪漫背景和深度补充。同时,语文课引入中国文化经典;高中则在此基础上,引入西方文化经典。
比如中国文化经典,会被以问题的方式设计成预习单,作为课程带给学生:通过《世说新语》有趣的故事,我们体会魏晋名士的精神风骨;之后选择《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揭示他们如何一步步从普通人到圣贤的精神历程;在学生们对儒家精神有了初步把握的基础上,带入发展儒家精神的《孟子》、儒家集大成者王阳明和他的《传习录》……这些课程伴随整个初中阶段。每学期进行4周20个课时,学生们常常讨论得热火朝天,兴奋不已。之后的写作,40分钟可达千字,周末时间充裕的情况下,灵感喷薄的学生写作可达万字以上。
这个阶段,学生进入青春期,正在经历剧烈的同一性危机。化“危”为“机”的关键,不是在“荷尔蒙”这样的生物性变化上做文章,而是引导个体与社会良性互动,从而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意义。所以,我会不断尝试将经典和学生的生命打通。比如,结合有意义的节点,利用暮省、班会等时机,以演讲的方式反思自我,观照世界。
现在已经进入十年级。从一年级就跟随这套课程成长起来的瀚同学,阅读经历了从海量到深度的发展过程。伴随阅读的同步,他能够享受中西经典带来的深刻欢愉,并从哲学的维度省察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而四年级进入的栋烨同学,则更清晰地体现经由经典阅读带来的变化。刚来的时候他写:“过去,我上课只想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吃饭。”在经历了儒家大课程之后,他开始对人之光辉有了向往,在七年级写给自己的生日信中说:“这几年常常是在舒适区里面待一会儿,但是,心里又想去外面看一看,一去外面又要碰壁,一碰壁就又回舒适区了。”
到了九年级,栋烨再次在写给自己的生日信中说:“我在王阳明课程中所学到的,其实正是我所朝向的生命状态。当我被问到未来想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老师而且是语文老师。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浸润了我生命的经典,经由我手再传下去。”
而现在,十年级的他在开学计划中说:“有时候我在想,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反问给一个大人,兴许他会让我想想,我想从事什么职业。但是我对自己使命的设想,不是局限于职业,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并让我所处的环境变得更好———我的意思是,无论我想要从事何种职业,使命都可以在我所从事的职业之中如其所是地呈现。”
我想,这,就是阅读的意义。
穿越了经典的生命,或许,未来将有能力活出基于价值选择的不凡人生。而民族复兴与发展的希望,正寄托在这一代具有理性思辨能力和使命感的少年身上。
(源自“中国教育报”)
责编:彭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