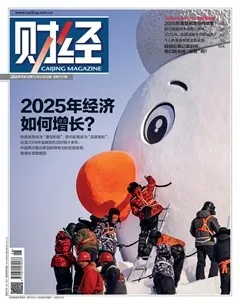官府与富民在粮食粜卖差异化目标下的博弈

《两宋农村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
余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10月
在粮食粜卖环节中,官府主要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为目的参与其中,对于富民而言,则是为了售粮以赚取差价。大多数情况下,在市场自发形成的粮食市场网络体系中,富民通过转手贸易获得正常经营利润,对此,官府并不过多干涉,只是借由商税的征收来分享富民粮食贸易的利润,以此达到官民两利的结果。
当官府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为目的出粜粮食,却因自身诸多局限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时,富民便成为国家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补充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二者间的博弈便在所难免。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早在秦汉时期,国家仓廪制度就已经基本形成,此后历朝不断完善,成为国家备战备荒的重要物资保障制度。宋代官府籴买粮食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增加国家常规的粮食储备,以应对荒灾之年和季节性的粮食短缺问题。
淳化三年(992年)六月,太宗下令创设常平仓时便明确指出:“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遂为永制。”把常平仓储低价出粜以救济贫民之事制度化。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真宗“令唐、邓等八州发常平仓粟,减价出粜,以济贫民”。庆历四年(1044年)春正月,“陕西谷价翔贵,丁丑,转运司出常平仓米,贱粜贫民”。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神宗诏:“闻齐、兖、济、郓州谷价贵甚,斗值几二百,艰食流转之民颇多。司农寺其谕州县,以所积常平仓谷通同比元入价,斗亏不及十钱,即分场广粜,滨、棣、沧州亦然。”这些都是官府通过减价出粜,稳定市场粮价,救济贫民的事例。旱涝灾荒之时,官府也会采取低价出粜粮食的办法,帮助小农渡过难关。
官府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为目的出粜粮食,尽管初衷甚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大多不能如愿。
一是国家粮食储备有限,遇到重大灾荒,往往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景祐元年(1034年)秋七月壬子,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闰六月四日,提举两浙路市舶曾愭言:“赈济户口数多,常平桩管数少,州县若不预申常平司于旁近州县通融那拨,米尽旋行申请,则中间断绝,饥民反更失所。”因此,宋人李觏曾指出常平米谷“至春当粜,寡出之,则不足于饥也;多出之,则可计日而尽也”。有时也因仓储管理混乱,储备粮食被侵支或不堪食用,无粮应急。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臣僚言:“国家置常平、义仓,为水旱凶荒之备。近来州县循习借用,多存虚数。其间或未至侵支,亦不过堆积在仓……初未尝以新易陈,经越十数年,例皆腐败而不可食用。”乾道四年(1168年)四月,臣僚言:“蜀中自成都、汉州之外,常平、义仓之额虽多,而借兑之数不一,甚者但存虚籍,本无储蓄,或遇水旱阻饥,何以为计?”
可见,原本作为水旱凶荒之备的常平、义仓,在真正面临灾伤需要出粜粮食时,有的甚至面临无粮可粜的窘境。
二是动用仓储之粮需经层层上报批准,往往无法满足地方救灾的紧急需要。如徽州“新安易水旱,地狭而收薄,虽常平有粟,然请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绝,赈恤不时”。“范忠宣(范纯仁)知庆州,大饥,饥殍满道,公请发封桩粟麦,郡官皆曰:‘须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岂能及乎!’”
可见,官府仓储粟米赈济灾荒缺乏应急预案,大都需要循常例向上级申报获批后才可动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常平仓出粜赈济也会因程序烦琐而削弱其救济灾荒的时效性。
三是官府出粜粮食的地点辐射范围有限。官府开仓救灾,设置的粜米地点多是在县治所、市镇等地,大多难以覆盖灾情发生的各地。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臣僚言:“诸处粜米赈济,只及城郭之内,而远村小民不沾实惠。”乾道四年(1168年)四月,司农少卿唐瑑言:“福建、江东路自今春米价稍高,民间阙食。郡县虽已赈粜,止是行之坊郭,其乡村远地,不能周遍。”也就是说,部分偏远的乡村受灾之处,因远离州县,并未享受到官府低价赈粜的实惠。
可见,仅仅依靠国家粮食储备平价出粜来突破民食艰辛的困境,往往收效有限,这便为活跃在粮食市场中的富民提供了成长空间。有的富民见到利好,争与出粜,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有的富民预测市价看涨,闭廪不粜。
针对此种情形,肩负着赈灾救济重任的地方官员通常会采取官方限价政策,禁止有积粮的富民趁机加价倒卖。然而,这一做法有时也因损害了富民的利益而适得其反。
开宝五年(972年)秋七月,陈从信对赵光义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
也有少数地方官员主动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来解决米价上涨问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乃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包孝肃公守庐州,岁饥,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但如此熟谙市场规律的官员毕竟是少数,而且靠市场自发调节供求,需要具备信息传递畅通、交通便捷和区域市场开放等条件。
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选择运用“劝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谓“劝分”,是指官府劝谕富民无偿捐赠粮食或低价出粜粮食,以帮助贫困民户。“劝分”的关键在于“劝”,官府通常采用道德感化方式劝谕富民。
“劝分”是两宋时期国家应对灾荒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面对官府“劝分”,不少富民响应号召,积极主动参与赈灾,天禧元年(1017年)四月,江淮两浙制置发运使李溥言:“江、淮去岁乏食,有富民出私廩十六万石粜施饥民。”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多户富民大家共同参与赈济的情况。
南宋时期,“劝分”之策更加广泛地运用于赈灾济贫,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右谏议大夫赵霈称:“去秋旱伤,连接东南,今春饥馑,特异常岁。湖南为最,江西次之,浙东、福建又次之。今日赈救有二,一则发廩粟减价以济之,二则诱民户赈粜以给之。”根据张文的研究,两宋时期“各地一遇荒灾,往往行劝分之政,将劝分视为荒政的一部分,尤其是越到后来越依赖于劝分”。在“劝分”实际执行过程中,财富力量不断增长的富民阶层,已经成为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所依赖的重要对象。
一些富民之所以愿意与官府合作,响应“劝分”,低价出粜粮食赈灾救济,是因为希望在乡里社会获得更高地位。宋廷规定,响应国家“劝分”者,根据捐赠或出粜粮食的多少,给予不同等级的荣誉旌表或官职奖励。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诏:“诸道州府被水潦处,富民能出粟以贷饥民者,以名闻,当酬以爵秩。”南宋董煟言:“国家赈济之赏非不明白,五千石,承节郎进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进士补上州文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富民出粜粮米的行为。
此外,一些富民也在积极追求文化教育,“耕读之家”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宋人张守就曾指出,宋代社会“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
在追求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富民群体的思想不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道德上有了进步,因此以道德规劝为主的“劝分”也往往容易为富民所接受。这些富民群体利用手中的粮食接济邻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为自身在乡村社会中赢得了较高声誉。
也有一些富民是为了缓解乡村粮食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如婺州长者潘好古,“有塘曰叶亚,溉数百顷,独听民取之不为禁。斥塘下田以广潴蓄,或献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乡邻安,则吾安矣”。有的径直就是为了在水旱灾伤之年免于劫杀,这类富民出粜赈济贫民仅是为求自保。
总的来说,粮食在宋代已经成为大宗商品在农村市场流通。作为交易主体的官府和富民在粮食贸易中既有同是买者的竞争关系,又有买者(官府)和卖者(富民)的合作关系,还有同是卖者但目标不一致的对立关系。
首先,富民是国家的基层统治必须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尽管民间参与农村粮食贸易的经济主体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在市场起主导性作用的是那些由乡村地主和富商组成的富民。面对战争军需,国家通过议价筹粮,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富民的支持才能完成任务;面对灾荒肆虐,国家欲发廪赈灾,也需要对富民“劝分”才能缓解灾伤。
其次,在农村粮食贸易的复杂博弈中,地方官府正因认识到富民拥有凭借财力和地缘左右市场行情的优势,故无论是“和籴”还是“劝分”,大都以满足富民阶层的合理诉求来诱导,使其粮食买卖活动符合国家预期的社会目标,一些富民也因积极响应国家的粜籴号召,获得了国家认可的乡里社会地位。
因此,从官府与富民围绕农村粮食贸易所展开的多重博弈中可以看出,富民阶层开始成为宋代乡村社会多元共治的主体之一,宋代统治者也认识到富民阶层对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因而既利用富民的财富来增强国家力量,又辅以激励安抚等措施保障富民阶层成长壮大。
(本文节选自《两宋农村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编辑:许瑶)